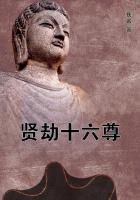崔氏体态微丰,肌肤白腻细柔,四十多岁的人保养得仍像是三十出头。一身绣衫罗裙,乌黑的头发,插着一支金凤簪。圆脸含笑,看着不像是花楼出身的教养娘子,而像是好人家出身的富太太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花绿芜想要立于不败之地,恢复完璧之身是头等的大事。
崔氏的绝技正在此处。其技艺之高,可巧手补天,返璞归真。
纵然崔氏长了一张慈爱的脸孔,动作也十分温柔,花绿芜仍红透了耳根。她大概一辈子也没有这么乖过,绷着身子,咬着唇,大眼睛水汪汪地,带着点儿纯真和委屈,跟被人点了穴道一样,乖乖地一动不动。
崔氏笑道:“姑娘骨架子小,面嫩,女子这样才好,能常葆青春。”
花绿芜咬着唇道:“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研究出这个?那样子痛一次还不够受的么?偏还要来第二次,舒服的也只是男人。”
崔氏道:“姑娘万金之躯,不知道咱们下等人的苦处。有些姑娘天生也是身娇肉贵,玲珑明亮的,偏偏命歹,或因家里穷,或因为府里男人犯事儿遭连累,入了那花楼,不得不货腰为生。好容易熬下来,见了喜欢的书生,又怕人轻贱,所以才不得不使出这招。”
花绿芜想一想,确实如此,便不吱声了。
过了整整两个时辰,崔氏额上冒出细汗,起身道:“好了!请姑娘放心,一个月内绝出不了岔子。只是到时候注意用酒灌醉了男人,再洒点儿鸡血羊血什么的便成了。”
花绿芜嘴里应着,心里头好笑:这崔氏当自己也是骗婚的了。想到此处,忽然又深入一层,心想要是拿这招对付罗钰,他的脸色该多好看啊,呵呵呵……
“瞧姑娘笑起来,真好看,跟那二月豆蔻似的。”崔氏也抿嘴笑,一则这姑娘招人喜欢,二来独孤家的五公子亲自交代的她,可见这姑娘前途远大,不可限量。门路多了方能发财,她起了巴结的心,便卖好道:“我摸着姑娘的手有些凉,姑娘骨架子小,是否来月事的时候格外痛呢?”
花绿芜小脸一红,讶道:“连这你也能看出来!”
崔氏有些得意道:“这姑娘就不知道了。我们这些人虽然没念过医书,但干的这行当,对女人得的一些病症见的比宫里头的御医还多,知道的土法子偏方也不少!女人呐,天生比男人娇弱,多灾多难的,都得仔细将养着才行。依我看,姑娘这是小时候受了寒,寒气浸体,一直没发散出来。既如此,我这里头倒有些有用的偏方,虽说不一定能除得了根,到了紧要的时候缓解缓解还是很见效的。”
“这感情好,我正为这件事儿所困呢。”花绿芜高兴极了。
崔氏趁热打铁,便口述了一张方子,令花绿芜提笔写在纸笺上。细看,全是一些温补之类的药物。
“姑娘来月事前七天,照着这方子抓了药,加上一大块红糖熬成浓浓的一碗药汁,撇去沫子甜甜地跟喝糖水似的,每早晚各喝上一回,等连喝七天,来月事的时候就停掉。这叫做暖宫,我们上头的老前辈一代代传下来的,管用!”
花绿芜很怕苦药,听了更是庆幸,立即赏了崔氏一把金瓜子。崔氏得偿所愿,也喜滋滋地走了。
披星戴月,日夜兼程,第二天清早便到了蒲州。
皇上委派了刑部侍郎查办此案。此君接旨以后便对心腹随从说:“左边猛虎,右边豺狼,这件差事不好办。咱们唯有小心翼翼,两边都不得罪方能保得平安。”
因此,见到独孤栖白一行人,并不刻意为难。
简单交接一番,事不宜迟,即刻启程,快马加鞭第三天就到了都城。
刑部侍郎去交差,独孤季川官拜定远将军,此次是以探亲的名义出来。值此多事之秋不敢再多露头,便回了家。
独孤栖白虽因身体残疾,无官职在身,作为国师独孤宇瞻的爱徒,却也常在御前行走。此次因他是找到郡主的第一人,便一同进宫,随时配合正主们的调查。
花绿芜被一顶青雀软帘小轿送到延禧宫,刚进了门,便有两位三十余许的宫装女官请她去盥洗沐浴。
原来后宫里头有这么个规矩,宫中女子从外头归来,怕染了外头不干净的东西,必须先去浸了药材的热水里清洗干净,身份高贵的,再根据各人等级请相应的御医例行检查一番。
花绿芜心里明白,这是太后借机验她的身呢。
花绿芜便正色道:“既如此,太后娘娘派了哪位嬷嬷来,等本宫净了身以后验看便是。其余人等都撤了,本宫不是猴子,不必耍戏给她们看!”——独孤栖白说收买了验看她的嬷嬷,她自然要防备其他人等。
左边黄衣女官吃了一惊,心道人家说郡主经此大难,性情大变,果然不错。往日那么软糯团子好脾气的人,焉得语气这么冷硬过。
右边青衣女官想拿捏郡主作脸,因此便垂着眼皮子讪笑道:“郡主擅自改了规矩,这怕是不妥。”
“哦?哪条规矩?记载在何种礼仪典籍上?请你逐字逐条拿过来。”
“这这……郡主说笑了,是累年累月传下来的规矩,并未有典籍。”
花绿芜便明目张胆地冷笑,缓缓道:“既如此,没有典籍的事情你不用去问太后娘娘的旨意,却随意来吩咐本宫。原来你竟是宫中的规矩了,谁都得按着你的规矩来,是么?”
“奴婢该死!”那青衣女官吓得立马伏首跪地,这天大的罪名她可担待不起!那黄衣女官与她一道的,见状不得不跪福求情。
“纵然她鲁莽了,好歹是太后宫里的人,请郡主饶恕这一遭,省的太后听了她做的蠢事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