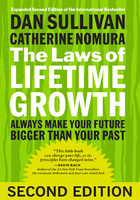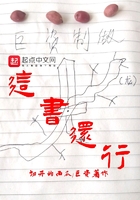一
北方春日的下午,阳光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一会儿就能把人晒出困意。杨玉梅从厚厚的案卷上抬起头,睡意朦胧地望了一眼窗外,窗外的国槐还在冬眠,显得毫无生气。收回视线,杨玉梅又看了一眼窗台上的绿色植物,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一盆来自南国的花卉长得蓬蓬勃勃,绿意葱茏,给她的办公室平添了几分生气。这盆花是春节前单位统一购买的,每个办公室分发了一盆,虽然到现在她也叫不上它的名字,但她让她在北方漫长的冬季里提前感受到了春的气息,乃至生命。
想到生命,杨玉梅把思绪停留在了她刚刚埋头的案卷里。那是一幢过失致人死亡案,被害人是一个深陷毒渊的四十多岁男子,犯罪嫌疑人不是别人,而是和他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了近二十个年头的结发妻子。事实上,妻子的本意是要帮丈夫戒除毒瘾,未曾想却要了丈夫的命。想到这里,杨玉梅在脑子里还原了案发时的情景,以及这个家庭前前后后的遭遇。
二
正月初四,正是举家欢庆的日子。一个叫程英的四十岁女人正在家里打扫卫生,她的几个亲戚刚刚来家里串过门。对于亲戚们还愿意和她来往,在过年的时候还愿意到她家里来坐坐,程英的内心是欣慰的,说明亲戚们并没有因为她有个吸毒丈夫而嫌弃她,她还是他们愿意走动的一门亲戚。但她的喜悦还没来得及发散,就因为丈夫的回来,让她的生活掉入了冰窟,甚至让人绝望。
说起来,程英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二十岁的时候,从偏远乡镇嫁到了城郊,丈夫张军比她大四岁。一开始,娘家人包括亲戚朋友都觉得她嫁得好,男人老实本分,离城又近,地里随便种点菜,拉到城里的市场上就能变成现钱,干完农活,晚上还能换身新衣服到城里的舞厅跳舞,或者去电影院看电影,日子过得和城里人几乎没啥两样。程英也很满意自己的这桩婚姻。
短短几年里,她们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一家四口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由于家里耕地少,加之人口急速膨胀,仅靠地里的收入,只能勉强糊口,而且地里的农活,一个人就能轻轻松松干完,张军便把农活留给程英,自己到城里打工,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回家,一家人团聚,倒也其乐融融。张军为人忠厚,也没什么爱好,每个月挣的工资,留点零花钱全都如数交给程英保管,程英也打心眼里放心自己的丈夫。
在城里打工一年多后,张军渐渐变了,拿回来的钱越来越少,后来甚至向她要钱花。程英问起来的时候,张军总是躲躲闪闪,要么说没有发工资,要么就说请人吃饭花了钱。程英最初也没在意,男人嘛,在外面交往很正常,他也希望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更多的朋友。
渐渐地,程英发现了一些破绽,张军下班后总是不按时回家,而且常有鬼鬼祟祟的人来家里找他,说话还背着她和孩子,交头接耳,很不正常。
当张军又一次伸手向她要钱时,程英终于忍不住问起了原因。张军起初一口咬定没事,后来终于承认自己染上了毒瘾。程英顿时感到一股寒流传遍全身,没想到自己老实巴交的男人也会学坏,她歇斯底里对男人发泄了一通,希望男人能够戒毒。男人倒也听话,乖乖去戒毒所戒了三个月毒。戒毒回来后,男人正常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又重蹈覆辙。任凭程英说尽好话,男人口头上答应不再吸毒,但背后仍在偷偷摸摸地吸。
从那时开始,程英的命运已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噩运也在一天天向她靠近。
丈夫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吸毒者。他虽然还在城里打工,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而且全都买了毒品。家里的日子,全靠程英一个人支撑。
为了让丈夫戒毒,程英想过多种法子,她找过丈夫的兄弟姊妹,兄弟姊妹们苦口婆心劝说没用。她找过村干部,村干部做思想工作还是没用。她向公安报过案,强制戒毒还是没有用。程英自叹命苦,只希望丈夫有朝一日能够浪子回头,但这样的日子遥遥无期。程英曾想过和他离婚,并以此为条件向丈夫摊过牌,但丈夫已经深陷毒渊,不能自拔,他甚至爽快地答应了程英的要求。他也觉得程英跟了自己太委屈。但心地善良的程英却又心软了,她心疼两个孩子,不希望孩子没有父亲。好在两个孩子从小懂事,学习也好,女儿刚满十岁就能在程英忙的时候替她做饭,帮她干些家务。孩子是程英最大的安慰,也是她生活的希望,她盼望丈夫也能看到这些,清醒过来。
三
五年前,城市开始扩建,程英所在村的耕地全部被征用,为了补偿他们,每户分到两套九十多平方米的楼房和一间不大的门店。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他们留下了一套住房和门店,将另外一套住房卖给了别人。
家里有了一笔钱后,张军更加贪婪了,他不愿去打工,白天一整天都呆在家里,一到天黑就不见了人影,有时候甚至整夜不归。这期间,张军的脾气越来越坏,稍不如意就会大发脾气,轻者摔碟子摔碗,重则打骂孩子,程英去阻挡,就会把巴掌甩在程英身上。只要张军脸色不好看时,为了不招来他的巴掌拳头,程英和孩子们就都躲得远远地,母子三人忍气吞声盼望有朝一日他能改过自新。
张军也有清醒的时候,每当此时,他会向程英和孩子们道歉,发誓再不吸毒,不对家人发火。但只要毒瘾一发作,他就会像魔鬼附体一样难以自控。
为了让丈夫离开毒品,程英想从经济上制裁他。自从地被征后,程英试图牢牢抓住家里的经济大权。但这些只是表面现象,丈夫毒瘾发作时是一头野兽,拿不到钱,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就这样,程英在心底里牢牢筑起的堤坝,总是被丈夫毒瘾发作时的洪水给冲决,她内心的创伤也随着丈夫毒瘾的一次次发作越来越重。到最后,她只能妥协,放任丈夫胡作非为。
短短几年时间,丈夫已经把卖楼房的钱糟蹋了一多半,程英既心疼钱,也心疼丈夫,尤其他毒瘾发作时用头撞墙,甚至拿起砖头来砸自己脑袋的疯狂劲,一直是她不忍面对的伤痛。
女儿马上要高考了,儿子也上了初中,两个孩子都是学校看好的苗子,眼看着家里到了大笔花钱的日子,程英不希望丈夫再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她希望能给孩子们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入冬后,程英找张军的兄弟姊妹说了自己的想法。兄弟姊妹们这些年来眼看着程英在张军的阴影下备受折磨,他们也对自己的这个兄弟恨铁不成钢,只要能使张军离开毒品,他们什么都愿意做。在兄弟姊妹们的轮番劝说下,张军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吸毒给家人造成的危害,答应再次去戒毒。张军戒毒的日子里,家里总算清净了一段日子。春节前,张军回来了,信誓旦旦地向程英和孩子们保证,以后一定远离毒品。程英也天真地以为,丈夫这一次能够彻底远离毒品,让她和孩子们过上安稳日子。
但就在正月初四那天下午,程英正在家里打扫卫生,并想着心事的时候,丈夫从外面回来了,进门就伸手向程英要钱。
程英问他要钱做什么。张军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地让她拿钱。
程英强烈地意识到丈夫旧病复发了。她冷冷地回了一句:“没钱。”
但丈夫已经冲进卧室开始四处乱翻。
程英见状,跟过去拦挡丈夫,并试图提醒他自己发过的誓言。但张军哪里肯听,他一把推倒程英,头碰在了床头上。幸亏程英早有防备,只起了一个小包。在隔壁屋里的女儿和儿子听到动静后跑了过来。
“妈妈,你没事吧?”女儿过来扶起程英。
儿子也拉了父亲一把。“爸爸,你不是答应过妈妈再不吸毒了吗?”
张军狡黠地答应着儿子,让孩子们先出去。程英也示意儿女们先出去。
两个孩子刚一出门,丈夫就不顾程英阻拦又开始了翻腾。因为他非常清楚程英把钱放在什么地方。程英一看这架势,明白丈夫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程英内心深处是再也不希望丈夫重蹈覆辙的,她一边扑过去从背后拦腰抱住丈夫,一边喊孩子们把绳子拿来,他们要合力把他绑起来。其实,用绳子绑的法子还是张军自己想出来的,以前他毒瘾还不怎么深的时候,有几次毒瘾发作,他自己要求程英把他用绳子绑住,等过了那一阵狂躁期再解开绳子,也能起到一点作用。但后来毒瘾越来越深,用绳子绑根本不起作用,他也不愿意被绳子绑,甚至看到绳子就恐惧。但眼前的情景已经不容许程英多想,她脑子里想的是尽快控制丈夫。
绳子很快拿来了,程英母子三人七手八脚把张军按倒在床上,绳子在张军身上缠绕了几道。他当然不愿意束手就擒,他在极力反抗。但他的反抗几乎多余,因为家人帮他解毒的决心远远大于他的毒瘾。张军很快被五花大绑。
就在母子三人松手的一瞬间,张军一跃而起,弯曲的身子撞碎窗户玻璃,重重地甩出了他们住的五楼。
在那个原本平静的下午,就因为张军的那么一跃,一家人的命运又一次被改变。
程英母子迅速从楼上冲下来,楼下来来往往走亲串友的人们已经先一步来到张军身边。只见他脸朝下趴在地上,脑门上一股殷红的液体正在汩汩下流,鼻子和嘴里也在流血。
“赶快打120!”人群中有人拿出手机来拨电话。
程英母子三人急忙蹲下身解开绑在张军身上的绳子,但张军鼻子里已经没有呼吸。程英立刻瘫软在地,儿女们也跪在父亲身边开始哭泣。虽然他们并不喜欢他,甚至惧怕他,但他毕竟是他们的父亲,他们的身体里始终流淌的是他的血。
张军被“120”拉走了。
程英很快被“110”带走了。
这个夜晚,这个曾经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家变得死寂一般。两个儿女胆怯地看着家里熟悉的一切,他们说什么也想不到父亲会以这样残忍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让他们的内心如何得以安宁?但事已至此,他们想得最多的是母亲会不会也很快永远地离开他们,他们为下午的举动自责、抱怨、流泪,如果他们不去帮母亲绑住父亲,这一切也许就不会发生。但父亲始终是他们不愿在生人面前提起的隐痛。
就这样,姐弟两在矛盾纠结、自责抱怨中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夜晚。
张军的兄弟姊妹也是一夜未眠,他们叹叹自家兄弟的命薄,程英的命苦。他们为两个孩子叹气,为张军的丧事盘算。当然,最重要的是如何保住程英的性命,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两个孩子成为孤儿。
程英在公安局待了一夜又被放回来了。并不是她的行为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而是让她先回来处理丈夫的后事。
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变得残缺不全,这是谁都不希望发生的,但他们谁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变故。
四
“叮铃铃……”杨玉梅抓起话筒,但电话里没有声音。
“喂,你好,请问你找哪位?”但电话那头的人却不说话。
“再不说话我可挂了。”杨玉梅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要么是打错电话,一听声音不对就迅速挂了。要么是案件当事人或家属打来的,打通电话往往又不知从何说起。
就在杨玉梅要挂电话时,话筒里传来了一个女孩怯生生的声音:“阿姨,我能跟您说话吗?”
“当然可以。”杨玉梅口气缓和下来,“你是谁,有什么事你就说。”
电话那头的女孩似乎没那么胆怯了,她说自己是程英的女儿,叫燕子,希望杨玉梅不要判她妈妈死刑,她和弟弟已经失去了爸爸,他们不希望再失去妈妈。
女孩声音颤抖得厉害,杨玉梅能体会到女孩此刻的心情,她在电话里安慰女孩说:“你和弟弟都不要着急,你爸爸的死虽然和你妈妈有关,但你妈妈不是故意杀人,不会判死刑。”杨玉梅还想安慰这个女孩几句,但她找不出合适的词,只好说判刑的事不是她一个人说了算,让他们姐弟相信法院一定会作出公正判决。女孩似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着“谢谢”挂了电话。
挂断电话后,杨玉梅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她清楚地记得,给她打电话的女孩正在读高三,而且是学校看好的苗子。她自己也是一个高三学生的母亲,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讲,她也希望这个女孩不要因为家里的变故影响高考。从一个高考生的到角度出发,她更不希望这个女孩在即将进入考场前,听到自己最亲的人被判刑坐牢的消息。
事实上,这起案件的当事人程英在取保候审后,案子还在公安局和检察院期间,程英原来村子里的人们、丈夫的兄弟姊妹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先后向公安局和检察院递交过过联名材料,善良的人们,在材料中痛陈张军的不务正业,对妻子和孩子不负责任,呼吁司法部门从轻处理程英,给两个孩子一点希望。材料中甚至说张军死有余辜,他死了是对程英和两个孩子的解脱。虽然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剥夺别人的生存权犯法,他们的说法也有点过激,但足以说明程英周围的人们对她的遭遇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
程英的两个孩子也分别给公安局和检察院写过信,他们用稚嫩的笔触阐述了自己对生命的看法,以及父亲和母亲在他们生命中的地位。他们的父亲一生活得不光彩,但他们的母亲能够包容他,迁就他,他们希望司法部门看在他们年幼的份上,不要让他们的妈妈坐牢。
公安局和检察院领导对此情况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答复所有关注程英的人们,司法部门会综合考虑,依法酌情处理。
半个月后,程英的案子开庭审理。一大早,法庭门口就围满了前来旁听的村民和亲属。整整一个早晨的审理过程中,旁听席上的人们始终表情肃穆,所有人都在仔细听着法官及公诉人的一字一句,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在他们看来,程英及两个孩子的命运就掌握在法官手里。
庭审期间,不知是因为紧张、恐惧,还是处于其他的原因,程英始终低垂着头,她机械地回答着法庭的提问。杨玉梅觉得眼前的这个杀人嫌犯非但不令人憎恶,反而显得很可怜,让人从骨子里同情。
法庭调查结束时,程英哭了起来,她说自己对不起两个儿女,让他们失去了父亲。也对不起丈夫,是自己害了丈夫,要是自己对丈夫看得紧一点,也许他就不会吸毒,自己也就不会站在被告席上。此时,她所有的忏悔其实都是多余,因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假设根本不成立。
程英在法庭上哭,或许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方面,在法庭没有宣判前,她不知道自己究竟会不会被判刑,会坐几年牢,想到这些,联系到自己的孩子还小,这个被生活的苦难折磨得心力交瘁的女人,终于忍不住打开了感情的闸门,尽情地宣泄。另一方面,她的哭,也是在引起人们对她的同情。
由于案情特殊,法庭不能当庭宣判。
走出法庭,杨玉梅很快被一群人团团围住,他们是程英的左邻右舍,或亲戚姊妹。他们向杨玉梅打听程英会不会被判重刑,杨玉梅从他们一个个希冀的眼神中,看到了善良的人们对一个苦命女人的同情,也看到了他们对两个孩子的关注,作为一个女人,杨玉梅多少有些感动。当法官近二十年,庭审后被旁听席上的人拦住问话的情形她曾多次遇到,但像今天这样的场面还是第一次。以往被围住问话时,她看到的大多都是怨恨的眼神,甚至言语中大多会有恨她意思,好像法院给他们犯罪的亲人判刑是法官个人的行为。
看到这样的情形,杨玉梅为程英能有这样的好人缘而感慨。同样是女人,又同样是母亲,虽然她们的身份悬殊,且处于审判与被审判的地位,但她不希望这个女人被判刑,她甚至希望程英能够无罪释放。当然,她的这个想法有些天真,也有悖法理。
开庭后的第三天,杨玉梅又接到了燕子的电话。小姑娘还是怯生生的,不过语气比上次镇定了许多。
“阿姨,我妈妈会被判重刑吗?”显然,有了上次的通话,小姑娘已经认定法院不会判她妈妈死刑。
“你不要担心,也不要着急,再耐心等几天,判决出来就知道了。”杨玉梅之所以不能给小姑娘肯定的答复,因为在上审委会前,她也不确定能判多长时间。不过,处于对这一家孤儿寡母的同情,她倒希望最好能判缓刑,也许对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能够有所帮助。
一周后,程英再次来到法庭接受宣判。杨玉梅发现,这个和她年龄差不多大的女人,仅仅一周时间就老去了一大截,仿佛她过的不是七天,而是穿越时空提前走完了七年的岁月。看来,她的思想压力之大绝非常人能够想像得到。当宣判结束,听到自己被判了缓刑,杨玉梅看到这个女人一直低垂的头突然抬了起来,目光里也有了神采,脸色稍有舒展。在她颤抖着接过判决书的一刹那,杨玉梅发现这个女人眼里含满了泪水,是喜、是悲,疑惑五味杂陈。她给杨玉梅深深地鞠了一躬后,在众人的簇拥下离开法庭。
结束了这起特殊案件的审理,杨玉梅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不清为什么,总之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放松感。
五
一晃几个月过去,时间进入了秋季。
这天下午刚上班,值班室给杨玉梅送来了一封来自外省某政法大学的信。杨玉梅觉得奇怪,自己在这里并没有熟人,会不会是有人打着该大学的旗号要引她上钩骗钱吧。身为法官,这方面的经验,她还是有的。
杨玉梅刚要将信件随手扔到一旁,但她又看了一眼,感觉不像是骗子的信,便打开信封想看个究竟。原来,这封信是程英的女儿燕子给她写来的,小姑娘在信中说她非常感谢杨玉梅,因为她的主持正义,她妈妈才没有坐牢。因为妈妈的案件,她对公检法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她发觉公检法的叔叔阿姨并非以前想像中的那么凶神恶煞,也不是社会上传闻的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他们也有可亲可爱之处。因此,在选报志愿的时候,她选择了政法大学,将来也要当一名像杨玉梅一样主持正义,惩恶扬善的法官。
看完这封来自大学校园的信,杨玉梅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其实,当年自己选择学法律,并最终穿上法官制服,也是因为与自己的亲人有关的一桩案件。二十多年前,当她还是一名高二学生的时候,她的父亲身陷一幢被诬陷的官司,因为对方势力庞大,加之公检法办案人员隐私舞弊,最终导致父亲身陷大牢,在狱中含恨而死,留下了她和多病的母亲。当时她就发誓,一定要考上政法大学,当一名伸张正义的法官,替天下如父亲一般被冤枉者伸冤,惩治贪官,扶弱济贫。如今,她当法官的愿望实现了,虽然现实距离理想有一定的距离,但她甘愿当一名默默无闻的司法公正的维护者,只要无愧无头顶的国徽,无愧于自己的良心。
她仿佛看到,几年后,燕子也穿上了法官的制服,而且就坐在她旁边。她相信,这个姑娘一定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