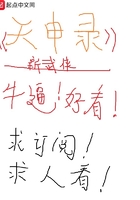十年一晃即逝,十年对于何人而言,无非仅是眨眼。十年虽短,可任由谁人也挡不住岁月的侵蚀,该弯腰的弯腰了,该长大的长大了。
正如‘柏木村’农家田地边玩耍的众多小孩。
七八个孩童围在一起,指指点点,更是哄笑不断。被围在其中的两孩童皆是一人手持一把木刀,看那嫩幼的脸颊上竟生出怒意,仿似两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张邈,我可不怕你,比刀,你定然不是我对手!”那手持木刀,身材略胖的孩童高举木刀指向眼前的孩童。
只见那孩童眉目清秀,年仅六七岁好似陶瓷般玲珑的娃娃,配上那怒气冲冲的脸,不仅没呈现出可怕,却更添几分可爱。
那被称作张邈的孩童不服,“呸!我爹教我的刀法,岂是你等能比的?看刀!”
话罢,那几寸长的木刀向着略胖的孩童当头劈下,看似不快的木刀,却又有几分力道。那略胖的孩童没料到对方说动手就动手,惊慌之下闭眼抬手。
恰好手中木刀与对方木刀相撞,姗姗挡住这一刀。
窃喜之下,那略胖的孩童大喝一声,抬脚便踹在张邈的小腹上,后者双手捂肚痛苦跪地。周围围观的孩童狂笑起来,愈笑愈大声。
“看吧,我说你张邈不会用刀,切要逞能,服不服?”那孩童仰头,充满胜利者的喜悦,指着张邈说道。
“论拳你不行,比刀更是不行,尽会吹嘘!”
“岂不是,没用!”
“哈哈哈,起来继续啊,张邈,你莫非认输了?”
围观的孩童开始挑衅,不断诉说张邈,跪地捂肚的张邈哪能受这般耻辱,一怒之下猛然起身,张牙舞爪扑向那略胖的孩童。
后者还沉浸在胜利之中,没料到这突如其来的攻击,被扑了个不防,两孩童同时倒地,抱在一起胡乱撕打起来。
助威声、哟呵声不断,倒地的两人愈打愈乱,先是用拳用脚,耳后开始爪、挠、咬!那略胖的孩子似乎比不过张邈,被张邈咬住耳朵,痛得他又哭又叫。
“我耳朵,耳朵!不打了...我认输,我认输啊!”那略胖的孩童开始求饶,张邈却未有松口的迹象。
眼见这田地边缘吵闹不断,田地中忙碌的长辈终于现身,入眼便看到那倒地撕打的两位孩童,其中一位老太猛然扔掉手中的物具,面露怒意几步跨越过来。
围观的孩童被老太推开,那老太二话不说,直接扯开扭打的两孩童,那略胖的孩童挣脱后,望着老太眼中瞬间涌出泪水,抱紧老太开始撒娇。
“阿婆,阿婆!张邈打孩儿,他...他竟然咬我,你看!”那孩童指着已被咬出鲜血的耳朵说道。
老太心疼之下轻轻抚摸孩童的额头,扭头间怒气滔天的双眼紧盯张邈,“又是你这杂种!三番五次伤我家阿虎,今日定要找你爹讨个说法!”
那老太一把抓住张邈的布衣,近乎拖着张邈往田地内走去。
“你放手!我不是杂种,是你家阿虎先惹我。”张邈不断挣扎,可这幼小的躯体怎能挣脱。
孩童一拥而上,围在身后跟随而去,那田地里众多村民摇头而散...
....
田地间,无一人不是面朝土地背朝天,苦劳的汗珠滴落在黄土之中。平淡无奇的日子,却让人沉积在其中,仿似这样与世无争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
那田地中,一位身穿布衣布裤,坐在田耕之上休息的男性,正手握粗粮往嘴里送。
此人面容平庸,眉目间流淌出‘幸福’二字,若是细看那男性手臂,翻起的手袖子下,是无数的伤痕印,不知是劳作时所伤,还是被某些利器所致!
隔老远便听到田地间老太的咒骂声,和众多孩童的嬉笑声。那男人无奈的低下脑袋,叹出一口气,缓缓起身。
老太一手拽着张邈,一手拉着略胖的孩童,眼中露出愤怒,盯着男性大呼,“张一霄!你孩儿又伤我家阿虎,今日若你不论个说法,我今日跟你没完!”
“陈婆,张某教导无方,还请陈婆息怒,这点碎银,请收下,拿给阿虎看郎中。”
张一霄正是男性的名字。一语结束,张一霄从怀中掏出碎银递给老太,后者本还想大怒,眼见这数量不少的碎银,立刻转怒未喜,“也罢,两孩童打闹而已,我这就带阿虎去瞧郎中。”
话罢,那老太拽着不服的阿虎消失在田地中,留下张邈与张一霄对视。
“爹,是他先出手的!”张邈低下头。
“爹不怪你,不过...今后别在打闹了。爹望你今后能考个秀才,平安一生。”张一霄伸手抚摸在张邈的秀发上,柔声说道。
“爹!孩儿不要考秀才,孩儿要做大侠,那行侠仗义的大侠!”
“什么大侠,傻孩子,真正的大侠,岂是彰显正义?顶天立地的男儿,是要保护家人,你娘亲还在后山采药,还不快去接你娘亲平安归来?”
此话结束,那张邈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有模有样的双手抱拳,“孩儿遵命!”,转身向着后山上飞奔起来。
张一霄望着远去的幼子,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溺爱....
....
后山之中寂静一片,奔跑的张邈并未发现不妥之处,往日后山即便人数不多,可依然能够看到足迹,却不料今日人影稀疏,一路甚未发现一个村民。
张邈若是抬头,甚是能看到树干上,那恐怖的刀痕印!
“娘亲今日怎么走这么深,快到半山了!”张邈一路未见娘亲踪影,焦急之下四处搜索。猛然间,那地面上翻倒的摇篮令张邈脚下踉跄,狠狠摔在地面。
摇篮中无数草药滚落而出,这摇篮分明是他娘亲的物具!
不仅是挥洒一地的药草,甚至那摇篮边缘还残有一道触目的血痕,血痕沿生到灌木丛中。不好的预感宛如浪潮涌入张邈的脑海。
年幼的他哪里经得起这般意境,颤抖之下几乎贴着地面爬到那灌木丛边。
当翻开那灌木丛时,张邈双眼瞪如灯笼。浑身无力,张开便要大叫,却不料一只黑手猛然捂在他的嘴边,张邈只感觉双眼无力,瞬间昏死过去。
那灌木丛中,正是一位无头的尸体,尸体身穿布衣...
夕阳徐徐呈现,田地中大多村民以陆续回家,张一霄却是心乱如麻,幼子去寻找爱妻,已几个时辰未归,担心之下便要动身去搜寻。
而当张一霄起身的顷刻间,后山树林中响起某个村民的惊呼声,“死人啦!快来人!死人啦!”
张一霄暗道一声不好,扔下锄头健步如飞,向着后山狂奔起来。那些刚要动身的村民才起身,那张一霄已奔到后山边缘。
若先前奔跑的速度很快,那此刻,张一霄宛如在飞。
双脚垫地的同时,弹射到树梢之上,仿似脱离了重心引力,在树梢之上飞驰起来,若是有高手在此,定要惊呼‘此人轻功简直逆天!’
一盏灯不到,张一霄已飞奔到山腰。
还未落地,那温和的脸色剧变,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杀意,可怕的杀意!单是望向那双眼睛,定要让人双腿发麻跪坐在地!
刺鼻的血腥味告知着张一霄不安。
遥远便望着那滚落在地的摇篮,而张一霄息在树梢并未动身,尽管他心急如焚,尽管他比谁也想要搞个明白,可他不能动!他在等,等着出手那一刻。
下山村民涌动,纷纷聚集向着山腰赶来,那纷乱的议论声入耳,张一霄依旧未动。
地面亦是如初,摇篮还是摇篮,鲜血仍是鲜血...
当村民议论声愈来愈近时,场中久等的黑影终于浮现!为首的黑衣人悄然从树身后露出脑袋,望着身侧的树身摇摇脑袋,仅此片刻,那黑人走出树身后。
第一个黑衣人出现,第二个紧跟其后,第三个也同时出现。
一连三人,每人皆是腰间悬挂着一把匕首。很难想象,这三人竟然在此静立了不知多长时间,若是心神不定之人,那早就厌烦了。
望着那呈现的三个黑衣人,张一霄本紧锁的眉头慢慢释然,虽杀意滔天,却不敢就此显露。对于一个成熟的刺客而言,杀意本是命根,但这杀意若不能掌控,高手瞬间便能抓住。
杀人不成,反倒事先暴露了自己。
三位黑衣人对视,相互点点头悄然转身便要离去!久等的机会终到,久蹲树梢的张一霄脱去那平庸的农夫之态,宛如飓风。
几乎残影还在树梢上,那人已飞射到后首转身的黑衣人背部。
那黑衣人双眼瞪大,还未回转身躯,却感觉腰间匕首落空,紧跟着脖颈上传入凉意,整个头颅已脱离了身躯!而第二个黑衣人,似察觉到异变,回身的时刻,双眼还未看清何物,胸口已被一掌拍中!
如同千斤巨石打中,‘咔擦’声入耳,胸骨断裂的同时,人已飞身吐血而死!
最后的黑衣人躲过了命运的终结,冰凉的匕首架在脖侧,吓得他猛然举手,而张一霄一把夺过他手中紧握的书信,还未翻看,那匕首已滑出银芒,带走了最后一条性命。
‘想见妻儿!十里外,茶铺相见。’
猩红的字体浮现在书信上,张一霄紧咬牙关,双眼爆发出无尽杀意,狠狠捏碎那书信,消失在密林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