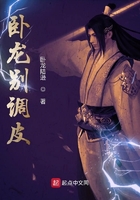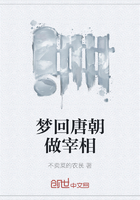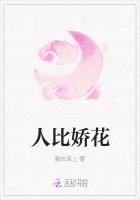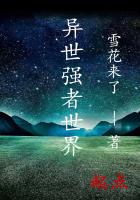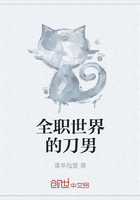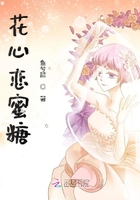姬职心中那个高兴,小样——跟我玩,看我不玩死你们。
那个……咚呛咚呛咚咚呛呛……
看着众臣一副我信你才怪的神色,姬职解释道:“寡人曾经见过乡间里社练。诸队齐发跑步前进的时候,如果不给他们设立一个目标,他们就会懒散。但如果有个目标,告诉他们跑到什么位置就算练结束,他们必定很快完成任务。
行旅也是这样,每个人上路的时候,心中都会有一个终点。身为燕国的一个国人,一个家主,一个大臣,甚至包括寡人这个君主,心中也都应该有一个目标。
目标有好有坏,但却不能没有。好的君主,应该是为他的国人们设定一个不断前进的目标,让他们努力奋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提高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水平以及社会地位。如此一来,家兴国旺,庶民归心。
寡人想要效仿秦国变法图强,想要为贵卿国人设置一个标杆,故欲设三十二级勋爵制,以鼓励国人奋进。”
上大夫卫满跳了出来,激动地挥舞着小拳头:“大王,是哪三十二级勋爵制呀,我等是不是也有分啊?我可听说秦国变法后,设了二十等军功爵,取消世卿世禄制,而我们这些个世卿却都没份,被取消了爵位,非得军功才得以赏,个个得像那帮子泥腿子一样从头再来。”
姬职早之前就做好了功课,殿上群臣的资料他都能倒背如流,现在这个急不可耐地跳出来的家伙是相邦公子平一党,背后牵连甚广,不可小觑。
还是喝头道汤好啊,利益上占了大头,虽说第一个吃螃蟹有危险,但是利润总是和风险相伴而行,风险越大,利润也就越大。如今秦国变法而强国,给各国开了个好头,让他们知道想要强国就得变法;可坏处是,有了秦国的前车之鉴,各国的旧勋和既得利益者相互勾结,扎紧自己的篱笆,阻挠那些损害自己既得利益的变革,让变法的难度大大增加。
但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咱们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姬职心中暗自腹诽,面上却是另外一副神色——和蔼如父:“各位都是国之柱石,寡人与诸位就是鱼与水,盲人与拐杖的关系——当然了,有一句话姬职没说出来:水臭了,我就换条河;拐杖不行,我就买根新的。
寡人之爵分公、侯、伯、子、男,每爵分六等,共三十等。爵位世袭罔替,但须世降一等;一等公爵禄二十万石,二等公爵禄十九万石,三等公爵禄十八万石,以此类推,六等男爵禄五百石。另设勋爵与准爵,为国民爵,无俸禄。勋爵可世袭,降则为准爵。准爵为荣誉爵位,实行终身制,不可世袭。得爵位者,可享有参政、人身自由以及私人财产不可侵犯之权,可免除兵役之外的所有徭役,只需缴纳赋税。同时为彰显国民对国家的贡献,制定纹章,公爵纹章为蛟,侯爵纹章为虎,伯爵纹章为狮,子爵纹章为豹,男爵纹章为狼,纹章均为银质勋章,添以五芒星以显级别高低,六等爵添星一颗,五等爵添星二颗,以此类推,一等爵有星六颗。勋爵与准爵纹章俱为鹰,分银质与铜质勋章以示区别。有爵者须佩戴勋章,不论官职大小,凡有爵者所过之处,无爵者须向有爵者行礼,低爵者须先向高爵者行礼,不尊条令者者当众鞭笞二十。同时设有国民参议院,参议院负责爵位的判定和授予,勋爵条令的施行,同时可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
众卿听了,心中那个火热,却又暗自嘀咕:这不就是世卿世禄制的翻版,只不过做了些改进,厘别的等级制度与世禄的多少,同时还要世降一等,可这个时代世卿之间斗争激烈,一不小心就会被诬陷,弄得生死族灭,名义上是世袭,可又有哪几个真真的世袭,封君终其一生能够保住自己的封地就算不错了,为了这个目标,大家都是不断的奔波劳累,互相算计,更有甚者是为了这个目标四处树敌,但仍死猪不怕开水烫,一句话——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春秋时代的晋国贤大夫伯宗就是被三郤诬陷杀害的,封地被夺,家族被灭;近有商鞅变法,功成而被诬陷身死,商地被夺;后有顶顶有名的纵横家张仪,一生周游诸国,把山东六国都给得罪了干净,靠着一张嘴,为秦国取河东诸郡,巴中黔地,最后还不是只身逃离秦国。这不是起点,也不是最后的终点,暗藏在贵族面具下的是赤裸裸的掠夺,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色——强者为尊,拳头大就是道理。
众卿对于国君玩了这么多花样,也就一句话——管他呢,只要不是根本利益受损,在怎么改革都行。既然国君给自己脸上贴花,说是改革,那就是呗,犯不着自找没趣。
同时又想到那丰厚的禄米,个个都是垂涎欲滴。
要知道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可是不高,如今整个燕国并行着针对私田的鲁国“初税亩”制与西周实行的助耕公田的劳役地租制,农民在耕种百亩份地(私田)之外,还要耕种领主的藉田(公田)。从经济学的意义来看,份地收获所代表的是农民的必要劳动,藉田收获所代表的是农民的剩余劳动。农民不仅要为贵族免费耕种土地,还要为自己的私田上交国家赋税。
据《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尽地力之教”所提供的数据:“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
据此,每人每年平均口粮为18石,五口之家全年粮食消费量约为90石,六口之家为108石,如果加上必要的种子等需要,起码要有一百石粮食才可敷用。百亩份地的产量当在此上下,农民才能维持生存。依此推算,当时每亩(周亩)的产量应在1石(大石)左右。
战国时代文献中对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供养的人数有以下记载:
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粪”,在这里作播种解),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万章下》)
从上述三条材料记载看,大体上上农“夫食”九人,下农“夫食”五人,平均“夫食”七人。若仍以《食货志》所载每人平均年消费粮食18石计算,七人粮食年消费量为126石,这可视为百亩份地的平均年产量,亩产为1.26石。
如果这种解释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可以据此推算一下西周时期的粮食亩产量。由于维持人体正常生长所需要的食量是相对稳定的,我们姑且把人均粮食消费量当作一个常数。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礼记·王制》)
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吕氏春秋·上农》)
上述文献虽然出于战国,但都是追述周制的。这里的“夫”,都是指一个农户的百亩份地而言。因此,引文中的“上农夫”“下农夫”不应连读,而应从“农”字点开。“夫食×人”指的是份地百亩所能供养的人数。从上述三条材料记载看,大体上上农“夫食”九人,下农“夫食”五人,平均“夫食”七人。若仍以《食货志》所载每人平均年消费粮食18石计算,七人粮食年消费量为126石,这可视为百亩份地的平均年产量,亩产为1.26石。这可能反映了西周稍为晚后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