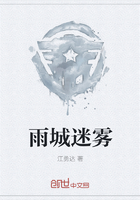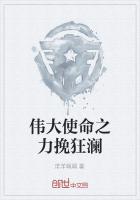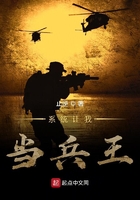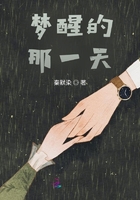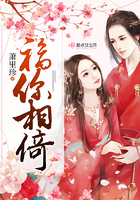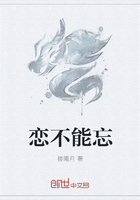十一月二十六日,东进纵队进了南宫城。
大家刚在司令部安顿好,就传来了范筑先将军阵亡的消息。徐向前刚收拾好自己的宿办室,正准备休息一下,就得知了这一噩耗。他呆呆地坐在那里,像一尊雕像一样一动不动;神情无比严峻,瘦削的脸上像罩了一层冰霜。看得出,他是在强忍着心中的巨大悲痛。此时,他的脑海里又俘现出在威县会见范将军时的情景,那健壮的身躯、那具有特殊魅力的音容笑貌都历历在目。他为失去这样一个慈祥的长者、一个伟大的抗日志士而深感悲伤,深感遗憾。呆坐了好半天,他才缓缓地说:“通知各机关负责人,今天下午在我这里召开纪念范将军座谈会。”
“是。”通讯员立刻跑了出去。
……
下午,座谈会准时召开。参加座谈会的有一二九师首长、东进纵队首长和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领导人。座谈会由徐向前主持。首先由宋任穷简单讲述了范将军的一生经历,重点介绍了他的爱国事迹。随后,刘志坚、陈再道、杨秀峰等人都先后发言,各自抒发对范将军的崇敬之情。最后,大家又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
……
陈再道:“……范将军不惜与日寇同归与尽,以身殉国。像这样的爱国将领,在国民党军中还真不多见!”
徐向前:“也不能这么说!国民党军中也有很多爱国人士。比如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他们也在顽强地抗击日寇。只不过我们冀南是******搞磨擦的重点,派到这里来的也都是反共顽固派。当然就看不到他们真心抗日啦。”
陈再道:“我真想不明白,既然******也抗日,为什么还要派人到我们这里来捣乱,破坏抗日?”
宋任穷接过来说:“心里不平衡呗!他看到八路军在华北发展很快,队伍不断壮大,心里很不好受。他派人到这里来,一是想和我们抢占地盘,发展他们的势力;二是想限制我们的发展,削弱我们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的时候好消灭一些。”
刘志坚说:“******答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本来就是被迫的。要不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将他扣押起来,恐怕到现在他还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
座谈会结束后,大家都站起身往外走。
“陈再道,你等一下。”徐向前叫住陈再道。
陈再道停住脚步,转身望着徐向前:“什么事?”
徐向前问:“各县的战况都报上来了吗?”
陈再道回答:“有五个县报上来了,其他县都还没有。”
徐向前:“等都报上来以后,你总结一下这次反扫荡的经验,以便以后吸取教训。”
“好。”陈再道说。
……
三天后,各县反扫荡的情况都报上来了。陈再道立即着手写战斗总结。然而,当他看着这一份份战报,心情却越来越沉重。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敌人的汽车、坦克和骑兵,在广阔的原野上横冲直撞,想怎么打怎么打;而我军则只能利用村落、坟头和土丘打击敌人。地形对我不利,已经成了制约冀南平原抗战的一个难以愈越的瓶颈。自从来到冀南,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陈再道。……
现在,陈再道认真地翻阅着这些战报,想从中找出破解这一难题的办法。忽然,他看到一则战报上说:在巨鹿县的某个村庄,我游击队隐蔽在村边的一个苇坑里,避免了损失。接着又看到一则战报上说:在广宗县,我军利用一条河沟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追捕。……看到这里,陈再道心里忽然闪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我们把所有道路都挖成沟,宽度只能走马车,而汽车和坦克却无法通行。这样,敌人的汽车和坦克不仅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还成了敌人的累赘。而我军则在道沟里任意穿行,战时容易接近敌人,战后容易撤退转移。……”想到这里,陈再道十分激动。他立刻找到徐向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徐向前听后,连连点头:“是啊。在这次反扫荡中,我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仅部队就伤亡三百多人。究其原因,除有些部队指挥不当,缺乏平原作战经验外,地形对我不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早就有‘改造地形、改造村形’的想法,现在看来到了非实施不可的时候。”
陈再道兴奋地说:“好!我们马上开会。”
徐向前又郑重地说:“这可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冀南地区,村庄星罗棋布,道路密如蛛网。要想把村与村的道路挖通,并保证大车通行,没有广大群众的参加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就发动全区群众,一起挖道沟。”
……
不久,冀南行署专门发布训令:“凡十五岁至五十五岁的健康农民,均须参加挖道沟活动,并限期完成。”训令还规定:“把所有大路都挖成深三尺,宽五尺的道沟,把挖出的土,堆到沟沿两旁,修成高一尺五寸,宽二尺的边墙,作为人行小道;每隔数十丈又挖两丈多的一段宽道,以便走碰了头的大车能够错开。”于是,一场群众性的挖道沟运动,在冀南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时值隆冬季节,土地冻得象石块一样坚硬。但到处是人山人海,有些人脱掉上衣,汗流浃背地抡着镐头,扬起铁锹掘地扔土。有的村庄,为了加快速度,在漆黑的夜里挑起灯笼,举着火把,昼夜不停地轮班干着。
据当时统计,冀南全区共挖路沟长达五万里。这些道沟如果连起来,可以从地球中心走个来回,其艰巨性可想而知。当时有人把这一工程称作平原的“马奇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