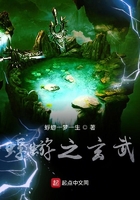四下一时寂静,静得呼吸可闻。
灰白的老脸抽搐几下,始终一言不发,杨虎振了振衣袖,在守卫押送中,慢慢走向囚室。忽然,他顿住,盯着囚室门前一抹人影,目光阴狠。
那人影纤细柔弱,缁衣衬得面容苍白。
“云依。”谢宜章上前,伸手扶她。
夏云依却轻轻挣开,径直走向对面,失魂落魄般,双眼一瞬不瞬。
天牢甬道内,火光忽明忽暗。光影中,两人对面而立,各自无言。
“我绝口不提过往,一心避世。”许久,她慢慢说话,声音像从远处飘来,带着沙哑,“你为何还要苦苦相逼?”
灰白的老脸露出轻蔑,杨虎哼了声,阴恻恻道:“问出这等话来,你真是飞龙的女儿,与你那死鬼爹爹一样,妇人之仁。为何?只因我绝不容许隐患存在。不管你对往事知道多少,都必须死,否则,就是我的心病。”
气血一阵翻涌,她晃了晃,摇摇欲坠。旧伤未好,又历波折,一天两夜接连剧变,早已身心交瘁。
旁边伸过双手,扶住她,谢宜章的声音带着嘲讽,冷冰冰道:“多亏这块心病,你才自投罗网。没想到吧?竟有一天,你会死在自己的狡狯多疑之下。”
火光摇曳,人影渐次散去。天牢再度关闭,锁住一片昏暗。惟有门上的青铜狴犴,在漆黑中注视一切。
天色破晓,朝阳如常升起,新的一天,与昨日似无二致。
夏云依伫立街边,深深吸入清晨的空气。
她活了下来,毫发无损地活下来。
回首昨日,如同梦境,一场生死诡谲的大梦。一朝梦醒,身心俱轻。
身世已解,仇恨已了。该死的人入罪天牢,而她,却被赦免。在这般波诡云谲中,竟能一力回天,她该感谢上苍,还是……
手指触上腰间,硬硬的冰凉。那是她的飞刀,又不是她的飞刀,因为,只有一层外壳,中间的金牌已被取走,就像人被掏去了心,忽失依托,不知何寄。
“不舒服么?”身后关切声近,谢宜章走过来,看着她。
“没有。”她摇摇头,淡淡一笑,“谢谢你,谢宜章。”
“谢我做什么。”谢宜章不由轻叹,莞尔道,“你呀,心知肚明。真正为你谋算一切,运筹帷幄的,另有其人。”
她垂眸,默默不语。
“生气么?”
“……不知道。”她盯着地面,手指绞紧袖角。
另有其人,但那是谁?还是那个孩子般的墨言吗?还是自己认识的墨言吗?熟悉的他,陌生的他,天真与奇谲忽然重叠,令她一时无措。应该生气么?不知道,因为,连自己也分辨不清此刻的感觉。
“谢宜章。”她抬眸,喃喃出神,“他,究竟是……”
“不要问我。”谢宜章看着她,轻叹道,“云依,这句话,该由你亲自问他。也只有你,最有资格问他。”
她没说话,半晌,点了点头。
“云依,往事加诸于你的重负,已经尽数卸掉。以后,你就再无负累,可以去做任何想做的事,这不是你一直希望的吗?”
“嗯。”闻言,她不由微笑。这是她的希望,没想到,此刻便已成真。
“那还等什么?想做什么就去。若有谁敢欺负你,你又不舍得动手,就来找我,必定替你出气!”谢宜章哈哈一笑,冲她挤挤眼,挥手道,“我先走了,不妨碍你找希望。”说完,忽又回头,有些愤愤:“如果,那个混蛋死皮赖脸,给你讲什么见鬼的故事,不要理他!”
“啊?”她一愣,茫然应了声,“……哦。”
谢宜章走了。街上人群开始熙攘,她杂在人流中,沿街漫步。清风拂面,带一丝暖意,她忽然觉得,自己就像片羽毛,飘然无定,悠悠地寻觅方向。
东西长街繁华依旧。庆善药铺关了,挤在周围的铺面中,似已被人遗忘。
转出长街,那条小巷安静许多,也短窄许多,五百二十七步,刚好走出。再拐个弯,屋影顿时成片。
她止步抬头,望着熟悉的别院,忽然,目光凝住。
高墙内,飘起一只纸鸢,越过琉璃瓦,迎风飞舞。清风扬起鸢尾长长,响起竹哨清脆。
她出神凝望。
不自觉地,她露出微笑,脚下步步进前。
“云依。”
蓦地,身后一声呼唤。她僵了下,缓缓回头。
几步之外,青衫男子负手独立,衣袂临风,眉宇间丰神高旷,一把折扇风度翩翩。
“飞尘……”
顿时,她红了眼圈,声音哽咽。压抑许久的情绪轰然溃堤,她像个小姑娘,哭得委屈。
“云依。”头上轻轻一暖,慕容飞尘的声音令人安稳,“我才至凉城,就听说了,猜到你会来此。”
“慕容!”她急忙拉住,顾不上擦泪,紧抓那幅衣袖不放,“没人算计我,慕容,你别去。”
朝阳柔和,照在她的脸颊,残泪莹然未干,难过却已被关切取代。
“唉。”青衫男子叹了口气,拉起她,径离别院大门,“云依,你不生气,我也生气。你不心疼自己,我还心疼你。走,跟我回去,回麒麟国,我们已经有了太子的一些消息。”
“慕容……”她吸吸鼻子,被拉着走远。依依回头间,纸鸢仍在飞舞,竹哨声声,越过琉璃墙瓦,似在呼唤。
鸢飞戾天,落下一抹淡影。高墙内,白衣少年牵线远望,目光温柔。
“公子。”陈为悄然出现,看着那个少年,欲言又止。
“什么事?”
“夏神医……走了。”
哗啦——
少年一呆,不觉手上松力。握轮急转,牵线骤然纾解。纸鸢乘了风势,扶摇直上,似欲脱离而去。
啪!
那只手立刻握紧,用力大得指节泛白。牵线绷紧,纸鸢又被拽住。
少年遥望不语,一手扯线,慢慢缠回握轮。
“公子,夏神医是被人带走。”陈为偷瞧少年神色,小心开口,“慕容飞尘,她的旧友。”
“慕容飞尘。”少年缠回最后一圈线,手持纸鸢轻抚,喃喃道,“陈为,纸鸢因何会飞?”
“因为风势。”
“那会随风而去,一去不回么?”
“不会。”
“为什么?”
“因为线在公子手中。”
少年笑了,轻晃手中纸鸢,像在宣告:“所以,还是我的。风势再大,还是我的。”
说完,他转身离开。行经树畔,柳丝一阵随风,飘摇扫过肩头。少年忽然停下,抬手折了一根柳条,扔在地上,气呼呼道:“我讨厌风,这些东西若再乱动,统统给我伐了!”
“是。”
迷迭谷,丛林叠翠。
奇花异草,溪流潺潺,像个世外桃源。纵有万种思虑,一入幽谷,似都随风淡了。可惜,却有一种例外。
夏云依正在厨房发呆。
视线越过窗台,盯着篱笆上的藤,眼也不眨,好似藤上绽出朵天山雪莲。
啪嗒啪嗒——
一阵微响,锅开了。她回神,揭起盖子。热气蒸上来,菌菇在汤里翻滚。
视线又定在沸汤上,她再次神游。双手却自动自发,舀了匙盐,加入汤内搅匀。
哗啦——
忽然,一股水从旁倾下。滚沸止了,汤水顿涨,半锅成了一锅。
她吓一跳,回头愕然:“……慕容?”
“唉,云依,我在你身后看半天了。”慕容飞尘放下水罐,苦笑无奈,“这锅汤,你已加了四次盐。我虽然不爱吃清淡的食物,却还不想被你做的饭菜咸死。”
“慕容……”
“云依,你回来半月,日日发呆。煮饭不是忘记加盐,就是反复加盐。看来,我当真惹人嫌了,你也如此对我。”慕容飞尘越说越沮丧,更带几分不甘。
“慕容,我没有……”夏云依垂头不语。
书房静悄悄。
她望着书案,愣了。
“慕容,这是……”
是她的行囊。如今打叠整齐,摆在面前,像正等着她,等她一起离开。
“云依,明日,你还是和那些你想挂心的人好好道别吧。”慕容飞尘开口了,波澜不惊。
她抬眸。
慕容飞尘却已背过身,临窗而立,清风入户,吹起他衣衫飘荡。
“慕容,我……”她抿抿嘴,有些鼻酸。
凉城天高云淡。
夏云依坐在小茶肆,轻轻抿茶。
“不许进来,出去出去!”旁边忽然一声。
她转头望去。
茶肆伙计提着壶,走向门口,手中抹布直挥,像在驱赶苍蝇。
门口并没苍蝇,只有一个小男孩,很脏的男孩。
男孩缩着头,袖着手,倚在门框上,无精打采。直到伙计走近,才懒懒抬了下眼皮,瞥一眼,又耷拉回去,像瞧见只苍蝇。
“咦?小要饭的,装什么大爷?!”伙计恼了,一伸手,去揪那只小耳朵,“你小子聋了?滚一边儿去!”
他揪了个空。
男孩像条小泥鳅,一下滑开,跑出几步停住,摇着小脑袋喃喃:“这年头,人心不古,不古啊。”
伙计呆了呆,半晌,才狠啐一口:“呸!小要饭的,还学人掉文?瞧那腌臜样儿,揍你脏了大爷的手!”
男孩却没理他,已走远了。
伙计又啐一口,转过身,满脸堆笑:“姑娘,您再续点儿水不?姑……”笑容僵住,他瞪着空桌发愣。桌上半盏残茶,两枚铜钱,方才喝茶的姑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