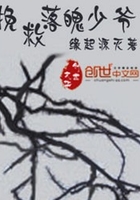静夜中,谢宜章一身煞气,眼神冰寒。
“你是谁?”他盯着对面,缓缓开口,“方才一击,我用了十成力道,却仍被震退三步。有此能耐者,天启上下不过七八个人。这种高手甘为驱策,墨言,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是谁都不重要。”墨言并不回答,淡淡道,“太子殿下,我在此等候多时了。”
“你还真自大。”谢宜章挑眉,冷然道,“你怎知我一定会来?”
“你当然会来。因为,你是她最好的朋友,必然要为她出气,找我这个不值得她付出的人算账。”
“你倒明白得很!”谢宜章不由切齿,恨恨瞪着对面,“墨言,我虽不明你的底细,但我知道,你必有能耐带她远走,逃离官府追缉。”
“不错,我可以。”
“那她昨夜前来,你为何任她离去?”
“太子殿下认为,我该如何?”
“当然带她离开舜香国,从此远走!”
“然后呢?”
“然后?”
“然后,隐姓埋名,就此江湖飘摇。天地之大,却再不能俯仰其间。如此终其一生,她会快乐吗?”
谢宜章不禁一怔,呆了半晌,竟无言可对。
“我不希望她将来如此。”他目光及远,带着温柔眷恋,轻缓的声音似在自语,“我想和她一起,陪她悠游天地间,一起开心,一起逍遥。所以,此刻她还不能走,仍要留下。留在这里,将往事加诸于她的无形重枷,尽数卸掉。只有如此,她才能束缚尽去。”
微风回旋,拂起他白衣飘然。满园沉静中,夜色越来越淡。
“你说得轻巧。”谢宜章忽然开口,声音冰冷依旧,煞气却消散了大半,“往事加诸于她的,何止仇恨?眼下她是重犯,罪在不赦,只此一件,便万难摆脱了,还说什么尽数卸掉!”
他恍若未闻,自顾道:“太子殿下,你手下颇多,可有那幕后之人的端倪么?”
谢宜章闻言,不由蹙眉:“那人是谁,不难推测,只是……”
“苦无证据?”
“是。此等大罪,若无铁证如山,绝难握住胜算。”
“这也不奇。”他微哂,淡淡道,“二十年了,什么破绽都已弥补妥当。与其追溯旧日破绽,苦寻不得,不如逼他露出新的破绽。”
“怎么逼?”
他不答,却探手袖内,取出一页信笺,颔首道:“还请太子殿下成全。”
陈为接了信笺,上前递出。
谢宜章一览而过,眼越睁越大,猛地抬头:“你……究竟是什么人?”
他笑了笑,轻轻歪头,像个孩子天真佻皮:“我的故事,只讲给一个人听。”
谢宜章气结,瞪他一眼,将信笺收好,哼道:“但愿那个人,不会生气不听。”
叹了一口气,他旋身欲走。
“且慢。”陈为忽然开口,声音压抑着怒气,“如果,方才我不在侧,那一击,你会收手么?”
“不会。”谢宜章头也不回,断然道,“云依若有不测,我难容他逍遥独活!”
陈为怒火冲天,正欲发作。
扑哧——旁边的少年却笑了,莞尔道:“难怪人言,太子殿下表面温和,实则煞气逼人。她得友如此,我实在欣慰。”
暗夜退去,晨光破晓,整个凉城慢慢苏醒。新的一天,似与往常并无不同。
城主立在府外,对天长出口气。
终于送走了,那个烫手山芋,所幸没出意外。深吸口气,还好,像这种棘手大案,自有三司推事,轮不到他。再吸口气,京官儿不易做啊,放眼一望,哪个不比自己官大?能脱一事是一事,方为明智之人。
他耸耸肩,挥着袖子,摇头晃脑回去了。
偌大的堂上,安静肃穆。夏云依跪在下面,目光扫过上座三人。
那样的官服气度,一看即知身居高位,她果然是个要犯,如此劳师动众。
视线落在右边的官员脸上,她不觉一愣。这个人,她见过。
当日凤凰楼上,雅间湘帘半卷,里面那个白衣折扇的少年,此刻身着官服,正在上面端坐,也正打量着她。
是……傅雪明。她忆起谢宜章淡漠的脸,是刑部尚书。
“两位大人,人犯昨夜被捕,于城主府严密拘禁,一早移送三司,还未进行搜查。”傅雪明悠悠开口,随和温吞,倒像在论家常,“不如,先搜人犯,看看是否存有证据?”
这话真傻,什么天启建朝最年轻的刑部尚书,浪得虚名,草包一个!大理寺卿暗自撇嘴,对这个小自己两旬的尚书,越发鄙夷。不过正好,有这草包在,出了篓子让他兜着,可保自己无过。
于是,大理寺卿严肃发话,老脸一副赞许:“傅大人所言甚是。”
“甚是,甚是。”御史中丞也在附和,笑出满眼皱纹。年轻就是好啊,无知无畏,敢说话。这是多大的案子!要担多大的干系!一个不妥,乌纱不保。他还怕另外二人也像自己一样,打定主意不先开口,那就有些麻烦了。还好,还好,有个毛头小子犯傻。
“既然二位大人赞同,来人!”傅雪明点点头,依旧温和,“搜人犯。”
搜查很快结束,因为,人犯身无长物,除了一块飞刀。
傅雪明接过飞刀,垂眸细看。举动间,袍袖微卷,露出腕上几道青紫。他不着痕迹轻舒袖口,遮盖起来。
昨夜被人拍醒,看见床畔红衣独立,他就知道,麻烦来了。
那人不由分说,嘱他一条‘妙计’。
记得当时,他刚蹙眉,想说此事有待商榷,手腕就被捏出几道青印。唉,真是好人难当,好上司就更难当。那人到底明不明白,自己好歹是个尚书,多少留些面子啊。
盯着手上飞刀,他目光凝在一点。‘妙计’说,飞刀顶端,右边第二朵祥云,按下去,可阻三司推事,保人犯暂押一时。
真是扯淡,莫非一按下去,会冒出观音菩萨?他想笑,可着实笑不出来。目光聚在祥云浮雕,他很有种被逼上悬崖的感觉。
事已至此,按与不按都已站在崖边。他不动声色,将飞刀翻来覆去,指尖暗中使力。
喀啪!
一声轻响,飞刀忽然裂纹,正反两面弹开,露出内中镂空。整个飞刀就像精巧绝伦的锁柜,瞬间开启,里面金光一闪。
“那是什么?”
大理寺卿探过头,御史中丞也探过头。有机关,就有秘密。有秘密,就有突破口。三个人,六只眼,目光汇聚一点。
飞刀中空,内嵌另一块牌,一块黄金打造的牌,中央镌刻阳文的‘赦’,其下两行小字:卿恕九死,永不加责。
刹那,六只眼都瞪大了。不知是谁,先漏了声音。
“……免死金牌?!”
二十年前,先帝抱病,垂危时,曾命特制金牌一块。长十八分,宽十二分,厚二分,其上镌‘赦’,下刻八字。制成后,这块金牌却从未现世,没人知道它的去向,甚至怀疑,它是否真的存在。
三人面面相觑。
谁也想不到,二十年后,这块金牌突然出现,出现在一个钦命要犯身上。
堂上震惊,堂下更惊。
夏云依睁大眼,几乎怀疑自己做梦。这飞刀是她随身之物,上面每一条纹理,她都熟记在心。竟然别有机关?怎么回事?怎么可能!
三司推事还未开始,即告中断。
人犯暂押天牢,三位主审匆忙入宫,带去震动朝野的消息。
凉城的天空,与往常并无不同,却为一个横空出世的意外,隐隐起了风云。
风奇云诡中,城东别院宁静依旧。
晨光斜入书房,窗棂格子滤了光影,投在窗边的月白衣襟上,落下一片斑驳。修长十指迎着窗影,正轻轻摩挲手中物件。
那是一块飞刀。顶端雕刻瑞兽,四周围绕祥云,黝黑光滑,每一道纹理都很柔和,似曾被人细心摩挲了多年。
此刻,摩挲它的是个少年,指尖流连反复,眸光脉脉低垂,仿佛在瞧心上人,眉目间无限温柔。
“唉——”旁边一声叹,书案后的男子站起,来到少年身侧,蹙眉道,“墨言,从昨夜到现在,你都没吃东西。看能看得饱么?多少吃一点吧。”
墨言摇摇头,凝目不移,喃喃道:“是呢,从昨夜到现在,她一定没吃东西。虽然暂时无法见面,我也要和她做伴。”说着,他垂眸浅笑:“表哥,我等她回来一起吃。她爱吃桂花糕,还有,不要做得太甜。”
“知道了。”男子无奈,又折回书案,却仍有些担心,“墨言,金牌一出,震动非小。你这次弄得大了,可好善后么?”
“无妨。”他笑笑,浑不在意,“这是唯一办法。一石激起千层浪,投石不大,激浪不高,就难惊起下面的鱼。至于善后……”一顿,他笑得懒散,眼底抹过难以察觉的复杂:“皇朝乃是谢氏天下,都是那个人的。如何善后,与我无关。”
男子闻言,似叹了口气,默然不语。
二人各自独坐。流光无声,惟余一室沉静。
较之此处的沉静,朝堂已是风云迭起。一名要犯,一面金牌,搅乱了整个早朝。
数番辨识争论,参详了无数文献。免死金牌是真?是假?谁也不敢妄断。满朝文武,数十道目光,都集中于丹墀之上,等待当今天子一言定论。
“这个……”龙椅上,皇上开口了,神色只有为难,却没半点威严,“这个,急切难辨。不如今日暂缓,众卿下朝后,各自思量周详,明日早朝再议。”
一句话,耗时许久的朝议,无果而终。百官叩拜退下,在这场叵测风云里,各怀心思。
人心浮动中,一天眨眼即过。夜幕降临,似将无形的躁动压入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