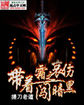转眼到了约定来接人的日子。
前一夜里,马晓南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摊煎饼,无法入眠。想着吕掌柜的话,深觉这一去前途叵测。她要去的可不是寻常高门大院,那是侯府啊,一入侯门深似海这话不会是无凭无据随口说的。再加上吕掌柜还说了,王侯鲜少与低贱商贾结亲,有这样的背景,更加去不得了。
踌躇一夜,直想到天边擦白。
马晓南看了眼窗外的天色,觉得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管它三七二十一,先跑了再说,总好过在这坐以待毙!于是起身将一身换洗衣裳,还有平日用的汗巾、木梳之类的小玩意一股脑打了个包袱,又从枕后翻出半袋油纸裹的桃仁小饼也塞进那包袱里。自从来了这儿养成的习惯,身边总要留些适合保存不易变质的吃食,谨防哪天再出了什么意外饿着肚子,现下倒还真的是有备无患了。做完这些,最后将铜钱银票细细分了,放在不同的口袋里。
收拾停当之后将房门错了个缝,从中一窥,见前院已经有伙计上工在做扫洒之事了,看来前门不方便走。后门常日里如若不是送柴米蔬果的过来,都是落着锁的,她没有钥匙。
不过这也难不倒她,后院墙角里有颗合抱粗的老樱桃树,枝桠伸出院外几许,又极易攀爬。马晓南瞅着个无人瞧见的时间,悄么向那樱桃树走去。
此时正值极好的人间四月天,樱花挤满枝头,晨曦一缕暖阳斜照,一树的娇俏柔嫩。
马晓南爬上树去,扒拉着枝杈挪近了,终于骑上墙头。抬眼望见吕掌柜居住的正屋,忽然想到自己这么走了,会不会叫沈晏为难他老人家,一时间架在那羞愧不已。
晃神间有人足底一蹬,两臂架上墙头,挺大声问:“马先生,你在作甚呢?”
马晓南慌忙低头,冲着来人以指抵唇,“嘘~小点声儿。”
“哦~,小声儿点。”王铁棒学着她说话的样子,只出气声不发喉音,并做了然状点了点头。
这俩人一对上眼,瞬间愕然,马晓南眼睛又睁的圆了几分,心中纳闷,便问:“你怎么也在这?”
王铁棒扮作忠实粉丝暗中保护马晓南已有些时日了,对她的脾气性格摸了个大概,知道这小主子心大神经粗,小事上头从来不钻牛角尖,极易相处,于情感上早将她当做了自家妹子,便没及时答,反道:“你先下来再说,上边危险。”
马晓南应了,反过身将另外一脚垂出去,扒着墙头一点点将身子放下来,却因这未完全长成的五短身材,没敢直接撒手,背着脸小声道:“你接着我点。”
咚的一声落了地,一点缓冲也无,脚心震的又麻又疼,自是站不稳,摔了个四脚朝天。樱花抖落一地,像袖珍人民币似的飘了她一身。
马晓南窘迫的从地上爬起来,一拍褂子,回身给了王铁棒一记白眼。王铁棒也不解释那些男女授受不亲的大道理,只低头笑了笑。瞥见她臂上包袱,便上前来问:“马先生这是要上哪去?”
马晓南对他比较信赖,想了想自己没有可去之处,不知怎样才能叫人找不到她,又能在那处生活下去,于是心念一动,仰头问他:“铁棒哥,不知可否给我指一条远走他乡之路?”
铁棒听了想笑,感情这丫头还没折腾够呢。若是叫她知道自己今日奉了命,晚些时候要送她回侯府,怕她就要着急跳脚了。当下也不急着劝阻,只道:“路是有的,只怕您这身打扮,认得的人不少,不如咱们先去寻个早饭摊子,美美将肚子填饱了,待那成衣铺子开门,您先换套行头再说。”
马晓南听他说的在理,自己近日确有声名鹊起之势,若就这样出去,难免落人耳目,想了想便答应了。只是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不祥的第六感隐隐作祟,总觉得哪不对劲,可又想不出什么,于是一切便堪堪上了王铁棒筹谋的轨道。
一顿稀饭包子油馍头吃完,东大街上林林总总的铺面多半也做起了生意。这回逛街有熟门熟路的王铁棒引着,再不用怕挨宰了。将她送进一家口碑好的成衣铺,王铁棒打了个幌子,说顺道办点家事,让她好生挑着,自己回身又去了一趟大食铺子,将事情的原委隐去细节同吕掌柜交代了,叫他放心,这才又回来寻马晓南。
此刻马晓南已选好了一身新衣裳,恰好此间当掌的是个妇人,领着她去里间换了。待她出来,俏生生立在堂中问王铁棒:“穿成这样合适么?”
薄袄换作夹衣之后没了那份鼓囊囊的感觉,身量随着腰间收敛显得拔高了不少,秋葵色的袖衫紧窄贴合,靛青的素面半臂收入底下轻灵利索的水云纹百褶裙中,若是避开那奇怪的包子头不看,这模样真是和从前判若两人。虽是寻常衣料,可颜色质地撞的巧妙,同一般女子喜欢的浑身丁香色或一身葱绿比起来,倒更显得人活泼喜人却又不失端庄。
王铁棒细品一番这女子衣裳的学问,心道这打扮也算像样,便投去一个赞赏的眼神道:“好。”
“那我现下是不是可以走了?”马晓南喜道。
王铁棒敛住神色,想着今后马姑娘回了她该去的地方,主子不知道会给他派什么别的差事,怕是再也听不到她的平话段子了,一时唏嘘,“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让我送你去吧。”
听了这话,马晓南也不免沾了伤怀之感,心里默默合计着,不管以后去了哪,也得尽快将脚跟立稳了,好找机会回来看看吕掌柜和铁棒大哥是否一切安好。默然片刻,重新仰起头笑着说:“那我们这就走吧。放心,青山不改绿水常流,有机会一定回来看你们。”说罢还抚慰的拍拍铁棒臂膀。
王铁棒大窘,不敢再多演下去,领了马晓南徒步向逸南侯府的方向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