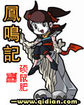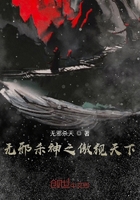涂苒听见他笑,心里却觉得不妙,两人隔得太近,她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心跳以及胸腔的微微振动,他的声音既低沉又温柔,顺着呼吸从嗓子眼带出来,夹杂了懒散的鼻音。就是这种氛围最容易让人迷失,而她的意志薄弱,偏巧他的手渐渐划过她的肚子,还一个劲儿的往上移。
涂苒心里一跳,有些慌神,抓住他的手腕脱口说道:“我饿了,很饿。”
陆程禹停下动作,问:“你想吃什么?”
她想了想:“冰箱里好像还有超市里买的速冻馄饨,你帮我煮点儿吧。”
陆程禹稍微静了静,起身下床。他在厨房的冰箱里翻了一遍,没看见,于是说:“没有,可能已经吃完了,要不煮面条给你吃?”
涂苒在卧室里大声应着:“不要,我想吃薯条和汉堡,你帮我去买。”
陆程禹走过来站在门口:“那玩意儿怎么能吃,里头尽是防腐剂,随便搁几个星期都不会坏。”
涂苒说:“你就是懒得出去买。”
陆程禹说:“除了这些,你再说一个。”
涂苒又想:“饺子吧,最好是那种汤料又酸又辣的,家里没有,超市关了门,想吃也没得卖。”
陆程禹披上件衣服,转身进了厨房。
涂苒躺床上等了半天也不见吃的东西端过来,心里不耐烦。
她这会儿倒是真的饿了,孕中期,她的胃口又变得不如以前,一到吃饭的时间,就觉着胃那里顶着难受,才吃几口就搁下筷子,到了夜里就饿得厉害,觉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眼前浮现的尽是叫人大块朵颐的美食佳肴。她实在耐不住性子,起身去厨房里瞧,却见那家伙正在擀面皮,旁边搁着一碗才调好的馅。
陆程禹见她来了,就说:“你先去睡会儿,好了我叫你,家里没肉馅,炸了点鸡蛋和豆腐皮,今天先将就着吃点儿。”
涂苒饿得发晕:“你存心的,就想饿着我,等你做好我都快饿死了。”
陆程禹手里的动作越发的快:“马上就好,我先煮几个你吃着,剩下的我包好放冰箱里。”
涂苒心烦,转身就走:“不吃了,现在不想吃饺子了。”
陆程禹问:“你又想吃什么?”
涂苒躺回床上:“包子,酱肉馅的大包子,你会做吗?”没听见陆程禹搭腔,她就合上眼睛睡去,居然就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就被人从床上拽起来,手里给塞了只热热的碗,听见那人说“慢点儿,还有点烫。”
她胡乱吃了几个饺子,既嫌汤料不够辣,又烦他好好地把自己吵醒,发了几句牢骚,倒头要睡,又被他拽过去刷牙。她那时一直迷迷瞪瞪的,心情也不好,王伟荔正好回家,推门瞧见他俩,奇怪的问了句:“怎么还没睡呢?”
涂苒没头没脑地答道:“你们这些人真讨厌,”然后爬回床上,一觉睡到大天光。
第二天早上起来,陆程禹已经上班去了,王伟荔蒸了几个包子拿来给她尝:“你老公昨天给你做的,那孩子忙到晚上一两点才睡,一大早又跑去上班。我看他做事挺利索的,问他怎么会这些,他说是他妈以前教的……到底不是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孩子,可比我们家涂峦能干多了,”末了又重复一遍,“小陆他昨晚俩点才睡,就在沙发上歪了几个钟头。”
涂苒说:“他那是为了他孩子,要不就是做给您看的。”
王伟荔斜她一眼:“竟胡说,有那个必要吗?再说了,他孩子还不是你孩子,哪有跟自己孩子计较的。”
涂苒哼道:“反正他脑抽了。”
陆程禹仍是隔三差五的过来看她,有时候是隔了一周,来了之后后照例先做自己的事情,晚上也不走,和她一起挤在小床上睡觉。
涂苒有时候心情不好,就踢他下去,赶他去客厅,他也不说什么,性格似乎讨人喜欢了许多。
又有一次,三人一起吃晚饭,她忽然发现他的下巴颏变尖了,像是消瘦了不少,王伟荔也使劲往女婿碗里夹菜,说这孩子每天东奔西跑的累坏了,得多吃点补充营养。
涂苒也就不忍心再折腾他,等他晚上钻进被子,也不赶他走了。
又是一夜相安无事,她早已习惯面向另一边侧卧着入眠,他就从身后轻轻拥着她,只把手轻轻搁在她的肚子上。
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床边空着,他已经走了。
她觉得自己像是做了回梦,而梦境总是虚幻得过分,所以那一切都不必去探究,也不必去相信。
过了几天,快递送了一个大纸箱,她打开一看,是台黑漆漆的崭新的十七寸笔记本电脑,从大小到颜色外观,无不体现了男性化的阳刚风格。
陆程禹后来打电话问她:“东西收到没?喜欢吗?”
她直接答:“不喜欢,太大,颜色很难看。你买给自己用的吧?”
陆程禹说:“要那种花里胡哨的做什么,这种就很好,性能好。”
涂苒没理会,反倒说:“我问你,你就是想买台电脑放在这儿给你自己用的是吧?然后还说是给我买的,想让我领你这个人情。”
陆程禹似乎有点不爽:“随你,爱用不用。”
涂苒径直挂了电话。
她早有购置笔记本的打算,之前看中一款朱光红十四寸的索尼,可是陆程禹先她一步给买了,她总不能再花一次钱。购物的愿望被人强行压制了去,所以每当她看见那台大黑,就从心里更讨厌了他几分,没有一点惊喜或者感激。
她觉得这样很好。
陆程禹再次见到李初夏,是她婚礼之后的第二个星期。
上周里,他的耳朵快要被“马尔代夫”这个地名磨出老茧,全缘于李院长的女婿,也就是科室里的一位同事和新婚妻子一起前往那片美丽海域共度蜜月。
几位护士和年轻医生闲来无事偶尔八卦,闪烁其辞的表示,男人找老婆和女人找老公一般无二,干得好不如娶得好。据说那位同事家境普通,老家在某地级市下面的乡镇,父母是工厂职工,全凭他本人艰苦奋斗才有了如今的境况,继而在众人间脱颖而出,最终得到李初夏的青睐,当然这两人能走到一起也是经过李初夏同家庭抗争的结果,李家初时并不赞成,关于这一点任何人都表示可以理解。
那天,陆程禹抽了点时间去食堂吃午饭,回来后在住院部底层等电梯。
若是按照以往的习惯,他多半是取道楼梯一气儿爬上去当做锻炼身体,但是那会儿却鬼使神差的跟着前面几人一同跨入电梯间。他前脚才迈进去,就听见后面有人小跑着过来,嘴里轻言细语:“麻烦您请等一下。”
他伸手按住即将合上的门,回头瞧了眼,瞧见了李初夏。
她似乎变了些,以前清汤挂面的长发如今烫成蓬松微卷,多了几分新婚少妇的喜庆。
李初夏看见他不觉微微一愣,似乎踌躇了数秒,之后步入电梯,一言不发。
电梯才到二楼,身后的闲杂人等都鱼贯而出,狭小的密室里只剩下两人。
没人不觉得尴尬。
陆程禹想了想,仍是说:“恭喜你。”
李初夏没说话,半响才淡淡笑道:“恭喜我什么?”
说话的当口电梯猛然一顿,两人一起抬头看上面显示的数字,橙色光点不再移动,在“4”上面停滞许久,头顶灯光忽然闪烁,紧接着陷入一片漆黑,电梯往下晃了晃。
李初夏惊叫一声,就听见陆程禹说:“站到墙边去,抓紧扶杆,”他迅速把每一层楼的按键都按下,才道,“运气好,第二次碰上了。”
警铃和应急电话都不起作用,黑暗中,电梯里异常安静,李初夏心里扑通乱跳。
陆程禹掏出手机看了看,竟然还有信号,于是给外面的同事打过去。电梯里有了几丝光亮,照着身上的白大褂,两人像是被罩了层朦胧的影子。
陆程禹站在门边,讲完电话后仍是将手机按亮了,屏幕冲着外面,李初夏看见亮光,情绪也略微平复了些。陆程禹看向她:“没事儿,他们已经让人过来了。”
她“嗯”了一声,大着胆子向着光源挪过去,终于在他身旁站定。起初仍是扶着栏杆,过了一会儿电梯好像又有一次轻微的晃动,她没多想,抬手抓住了眼前男人的臂膀。
陆程禹似乎没动,既没抽回手,也不曾更进一步,他一句话也没说。
略等了会儿,两人听到外间的脚步声纷沓而至,有人冲他们大声喊:“电梯停电了,我们已经让人过来抢修,里面一共有几个人?”
“两个。”陆程禹问,“多久修好?”
那人说:“具体不清楚,旁边修房子把变压器掘坏了。你们里面的人要注意安全,不要乱掰门,不要自己出来。”
陆程禹说:“兄弟,我们要是能自己出来,早出来了。”
那人想明白先前的说辞有些问题,不由跟着笑了一声。
听这两人说得轻松,李初夏的心放下一半,现在又模模糊糊的希望,时间过慢一点才好。她腕上带了块浪琴手表,此刻,秒针滴答滴答走过的声响竟如震耳欲聋一般,她不自觉的低头看表,看得有些费劲,不太清楚。
陆程禹瞅了眼手机告诉她时间,两人接着话茬随意聊了几句,无非是工作相关。不知不觉中她手里空出来,他不着痕迹的稍稍往一旁挪了挪。
李初夏回过神,心里一阵紧缩,顿时默不作声。
眼前的光亮消失,手机电池已经耗空,立在黑暗里,身边只有对方轻轻地呼吸声。
不知过了多久,才听见外面有人喊:“里面的人注意,现在我们先试着把门撬开。”然后有听见外面乒乓作响,没多久明晃晃的光线从门缝里一点一点费力钻进来。
趁着光明驱逐所有黑暗之前,李初夏忽然低声问了句:“如果上次我没提出分手,我们……能走到最后吗?”
话音刚落,电梯门被人哐啷一声使劲撬开,外间众人甩掉手中的器械,一阵纷扰的埋怨欢呼或者感慨。
在各种嘈杂的声响里,她听见了答案。
他在她身后说出了答案,李初夏眼里稍许湿润,在午间强烈的阳光中,她不禁轻轻捂住眼睛。
外面早有人伸手过来,将她拉了出去,身上的白大褂蹭上门口的灰尘,在膝盖处留下两道黑色印迹,她弯腰拍落尘土,再直起身来时,他正往楼上去,不多时,熟悉的背影消失在楼梯的拐角处。
傍晚下班,陆程禹开车过江。
夜间,他在电脑上修改论文,msn弹出一个窗口,是雷远发来的信息,让他接收文件。陆程禹也没细看,直接点了“接收”,传送完成后,屏幕中间跳出一幅照片,是李初夏在喜宴上的单人照,身着红色露肩长裙,裙摆曳地,袅袅婷婷,很漂亮。
他看了一眼,即时关掉。
正好涂苒从他身后走过,好似看见了,又像没看见,她一言不发,走到床边踢掉鞋子,安静的躺进被褥里。
陆程禹又琢磨了一会儿论文,这才合上笔记本。
等他上床以后,她还没睡着,两人身体一有接触,她就慢慢转向另一侧。他试探着从身后轻轻拥着她,她也并不推却。就这样躺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今天被关电梯里了,关了快一个小时。”
涂苒应了一声,问:“当时害怕吗?”
他不答,只道:“以后你也少搭电梯,适当爬楼梯锻炼身体,万一被困在里头了还是挺危险的。”
涂苒又应了一声,不再说话。一室安静,两人渐渐睡去。
大晚上的,雷远呆家里很无聊,于是给陆程禹发了照片捉弄他,不想这小子没半点反应,话也没回一个。
雷远越发无聊了,就想给前不久才交往的小女朋友打个电话瞎聊聊,号码拨了出去,又迅速按掉。
这位女朋友仍是二十出头,他有时候不爱同大龄女性神交,总觉得她们心里弯弯绕绕太多,过往也不甚清楚,如果不是太喜欢,接触起来会有难度,总会相互间防着些什么,没有谈恋爱的劲头。
他这位新女友还不错,一切都新鲜,主张及时行乐过了今天不想明天。
唯一不好的是太有活力,晚上不睡,老约些狐朋狗友流连夜店,白天还能照常上学上班。
雷远跟着她着实疯狂了几天,过得很恣意,时间长了却是吃不消,精力跟不上,隔天早晨躺在床上起不来,跟吸过毒一样没精打采,大脑犯抽,最后只得长叹一声,到底是年纪不饶人。
另一方面,越放纵越空虚,渐渐也起了腻味,又想回复正常的轨道,偶尔走在路上,看见和自己差不年纪的小夫妻带个孩子,或说笑,或斗嘴,或行色匆匆,忽而觉得,这才是人过的日子,这才叫生活。
雷远不由自己地想起了苏沫,好奇她最近过得如何,孩子谁给带着,复合了还是离婚了?他想来想去又掏出了手机,再看时间,夜里十一点,他对着屏幕发了会儿呆,把手机搁回桌上。
过了几天,他碰巧去苏沫家近旁办事,完事了又正好是下班的点,他把车泊在小区门口,吸了支烟以后,看见苏沫抱着孩子远远走过来。
她到了近旁,像是认出了他的车,又往这边瞧了两眼。
雷远摇下车门:“嗨,挺巧的。”
苏沫问他:“你怎么在这儿?”
雷远答:“我才在这里办完事,正要走。”
苏沫点点头:“那我先上楼了,”她肩上挎着大包,臂弯里抱着孩子,一条胳膊上还吊着只医院里装药的白色塑料袋。
雷远开门下车:“孩子又病啦……这么多东西,我送你上去。”
苏沫也是累的够呛,稍微推辞两句,把肩上的大包递过来:“又麻烦你,这小家伙真是折腾人,感染了什么轮状病毒,上吐下泻,才从医院挂完水回来。”
雷远没去拿包,倒是接过孩子抱在怀里。
小孩儿昏昏欲睡,哭了几声以后趴在他的肩上休憩。
苏沫又叹气:“我待会儿还得把家里的玩具,她用的东西全部消毒,她只要一生病,我就脱不开身。”
雷远问她:“你上班怎么带孩子?还送幼儿园?”
苏沫摇头:“我妈来了,帮我看着,她才买菜去了。”
隔了半天,雷远忍不住问:“家里人知道了?怎么说?”
苏沫苦笑:“还能怎么说,现在是人家不要我,就算不同意,也没什么好说的。”
雷远没吭声,抱着孩子径直往前走,上楼的时候想是略颠簸了些,那孩子就呕起来,张嘴往他肩头吐了几口奶腥味的东西。
苏沫伸手去拍孩子的屁股,忍不住骂她:“讨厌死了,一老生病,又把叔叔的衣服弄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