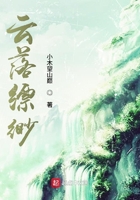傍晚时分,日薄西山。天空如同一张泛黄的旧纸卷,任凭余晖用最随意的笔锋勾勒出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面。夕阳之下,地平线的尽头,黄沙四起,一人一骑像是被红日从腹中吐出一般。随着马上骑士身形愈来愈近,隐隐可见其俊俏面容和华丽衣着,显然非富即贵。又见三人三骑紧随其后,皆是黑甲黑马,手中白芒闪烁不定,杀气森森,仿佛要将前方那公子吞噬。
双方马力充沛,在黄尘路上风驰电掣,展开了一场追逐。日渐西沉,气温骤降,冷风四起,似有一双双无形之手将路旁的竹林中的修竹摇得沙沙作响。马蹄声声,正当那公子纵马掠过、三骑紧追不舍之际,林中笛声大作,又听一声鹤戾自平地急转直上冲破云霄,竹叶霎时化作万千暗器,皆似活物一般朝后三骑闪电般刺去。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马上三名黑甲士齐齐自马上一跃而起,聚拢在空中,而三道白芒也化三为一,就在竹叶逼近那刹那,空气扭曲了起来,三人同时消失不见。
笛声一抖,吹笛者似乎心神不定。随后笛声戛然而止,竹枝唰唰四下分开,一条白影掠空而行,朝马上狂奔的那公子飞去。但人未到,前方空气再度扭曲,三条黑影交织着从虚空中俯冲直下,如三道死亡之影盘旋在那公子头顶上。
马驻,人静,斜阳下,好似一座雕像。三道黑影化作三缕淡淡黑烟,竟无声无息地在空气中蒸发不见。白衣轻轻落在马侧,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他半晌不语,终究还是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当”的一声,一块晶莹剔透的玉佩自马上公子的衣角碎成两半滑落在地,玉佩上面那残缺的云龙图案正映着余辉,折射出鬼魅的光线。
###########
夜沉如水,月如钩。老吴坐在书案前,一油灯、一方砚台、一支狼毫以及一张只字未动的白纸静静地摆在眼前。
他几度提笔,又几度放下,终究叹了口气,眉目间布满愁云。
他时任龙骧城捕头也有二十三个年头了,没几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先是昨晚城西一家五口被残忍杀害,年仅五岁的男童不知所踪;离案发处不远的一间酒铺外两名当差的衙役也惨死街头,杀害手法与死去的一家极为相似;本以为事情便暂告段落,却不想今日夜间有人发现了城外竹林小道上的尸首。
三处命案,凭他二十几年的查案经验竟毫无头绪。油灯眼看要燃尽,火苗忽闪忽闪地跳动起来。老吴呆呆地望着火光,忽然想起一个人来。
“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但尸体会。”十几年前,那个林间小屋前升起的火堆旁,老吴记住了那双透着淡淡倦意的大眼睛。
第二天的清晨,天空刚露出鱼肚白,老吴便早早起来了。他匆匆换上官服,带上佩刀,随意洗漱了一下便往城外去了。守城的卫兵与他是多年相识,私下开了城门放了行。之后,他一路向北,行了约五里路程,来到一片树木参天的林前。
林中一条小径直通后面的柴居山,满山上下都是大大小小的土包,龙骧百姓世代的祖坟便安静地坐落着。在山脚的路口,简单地搭着两个一大一小的茅草屋,这便是守墓人的家。
此时,老吴大口喘着粗气立在近前,不由地想起往事来。从第一次见到那个孩子起,十几年里他总共来过四次:
最早的那年,老吴因公事来访。初见时,那男孩紧紧地依偎在守墓老人的怀里,眼神有些痴呆,像是忘记了一些东西似的;老人半生无子,多了个孩子后竟笑得合不拢嘴。那时,这里只有一个半新的小茅屋。
第二次来时,日子已经过了六年。守墓老人鬓角的白发多了许多,脸上的皱纹也深得更厉害。来时是隆冬时节,老人当时生着病,那个孩子鼻子上挂着一大条浊青的鼻涕,认真地帮老人吹着碗里热气腾腾的药汤。那时,茅屋上的茅草少了许多,不知是否被八月怒号的秋风卷上了天。
第三次到这里是四年前,那天是个大晴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远远便听见老人孩童般的笑声,待老吴走近时,屋门开了,走出一个身体壮实的少年。少年只穿着件灰布短打,袒着胸膛,露出腹部精练的八块肌。少年脸上挂着笑,见到老吴的时候目光呆了呆,依稀让老吴回想起初遇时的眼神;随即他便灿烂地迎了上来。那年,茅屋比原来已经大了一倍。
最近一次便是今天。老吴百感交集之际,小茅屋的门“嘎吱”一声打开了,一个虎狼般的青年走了出来。他简单地打了个头扎,棱角分明的下巴上点缀着些胡须,勾勒出浅浅的络腮胡形状;穿着件打满补丁的褪色的蓝衣,袖口高高挽起;全身上下透着一股野兽般的活力。他抬起头来望向老吴,那眼神一如从前,透着一种难以明说的倦意。林明珏,一个微末而普通的人,却有着这样一个动听的名字。
“吴伯早。”青年笑容有些僵硬,或许见过了太多的死人,再笑起来难免有些勉强。
“明珏啊,你爷爷还好吗?”老吴用袖口擦了擦鬓角滚下的汗珠。
“爷爷最近身体有些……”青年顿了顿,道,“可能是真的老了吧。吴伯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老吴挠了挠头,觉得有些难以启齿,“呃,你吴伯查案上遇到点麻烦,恐怕要你来搭把手。如果你没什么要紧事的话,现在能不能跟吴伯走一趟?”
“是不是又死人了啊?”青年话里透着淡淡的忧伤,他快步走到老吴身边,拍了拍肩膀,“吴伯,那我们还是快点去吧。”
两人赶回城中时,街上已经热闹了起来。城西的露天小酒馆和惨遭灭门的房子此刻仍被衙役们保护着现场,尸体虽然不在了,但行人依旧如避瘟疫般躲得远远的。老吴领着他先回衙门里检查了死者的尸首,林明珏沉默了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最后他要求回现场察看。
林明珏第一个来到了小酒馆的命案现场。由于老吴的存在,使得现场围观的百姓一下多了起来。林明珏弯下腰来,双眼紧紧地盯着一张桌子上浅浅的刀痕,轻轻地用手摸了摸。过了一天一夜,再想看出地上打斗的脚印已是不可能,但他仍然跪在地上不知在找些什么。
片刻后,他附在老吴耳边轻轻说道,声音里透着哀伤与疲倦:
“凶手看来并不是本地人,甚至不是正常人,这完全是头发了疯的野兽。”
话毕,林明珏的视线在周围的围观人群中扫过,最终停留在一个人的身上。
那人身材微胖,披着件粗布坎肩,里面穿着件灰黑色长衣,脚下踏着双破旧的草鞋,神色冷淡,仿佛稻田里驱赶麻雀的稻草人。林明珏看着他,他也望向了林明珏。五个呼吸过后,林明珏扭过头去,对老吴说道:
“吴伯,带我再去城外那处现场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