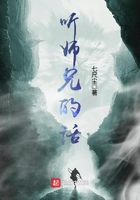蔡文花家几代以来阴盛阳衰,到了她这一代,衰的只剩一个独苗闺女,文花她娘刚性有主意,心想着要是这闺女嫁了出去,这一支就真绝户了。于是,暗下里给文花搜罗上门女婿。招女婿是个讲究学问的事儿,太强的人招不来,太弱的招了来也撑不起个家。眼看文花长到十八九岁,水灵灵胖嘟嘟,一碰就能挤出水来。十里八村上门提亲的不少,可一听要做上门女婿就都吓跑了。
苗德光是个走街串巷的小木匠,打十三四岁就跟着老师傅挨家挨户的修木器。师傅喊一声:木~器~。他就跟一声:修~木器。前年根儿上,老师傅没了,德光就一个人背着木器匣子挨村挨店的转悠:木~器~,修~木器。
苗德光早先跟在师傅身边,都当他还是个俊俏的小孩,师傅没了,自己单干这一年多,瞬间长成了个结实的大小伙子。上门做木器活时,小寡妇小媳妇的都偷偷给他木匣子里装干粮,大姑娘也忍不住给他抛媚眼。但德光木木的,跟那些木器一样。
文花她娘注意到了这个小木匠,三天两头的叫他进门来修木器。
“小木匠,你叫啥?”文花娘看着他那双粗糙又灵巧的手。
“德~德光,苗~德光。”小木匠不敢抬头,结巴着说。
“咱这十里八村的没有苗村,你咋就姓苗呢?”
“师傅,师傅姓苗。师傅不是这里人,师傅养了我,我就姓苗。”
“师傅没了你住哪?”
“师傅以前搭的棚子,就在三里外的瓜地里。”
文花娘听了,怜爱起这个小木匠,也中意起这个小女婿。
“大娘还有好些木器要修,晌午你就呆在这吃吧,大娘给你炒俩菜。”
“有,有吃的。”小木匠拍拍自己的木器匣子。
文花在里屋偷偷听着看着,把小木匠看到眼里,迷到心里,跟着他娘一起进了厨房。
“这个小木匠咋样?”
文花拿了面盆,使劲揉着面。
“招来给你做姑爷,咋样?”
文花揉好了面,拿起油瓶倒了小半瓶。
苗德光入赘到了蔡家,日子过得安稳祥和。木匠还是木木的天天鼓捣他那木匣子,老实巴交,从不多讲一句话,蔡文花也还安安稳稳的做她的小媳妇。但文花娘坐不住了,成婚第一年上,文花肚子没见动静,第二年没啥响动,第三年还是没怀上崽儿。蔡文花高挺着胸脯,圆滚滚的******,一看就是个能生能养的女人,问题要出就一定在那干瘦的木匠身上。
文花娘是个有主意的人,是个能说得出话做得了主的人。这日,木匠正在院子里打磨一根木棒,刨花在阳光里飞着,木棒越磨越细,越磨越圆。
“这棒棒真直啊。”
“嗯。”
“准能做把好家什儿。”
“嗯。”
“你们得有娃儿。”
“是。”
“可是三年了。”
“是。”
“我想办法了。”
“好。”
“大娘对不住你。”
“没。”
刨子一滑,在棒棒上刨出一个坑。木匠打量着棒棒,转身进了屋。
文花正在烧火,柴棒子又细又潮,烟大火小,呛得文花直流眼泪儿。文花娘从外面拖来两个大木杆子,填进灶膛,火一下旺起来。
“不是灶不行,是柴棒棒不行。”
“娘,你说啥?”
“咱家得有后。”
“娘,我也想。”
文花往灶膛里塞着大干棒,火呼呼的往里吸,烫的她脸通红。
“不是灶不行。”
“娘......”
“听娘的,咱家得有后。”
“我听娘的。”
早些年,求子都是婆婆带着儿媳妇到观音庙里过上一夜。文花娘本可以带着文花走个三五十里,到个谁都不知不识的地方。可她精明就在这里,要是到外地求个子,不管男女,都还是她蔡家的独苗,呆木匠撑不起这个家,以后还是受人欺负。不如就在这老庙里就地求子,蔡庙的小伙子们都知根知底,以后娃娃长起来他们也会明里暗里的帮衬,总不会受人的气了。
文花娘拿定主意,到老树下找了蔡老鬼。
“老鬼哥,我来求您个事。”
“哎呦,这四十几岁的小寡妇,还是水嫩嫩的一包油,咋养的?”
“老鬼,我跟你说正事儿。”
“文花爹没了十多年,看样子你是没亏着自己啊。”
“蔡老鬼,你这个下三滥的东西,好好跟你说话你就没个老人样。”
“我蔡老鬼这么多年过来,吃不着还不兴说说了?”
“你别满嘴放炮,正正经经的我跟你说正事儿。”
“你说,我听着呢。”
“文花三年没娃娃,得想办法。”
“我年纪大了,这事可帮不了。”
“你这个没脸皮的老怪,小辈儿的你也胡咧咧,真不是个人。”文花娘说着就上去撕他的嘴。
“唉唉,你别动手,咱说正事儿!”蔡老鬼躲到一边,理理胡子端坐起来。
“我都想好了,现在就让你做一件事,......”文花娘凑到老鬼耳边轻声说着。
蔡老鬼听完,瞪圆眼睛看着蔡文花:“嘿,真有你的,这能行?!”
“你就按我说的办,事成之后我给你说个大姑娘,让你也受受喜。”
“大姑娘咱受不起,光你就够我受活啦。”蔡老鬼说着,在文花娘身上捏了一把。
文花娘轻拍了老鬼一巴掌,扭着腰站起来,说:“跟你说正事儿的可别忘了!”
“嘿,这软乎乎的......忘不了。”老鬼吸溜吸溜的笑着。
十五的夜里月亮大的像个磨盘,照的地上明晃晃的,像是撒了一层白面。文花娘走到这白面里,喊着,文花你到屋里来,娘有话跟你说。文花从小木匠身上翻下来,披了件衣服,脸蛋红红的就跑了出来。
“种子不行,耕的再勤也发不了芽。”文花娘拿眼斜看着她,“该说的都跟你嘱咐过了,明夜里到老庙去睡。”
“娘,我怕。”
“怕啥,男人都一个样,都能让你受活,但别的男人不光让你受活,还能让你开花结果。”
文花被她娘说的脸热热的,身子也热热的。
“今夜里好生歇着身子,别耽误了大事儿。”
“嗯...”文花裹紧衣服,胸脯鼓鼓的凸出来,转身掩上们又走回到白面里。
蔡文花推门进去时,小木匠正在摆弄结婚时给娃娃预备下的木器物件,见她进来,忙慌藏起来。
“木匠,我对不起你。”
“没。怨我。睡吧。”
蔡文花脱光了自己,吹灯上了床,俯到木匠身上,抱紧了他。
木匠不是不能让文花受活,婚后俩人天天欢腾的翻江倒海、云里雾里,光受活不结果就是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没有内容的空欢喜,是不被允许的。
文花慢慢晃动身子,轻声唤着,小木匠浑身一紧,打了一个哆嗦,双手捂住脸,呜呜的哭了。蔡文花用胸口蹭着他,用两手抚着他,她想用自己所有的柔软,温暖身下这个受伤的小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