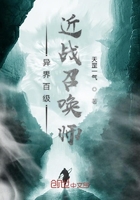凉州初春的夜里还是带了些微凉意。
李祥将炊事堋的挡门板乔了乔位置,确定关得严丝合缝了才回身跟着大家一起围坐在小火炉旁边。
蒋卓恩紧喝了几口热汤,驱了身上带着的夜里寒气,才捧着汤碗满足的呼出了一口气,边暖着小手边看向笑眯眯看着他们的老张头:“张大叔怎的不吃一碗?”
老张头见最乖巧的蒋卓恩这么一问,众人俱都抬头看了过来,心下又疼惜又满足,笑呵呵的揉了揉蒋卓恩的头顶:“你张大叔年纪大了,夜里吃多了积食,要睡不好的,大叔可不比你们这些壮小伙子,早不馋嘴啦。”说完又微抬了下巴示意众人继续吃汤。
二虎十三岁正是长身体又馋嘴的时候,低头猛灌了几口就撂了碗,抹着嘴对老张头说道:“改天我出营的时候再给您弄点好酒回来。”
李祥闻言就抬手拍了二虎的脑袋一下,笑道:“你小子别添乱了,上次居然明目张胆的扛了一大缸子就要往营里闯,要不是林副队正好撞见,帮着你遮掩了可有你好果子吃。张大叔的酒自有阿卓去料理,你少瞎操心!”二虎闻言微红了脸,不好意思的冲老张头笑了笑,也不反驳。
老张头看着他们几人笑闹,只觉得心都跟着暖了起来。
老张头原有个小儿子当年被分到了壁虎军,老张头便求了伐北大军伙夫房的头头,跟着壁虎军一起走了。金城一役他小儿子却战死了。李祥和马向文当时就是和老张头小儿子分到了一个阵营里的,自那之后,就常常没事找事的趁着领饭的时候围着老张头帮前帮后,老张头自知他们的用心,慢慢也放下了丧子之痛,将他们当成了自家孩子般照顾疼爱,有好料总紧着他们,一来二去,二虎连带着白术蒋卓恩也靠着和李祥马向文的关系和老张头熟识了起来。
蒋卓恩知老张头唯一的爱好就是喝几口小酒,但营内管得严,不能明目张胆的弄酒给老张头,便借了药酒的名头,打了白子泉的名号,隔段时间给老张头捎带那么一点,老张头也不是那莽撞的性子,受了蒋卓恩的好意,也只是偶尔和他们几个小子聚在一起的时候才喝那么一点点--总不能真惹出了事来反倒污了这几个好孩子的孝心。
待得大家伙喝完了汤吃完了肉,又围着老张头说了些白日里操练的趣事,老张头喝完了一小杯酒心里身上都舒畅,冲着做惯了后续收拾活计的蒋卓恩交待了两句,留了李祥几个在这里烤小火炉,便自行先回去睡了。
这边蒋卓恩起身将碗筷收了,舀了水洗干净收好,才坐回小火炉边听李祥几个讲话。
几个小子又不似那成过亲有了年纪的老兵,话题少不了女人,又都无家小亲人可念,便都只围着操练的话题讲,便说到了三个月后的季度考校。二虎才升到伍长,他身上无军功年纪又小,要再往上升就只能下狠功夫操练,便求李祥和马向文每日操练完再给他开小灶,少年人总是争强好胜的,希望能得到长官的肯定赞赏。
蒋卓恩和白术听得性起,也跟着拿二虎说笑,似模似样的要指点二虎,二虎哪里耐烦被他二人调侃,嘴上说不过就小打小闹了起来。
蒋卓恩只觉得每次和他们几个凑在一起的时光都美好无比--这可不就是闺蜜们的午夜茶时间么,不过是古代版的,还是男版的。蒋卓恩被自己这恶趣味的想法惊得抖了一抖。
一时间,这小小的只亮着个小火炉光的炊事堋里洋溢着低低而热闹的说笑声。
入夜了还不休息的,却不止蒋卓恩这几个做熟了的惯犯。
白子泉走到黎晰鸿的大帐近前,见大帐果然还亮着灯火,便让守在帐外的侍卫通传了一声,待听得黎晰鸿应声便撂帘入内。
黎晰鸿只抬眼示意其自己找地方坐,就继续皱着眉看着手中一封书信,白子泉现在看到书信就心烦,也不在乎黎晰鸿这冷淡态度,寻了椅子坐下,自己摸了茶壶倒水喝。
这几年相处下来,白子泉同黎晰鸿倒更似一对有着隐隐默契的忘年好友--年已十八的黎晰鸿,经过这几年独自在凉州历练,愈加显得成熟稳重,反而大了他五岁的白子泉行事还是老样子,全凭着性子来--好在也不是什么令人头疼的执绔子弟性子。
眼前的少年早已褪去了三年前重见时的稚气,自西平一战成名后,随着年岁增长,过手的事务渐增,仿佛整个人无时无刻都不散发着阵阵肃穆之气,人愈加寡言少语,行事愈加沉稳果决,常常让人忘了他也不过还是个未及弱冠的少年郎。若细细推敲下来,黎晰鸿自入凉州之后的行事必定是受了黎老将军私下指点的,行兵布阵也全无初入战场的青涩,杀敌毫不手软甚至狠辣,更无初上战场的畏缩恐惧,仿佛打仗对黎晰鸿来说不过是换了个地方,换了种方式继续跟着祖父读书习武一般--不改的是那股不要命的拼劲。
他忽然清晰得认知到,这位曾经他眼中的小表弟已经真真正正成长成了一位可以独当一面的男人了。
再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梦想,还有今天刚收到的那封母亲的亲笔信,白子泉重重的叹了口气。
黎晰鸿被这突兀的叹气声打断了思路,终于放下手中密函,抬眼正视着白子泉问道:“得曦兄可是有事?”
白子泉不自觉苦了张脸,又长长叹了口气说道:“今日收到了家母的亲笔信,道是已在京城帮我订好了人家,若是我仍不回去,便让我四弟抱着公鸡先将人娶进门。”
黎晰鸿闻言挑了挑眉,口气里带了丝揶揄:“大舅母帮表哥择了哪户好人家的闺秀?”
白子泉无力的摆摆手:“我哪耐烦去记姓甚名谁,你莫看我笑话,我可是烦死了,京城我好不容易出来了,便不会轻易回去。”
黎晰鸿倒水的手顿了顿,想要开口劝白子泉回京,定亲成婚可不是小事,况且舅母的脾气他也是晓得的,现下凉州无事,军医再从别处调派即可。
虽则他亦十分珍视和白子泉的情谊,也只得压下私人情绪,待要开口相劝,便见白子泉摆了摆手:“你先听我说完,我虽是任性之人却还分得清事情轻重。只若回了府里我却是别再想轻松出来了,京城我实是入不得,但我也不愿害了女方,我自会想办法解决这亲事。我已写好了回信,告知家里三日后启程离开这里,你莫错了口风。若之后家里再派人来此寻我你便只咬定只知我离了凉州是回京便可。其他我自有安排。”
黎晰鸿听他这么说,虽觉不妥却也不想胡乱插手,再者白子泉在大事上还不至于犯糊涂。只默默点头表示知道了。
白子泉待看他点头答应了,便轻轻松了口气,又说道:“另外还有件事,是关于我身边那两个药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