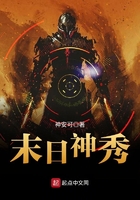那个吻,相当用力。
她不愿意相信,但她有基本的判断能力,事实也让她不得不信。
慕氏大厦顶层的总裁办里,慕寒川那双剑眉微微蹙起,他打给江韵的电话被挂断了,他又接二连三的打,没人接。
心里咯噔一下,他想起今天审讯那个赌鬼的事。
当时冯远的人把那男人带过来,他是很生气的,眸中带着刀剑一般的刺骨阴寒盯着那男人,“撞车的事,是谁指使你?”
那中年男人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微微笑着看他,“没有人指使,我撞车看心情,撞谁也看心情。”
慕寒川啪一声点燃指间夹着的香烟,“你信不信,只凭故意伤人这一个罪名,我可以让你把牢底坐穿。”
然而那男人并不畏惧,脸上的笑愈发恣意,“江州的慕先生,谁不知道,我当然清楚你的能力。不过你有本事把我送进去,我也有能耐让他们把我放出来。”
一个赌鬼,却那般大的口气,不用多想慕寒川也知道,他说他背后没有人,摆明了是胡扯。
最后他把人放了,冯远从大门口进来时正好看到那人从慕氏出去,他十分不理解,到顶层时问慕寒川为什么。
慕寒川背对着冯远,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男人周身烟雾缭绕,最后又想起了什么似的,回过神问冯远,“叫你调查的事,怎么样了?”
冯远把手里拿着的资料放在大班台上,“信息已经整理出来,结果还挺让人惊讶的。”
“哦?”慕寒川挑眉。
“那赌鬼叫江秉侦,是江秉毅的堂兄弟。不过很奇怪,他来江州之后从未联系过江秉毅,反倒是帮吕秀珍做过不少事,巴黎那个肇事司机也是他安排的,只可惜,那人死了,线索断裂,我们手中掌握的证据也太过片面,否则给吕氏定罪不是难事。江秉侦手里握着吕秀珍的把柄,所以吕氏母子对他十分客气,他开口要钱,吕秀珍与江明琮从未拒绝过。”冯远回话。
慕寒川点点头,后来又吩咐冯远,“澳洲的案子年后从江氏撤回,以招标的形式在江州另找合作方。”
冯远拧眉,一双黑眸猛地暗了下来,“按照当初澳洲那边与江氏签下的协议,如果我们单方面终止合同,可能要赔给他们相当大一笔钱。”简直堪称巨款。
慕寒川两指夹烟在大班椅上坐下,似乎对要赔偿多少毫不在意,蹙眉道,“叫慕氏的律师团队过来,关于协议,让他们仔细研究一下。如果能赢这场官司,除了律师费,慕氏愿意把与江氏合同里规定的违约金全部当做报酬,送给他们事务所。”
“慕总这是舍财也要让江氏栽跟头?”冯远笑。
慕寒川神情却很凝重,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意思,蹙眉交代冯远道,“去安排吧。”
把江秉侦放走后,他想了很多,江韵的事,不是江明琮做的,更不可能是江秉毅。
那江家剩下的人还有谁?吕秀珍、江萍。这母女二人想害江韵不是一两天,大大小小的坏事做了那么多,也该付出点代价。
江氏这几年业绩虽然勉强维稳,但上个季度却有下滑的趋势,为了稳住局面,江明琮费尽心思才拿下澳洲那个单,这些情况慕寒川是知道的。
他不出手便罢,一旦出手,就要打蛇打七寸。
这天中午,慕寒川有个加时会要开,江韵电话没人接,他打到知行公司前台去,前台小姐十分客气的对他说江韵下班吃饭去了,等下午上班时,她会叫江韵给他回电话。
确定了江韵的安全,慕寒川说不必了,午饭没来得及吃,就赶着与北京方面探讨年后的合作方案。
下午他推了饭局,亲自去接江韵,却见她对他不咸不淡。
一路上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期间江韵手机短信提示声响过一回,她没看,只愣愣望着窗外的风景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慕寒川往她身边挪了挪,要握住她的手,被她不动声色地避开了。
这般的抗拒,简直比刚结婚之时还要严重,慕寒川眉头一蹙,心头隐隐觉得不安。
“不舒服?”他试探。
“没有。”她冷漠,似乎多一个字都懒得说。
终于车到于归园,两人下来,往别墅里走。
江韵走在前头,脊背挺得很直,未回头看慕寒川。
在玄关处换鞋时,她的手机从包里掉了出来,慕寒川正好进门,弯腰帮她捡起,不小心按亮了屏幕,那条消息便清晰地映入他的眼帘。
鸿鸣山殡仪馆天堂六号厅,追悼会定在明天上午十点。
发信人是温欣然。
江韵也看到了,从他手中夺过手机,很不客气地按灭显示屏,低垂着一双眸子,看不出情绪。
她换好了拖鞋,起身往客厅走,边走边语气淡淡地说,“方岳父亲过世了,明天的追悼会,我会去参加。”
男人挑眉,没有回话。
吃晚饭时,慕寒川隔着餐桌问江韵,“你非去不可吗?”
江韵轻笑,明明在笑着,脸上的表情却十分淡。
她抬起头静静与慕寒川对视,良久,淡粉色的双唇中才吐出一个字,“是。”
“我跟你一起?”慕寒川问她。
江韵静静地吃饭,咽下口中的汤之后哂笑一下,“不必了,我是通知你,不是跟你商量,明天的追悼会,我自己去。”
她吃完了,放下碗筷起身走人。
慕寒川心里窝着一股气,却无处发泄,待江韵走到门口,他问她,“在你心里,方岳还和从前一样重要,是吗?”
江韵一愣,身体僵直,她双眸中有泪,没有回慕寒川的话,大步走到楼梯口,飞速上了楼,洗漱之后就钻进了被窝里。
慕寒川回房后对着手提办公,马上要过年,公司很多事务要处理,往年他一般是留下来陪着办公室所有人一起加班的。
今年不同了,他有了妻子,舍不得让她一个人独守空房,已经多次破例把工作带到家里来做。
但这个夜晚,他忙碌的同时心里却被阴霾笼罩,关于江韵对他忽然转变的态度,他心中不舒服。
他下半夜才忙完,回到床上要抱住江韵时却发现,她根本没睡着。
“怎么不睡?”他轻声问
江韵原本睡在床的一侧,面朝外,背对着他,被他抱住之后她慢慢转过身来,漆黑的眼睛在黑夜里闪着光。
她望着慕寒川,似乎要看穿他的灵魂,最后低眉问他,“我为我母亲的事赶往巴黎那段时间,你也曾在巴黎待过很久,是为了我去的?”
慕寒川沉默良久,最终点了点头,“是。”
就承认吧,承认你对她爱的疯狂,承认你曾有过那样一段痛苦挣扎的暗恋。
“我回来你正好去接机,你早就知道我那天会回江州?”江韵又问。
“对。”慕寒川仍旧实话实说。
江韵轻叹一声,头埋在他胸膛里,过了许久,才终于蜷缩着身子咬紧牙关颤声问他,“是你叫人通知周致敏我那天会回来,所以周致敏才会出现在方岳那里,所以我才会碰上他们?”
男人抱着她的动作一僵,半晌才回话,“算是吧。”
慕寒川双眉紧拧着,他早猜到会有这一天,他做了使计策耍手段破坏别人感情的事,早想过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但他还是做了。
就像快要渴死的人,明知道面前放的是一杯毒酒,还是毫不犹豫地饮鸩止渴。
对他来说,江韵就是那杯他宁死也要饮下的酒,用计破坏她与方岳算什么,为了得到她,他早就满腹阴谋地跌入黑暗中,机关算尽、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