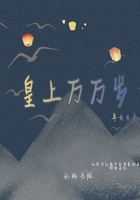白随意走后的第三天。
清早。
晨曦微露,白霜清寂,千丈高峰,处处冒寒。
待得天光大亮,屋中空气俱都被照得通透,粒粒尘埃漂浮在缕缕光柱中,翩然沉浮,自有一番韵味。
又是一个美妙的早晨。文舒轻眨睫毛,注视着跳跃在光柱中的尘粒,唇角缓缓弯起一抹清浅的笑意。日子很美好,庸人才自扰。不就是走了一个白随意吗,她的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不是?不仅要过下去,还得好好地过下去!
“吱嘎——”神医山庄真是个好地方。庄人不似想象中的严肃、谨慎、冷淡,而是俏皮、欢乐、赤诚,对人对己都敞开胸怀,展开笑脸。文舒回想着这两日帮他们采摘药草、分类晾晒,不自觉又抿出一朵笑意。
“庄主?”她刚刚打开房门,便对上一双清澈的温柔蓝眸。背着光,那双蓝眸看起来深沉广阔,温柔似水,正是一早等候在外的褚华。
褚华眼中映着她尚未消去的笑意,触到她略微诧异的神情,两颊渐渐涌上一团绯意:“叫我名字就好,叫庄主太生分了。”
文舒眉毛一挑:“那庄主为何从不唤我名字?”
他似乎总是避开唤她名字?她略略回想一番,不禁有些讶异,他是怎么做到的?明明总跟她搭话,却从来不叫她的名字,真是好技巧!
褚华颊上的羞意更深,憨憨一笑:“有吗?”
扑哧!有吗?他竟然问她有吗?文舒瞅着他红得快烧起来的脸颊,甚是想笑,这个人,见着她会脸红呢!比起脸皮贼厚、恬不知耻的白随意,他真是太可爱了!霎时,她脑海中浮现出白随意不正经的、满含促狭的脸庞。
可恶,她干嘛拿那个坏东西跟褚华比较?岂不污了褚华的风姿!她想到这里,心下气愤,狠狠一闭眼,甩甩头,方笑笑道:“不知庄主找我有何事?”
褚华见她又唤他“庄主”,很不高兴,张口要纠正她。然而就在这时,身后忽地响起一阵朗朗笑声:“文舒姑娘,我家庄主这是跟您报喜来了!”
“报喜?”报什么喜?庄中要有喜事了吗?
说笑之人正是庄中待人最为热情的褚言,他冲文舒一挤眼,露出一排齐整的小白牙:“我家庄主神志渐清,可以操起老本行干活了!”
呀?文舒又惊又喜,他可以干活了,岂不是说……
褚华狠狠瞪了褚言一眼,挠挠额头,赧然笑道:“文舒姑娘,你,你什么时候方便,给我看看你的伤?”
这,这是真的?她不是做梦吧?文舒捂住怦怦直跳的胸口,呼吸愈来愈急促——传说中只为皇室医诊的神医山庄,居然肯为她医脸?况且,为她医诊的竟然是山庄的庄主?哈,这,说出去谁信?
“文舒姑娘?文舒?文舒?”
“嗯?”耳畔响起一阵陌生的呼唤,眼前一只白皙的手掌挥来晃去,文舒定神一看,这才发现自己刚刚走了神,以至于褚华拧眉,褚言憋笑。一时也有些羞赧,垂下眸子,半笑着捻着地面:“我,我随时方便。”
真的,她随时方便!她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倾听着心中传来的阵阵强烈的、迫切的嚎叫声,文舒这才发现,曾经的淡定都是假的!她身为女子,对容貌的爱惜不亚于任何平常妇人!
更何况……她想起白随意那张俊美得光芒四射、招蜂引蝶的脸,心中流过淡淡的欢欣。终于,她能配得上他了。终于,面对万千面容姣好的少女,她不必再那样自卑了!
呸呸,她怎的又想起他来?文舒狠狠闭了闭眼,暗暗将自己唾弃一番,这才望向褚华笑道:“庄主大恩,文舒无以为报。日后庄主有任何差遣,文舒必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褚华惊得张大嘴巴,后退两步,连连摆手:“不用不用,医者父母心,这本是我应该做的!”
“噗!”褚言正蹲在石凳上啃一只翠绿的青果,闻言全都喷了出来,“庄主,举头三尺有神明。您说这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真是的,他明明就是为了讨美人欢心,做什么说得大义凛然?
褚华被他一打岔,气地拧眉,扭头冲他吼:“什么三尺有神明?什么风大闪了舌头?你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就闭嘴,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
真是个讨厌的人,走哪儿跟哪儿,烦死烦死!褚华恨恨地瞥他一眼,心道:在文舒来之前,他可从来忙得很,三天两头见不着人影儿!现在庄里来客人了,他不去围着那漂亮的文槿小妞儿转,而是亦步亦趋地跟着他,是何居心?
褚言狠狠啃了一口果子,毫不示弱地反瞪回去:你以为本大爷爱跟着?要不是你这庄主做什么事情都不让人省心,鬼才愿意跟着你!
事实上,他跟绿儿的感情刚刚有所进展,恨不得时时刻刻待在她身边,寸步不离!可是上回这二愣子庄主举针狠戳文舒,将人家的手指头扎出来N多血珠,简直丢尽了山庄人的脸!传出去(虽然不大可能,但是以防万一嘛),他们还要不要做大夫了?
显然,这俩从小一起长大,甚至同穿过一条裤子的男人很有默契。褚华接收到那一道气愤、悲愤、恼怒、委屈等交集的眼神,身子一抖,心头升起些许心虚与内疚:“文舒,那天的事情,对不起。”
“嗯?那天?什么事情?”文舒被他软软的眼神搞得有点蒙,歪头想了一会儿,才知他说的是那天拿针戳她之事,好笑地摆摆手:“庄主言重了。”
褚华对上她坦承澄澈的眸子,只觉脑袋恰似一半装了水,一半装了面粉。一晃,就混沌不清了。喃喃地张张口,眸子愈发迷离。
褚言瞅着手中晶莹剔透、美得仿若艺术品的果核,又歪头瞄了瞄褚华那颗圆滚滚的脑袋,阴森一笑,腕上一用力,那颗果核便划出一道儿优美的弧线,正正击向褚华的后脑勺:“嗷——”
褚华触手一摸,只觉一片湿哒哒、黏糊糊。往地上一看,正见一只碎成两块的果核歪歪横躺,其上牙印遍布,森然可恶:“褚言!”
褚言嘻嘻一笑:“庄主,别傻愣着了,人家文舒姑娘等侯多时了!”
褚华这才发现自己又看呆了,挠挠头,很是不好意思:“这边请。”说罢,背着她对褚言做了个恶狠狠的表情,张口无声道:“滚开,让个空儿!”
褚言撇撇嘴,脚尖一点,跳下石凳,也对文舒做了个:“请!”
好一张精巧细致的脸庞!褚华打量着手中这张看似普通的面孔,眸中划过一丝惊艳:不愧是拥有那样一双黑眸的女子,拥有这样优美的轮廓,配上她沉黑幽静的双眸,简直得天独厚,备受上天恩宠!
在他心中,文舒早已是女神一般不可撼动的地位了吧?怕也只有他,会对这样一张惊悚的面孔发出赞叹之声吧?褚言眯起眼睛,难得肃了容:庄主他,是真的喜欢上这个名叫文舒的女子了吧?
而就在此时,被两个男人一动不动瞅着的女子,却紧闭双眼,紧张得不能自已。
关闭了眼帘,听力便变得尤其敏感。文舒听着耳畔响起的低低的叹息声,手心渗满滑腻的汗水——不是她不相信褚华,实在是她对自己的面容能否恢复,抱着太大的期望!
“是谁?是谁将你伤成这样?”粉白的肌肤上,遍布着纵横交错的疤痕。粗粗细细,深深浅浅,将一张姣好的面容割得支离破碎!褚华呼吸渐粗,颤着嗓音道:“何人如此狠毒,将你伤成这般模样?”
他的嗓音低沉而沙哑,充斥着愤怒与心痛。文舒感觉到他轻颤的指尖,心中一动,绷得紧紧的心弦松了许多:“无碍,我已经报过仇了。”
是的,她已经报过仇了。那个狠厉的刀疤汉子,已经被她一剑穿过胸膛,下去见阎王了!
“哼,胆敢伤害我姐姐,我岂能留他活命!”一声清脆娇嗔的声音由远而近,走来一个蓝衫女子。她下巴高昂,鼻孔朝天,一副“挡我者shi一百遍”的样子,正是早起捉鸟的文槿。
“师兄,阿槿,你们来啦。”文舒缓缓睁眼,对上来人关切的神情,心中一暖。
文槿灿然一笑,欢呼一声奔了过来:“阿姐阿姐,你们刚刚在干什么?呐,让我猜一猜……唔,是庄主准备为你医脸了么?”
一旁,田伯棠也略为紧张地看过来。文舒好笑地摇摇头,轻轻戳了戳她脑门:“是啊,鬼灵精,庄主特地抽出时间要为我医诊呢!”
“嗷——庄主你真是大好人!”文槿松开自家阿姐的脖子,转去要搂褚华:“比那个不知所谓的白随意要好上一千遍、一万遍!”
田伯棠淡淡拧了眉,捉住她的后颈:“阿槿,不许胡说!”虽然他也不太喜欢白随意,但是看文舒的模样,恐怕多说也无用。
“当真?文槿姑娘,此话当真?我真比姓白的那臭小子好上许多?”褚华却将此话当了真,紧张兮兮地瞪着她,一双深蓝色的瞳仁晃呀晃,满满的期待。
“呃?”文槿方知自己说错了话,挠挠头皮,干笑两声:“当真!在阿槿心中,庄主比那白随意好太多了!”
方才她说那话,并没过脑子,当不得真。但是这回,却是她细想之后的回答!
“嘶——”褚华深吸一口气,转身看向文舒。一双水润的蓝眸闪烁着灿烂与深情,其中似有千万颗烟花同时绽放,璀璨至极,绚烂之至!
文舒被他明亮的眼睛灼灼盯着,心中涌起一股奇怪的滋味。不甜不涩,不苦不咸,不温不寒。她将这滋味儿品了品,缓缓垂下眼睑,静静地看向地面。
“喂喂,庄主大人,您再发呆下去,黄花菜都凉了!”褚言不知从哪里又顺了颗果子,握在手中不紧不慢地啃着,不轻不重地出言提醒他道。
“嗯。”褚华缓缓收起那丝迷恋之情,努力做出一副镇定的表情,“文舒姑娘,请把眼睛闭上。”只有她闭上眼睛,他才能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地瞅她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