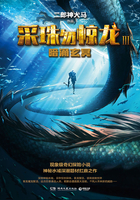本来想去找洋哥商量再下一次地洞看看能不能有所发现,但是不管我怎么说妈妈都是坚决不让出门,我说伤口已经好了没什么事。妈妈白了我一眼没好气的说:“你不要再说了,反正年前我是不准备叫你出去的,这才二十来天,万一你出去喝个酒,不注意再吃个辣子,到时候伤口一发炎你看咋办。关键你这是伤到头上了,再不小心变成傻子咧叫人都咋办,我和你爸以后都靠谁呀。”
彻底被妈妈说的无语了,难道我真的已经变的有点傻了,无奈之余只好打消了去找洋哥的想法,想想年前都不能出去就无奈的叹气。每天都享受着和猪一样的生活,吃了睡,睡醒了再吃,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因为我从学校出来的早一点,几个年龄相仿的都还在上学,刘果又没在,真正的快憋死了。那时候又没有杂志什么的,闲的把从张屯村收来的那几本爱国青年留下的旧书都看完了,想帮妈妈做点事打发一下无聊的时间,但妈妈坚决不让我动手。就只能在门口村口转转,这天刚出了后门就听有人按喇叭,抬头一看就见从西边渠岸上来了一辆摩托车,再见骑车的人时心想,终于有说话的人了。刘果到了我跟前后,很明显他变了很多,首先就是成熟了,也微微有些发福,不过说话和以前的感觉一样:“唉,老伙计,咋听说这次差点回不来咧得是。”
我心中暗自吃惊他离得这么远怎么会知道我受伤的事,就紧张的问:“你都不在家,咋知道这事的?”
刘果看我的样子嘿嘿一笑:“上次在县城碰见邻村的谁后听说的,咋了,我还不能知道吗?”
听他这么一说心里便释然了,主要是我担心引起萧哥他们的注意,见是这样就摇摇头说:“这事也传的太快了吧,碎碎个事传的满世界都是。”
表面上看虽然是兴高采烈的刘果,却难以掩饰内心的那丝忧伤,仔细看他时就觉的哪里有些不对劲了,他的右脸好像是稍微有些红肿。可能也是觉的我看出了什么,就说先回家去转一下,晚上再聊。呆了一会确实有些冷,抽了一支烟刚准备回去,没想到刘果就又骑着摩托车过来了,不过明显是情绪不高,有些发牢骚的说:“真******背到家了,在外头挨骂,回到家还是个挨骂,早知道就不回来了。”
我拦在车前有些奇怪的问:“咋咧,刚回来可又准备走呀?五分钟都没停下。”
刘果啐了一口说:“之前知道家里人要回来,想着回来看看,一见面就是个骂,先走啦,回头咱再谝。”
说完就准备走,我忙拦住他,因为洋哥说过还要想办法让他给弄点子弹,就拉着他说:“果子,时间长也不见了,走去家里坐坐谝一下,急的干啥。”我是连说带拽,刘果就掉转车头把车停在后门口和我进了院子。大冷的天让人直打哆嗦,我的房间因为没有生炉子而显的特别冷,刘果喝了一口热茶后有些感慨的说:“当时收破烂多好,非要去跟萧哥混,到头来是光落了个肚子圆。”说完拍着肚子,看他那表情也不知道是炫耀还是真的伤感。
我敷衍着说:“不是挺好的吗嘛!收破烂能有个啥明堂。”
刘果仰着头故作深沉的说:“其实也没有啥事,就是感觉在人家手下当马仔不好受呀!”
这家伙原来是嫉妒别人了,我嘿嘿一笑:“那就做老大呗,果子,你最近没再炼那个什么功了吧?”
一提这话刘果马上就像变了一个人,拉着脸说:“我现在都没主意了,咱都是自己人,也没什么可瞒的,今天就为了炼功的事叫萧哥把我还打了一巴掌。”
其实从他微胀的脸上已经能猜出来什么了,但没想到竟是萧哥打的,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下我也不好劝,就只能实话实说:“那人家也是为了你好,那个什么功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刘果目光呆滞,痴痴的说:“以前谁和我这样说我绝对和他急,但今天萧哥说的事真的是叫我不知道咋办,老伙计,你相信不相信什么长生不老啦成仙之类的事。”
我心里一惊,萧哥竟然把这事到处说,或许是把刘果当成自己人了吧,想着刘果也终于知道他和萧哥还有台湾人是在干啥了,但这事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在暗处,也不能告诉刘果呀,先听听他对这件事知道多少吧。我就有些装疯卖傻的说:“有这事吗?咋有些跟听神话故事一样。”
刘果哼笑了一声,有些生气的说:“我也在想这事的真假,******,今天早上萧哥让我去张家山办个事,我就说练完功马上走,也不知道今天为啥人家火气特别大,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说我练还是个球,后来人家说的那个事真的把我听的是晕晕呼呼的。萧哥说,‘看你这碎怂还可以才给你说这话,要不然谁管你干啥,你们练这功的人都是些脑子有麻达的货,知道叫你去张家山干啥不,就是去找能成神的东西,光练‘乏仑拱’起个球的作用,不把那几样东西弄到手能干个怂,从今天开始你不要给我再炼这个东西,专心给咱办事,不要叫我失望。’我就想这啥东西还能把人变成神仙,问人家是啥吧也不说,光说到时候就知道了。”
看来刘果只是听了个皮毛,根本就没有接触到实质,这个萧哥也放心,这秘密都随便给别人说。还有就是难道张家山又有啥消息了,估计刘果他也不会知道什么,先问问吧。我就故作轻松的问:“果子,那萧哥让你去张家山干啥?”
刘果摇摇头很严肃的说:“这个不能再说了,这是咱俩人谝,老样子,你不敢把这事乱说。”
肯定不会给谁说的,因为我自己要做这事呀!有时候在想刘果对咱那是绝对没的说,做为朋友的我却一直在利用他,真为自己的卑鄙感到无地自容,但为了喜儿也没办法了,只能在心里替喜儿向刘果道声谢谢。我憨憨的笑了笑说:“放心果子,我知道什么该谝什么不该谝,不过有个事得求你给我办。”
可能是从来没在他跟前用过这个求字,刘果听的一愣,继而爽快的说:“说吧,咱兄弟俩个渥是个啥事,尽力而为。”
我奸笑了一下:“也没有啥大事,你不是玩枪吗?给弄点子弹玩得行。”
刘果以为我是用弹壳做链子枪,当即表示没问题,他答应的如些干脆,我想他肯定也是会错了意,忙半开玩笑的说:“果哥,弹壳玩没意思,弄些真子弹得行,还有你玩的那手雷什么的,给弄上几个让咱见识见识。”
刘果愣愣的看着我,这才看出了我笑的很奸,他肯定也不会想到我会有枪,只当我是闹着玩,他沉默了一会就点了点头说:“可以,不过要等几天,光是子弹,别的你就不要想了。”
我也没指望着能要上手雷,就说:“开个玩笑,谢谢果哥,不过把子弹给咱多弄些,叫我拿出去也显摆一下。”
听了这话刘果猛地抬起头说:“千万不敢,你要是这想法就不能给你拿了,这些东西敢随便拿出去吗?”
真想抽自己几个嘴巴子,在向他诚恳的道歉和保证后,刘果终于答应过几天把子弹给拿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