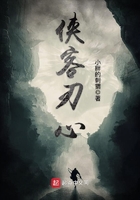“什么?难道说子敬兄弟的货物也被这伙盗贼掳走了?”
“嗯,就在前两天,我从开封运往庐江的一匹丝绸被人劫了,今天经你一说,倒是和我家丁所描述的体貌特征极为相似。”
粥场旁边有一家酒楼,名曰“九江坊”,掌柜的也是和鲁肃一样,经常差人到隔壁放粮。
“黄巾大乱后,只要是没打起造反的旗号,朝廷都很少有人管,所以事发后,鲁某也并未报官。”
许褚,许定,鲁肃,董袭,四人包了二楼雅间儿,于屋内吃着酒。
“这么说这股江|贼的来路,连子敬也不知晓?”
“是啊,我托人打听了,这伙人似乎常在涡河一代出没,作风硬朗,谁的面子都不给。”
“那往东边走的船岂不是全要被他们洗一遍?”
“哼,江山代有才人出,贼寇强匪亦如此。”
董袭将杯中残酒一饮而尽,然后又倒了一大碗,端着站起身来。
“诸位,今日是董某冒失,差点冤枉了好人,想这伙儿贼人必是流寇,吃肥了就会******转移,因此事不宜迟,既然有了其藏匿的线索,我这就回驿站召集人手前去把这帮龟孙儿收拾了,也一并帮子敬兄弟把货物夺回来。”
天还没黑,火红的夕照日还剩下一半露在天际。
鲁肃也把酒端起。
“董大人这就见外了,如今天下纷乱,贼势猖獗,我鲁子敬养的这些乡民义勇,就是为了协助官军平荡这些恶寇,不然私拥卒众,与谋反何异?”
许褚不饮酒,只是点了点头,由其哥哥许定代劳,也表达了全力帮忙的意思。
这正是董袭最希望得到的回应,因为从素质上来比较,董袭手下这些差役的战斗力,根本比不过鲁肃的壮丁,更别说许褚身边那些日后会成为曹氏虎贲军成员的硬汉。
从理论上来说,鲁肃这种头上没衔儿的,私造兵器,私练兵丁,和北宫凝一样,都是绝对违法的。
但现在谁有空来管?势力小的不敢管,势力大的巴不得你多练点儿兵,然后把你拉拢过来,收为己用,即便收不了你也可养寇自重,要挟朝廷,以逸待劳。
虽说天湿地潮,大家的酒还是喝得很温暖。
很久没活动筋骨的许仲康,方才体力并未被榨干,此刻还显得有些意犹未尽。
董袭本想拿着酒碗上前揽着他多说几句话,交下来这个不打不相识的猛人,可对方一来不喝酒,二来总是给人一副严肃毅然的感觉。
许定就像个代言人一样,替弟弟把话都说得很明白。
完全找不到亲近的突破口。
无奈的董袭,只得自己闷头连干了三大碗。
-
当贺齐看到回来的董袭身后跟着的这些人时,纠结的五官总算舒展不少。
“我来介绍,这位是山阴贺公苗。”
“哦!久仰久仰……咦?为何不见锦帆贼甘兴霸?”
鲁肃左右张望着,在他的印象里,以华丽著称的两大豪侠向来是形影不离的。
董袭见贺齐的脸僵硬了一下,连忙解释:“锦帆贼临时有事,入蜀了。”
贺齐并没走董袭给的台阶。
“以后我与甘宁,便是两路人了。”
贺齐漠然地指了指桌上的官印。
“从此长江八百健儿与我贺公苗再无瓜葛,若要让我遇到,必逮捕其归案,决不姑息!”
“妈的少说两句吧!”
酒喝得半酣的董袭听了这些话,兴致又没了。
“贺大人这也算是弃暗投明了。”
鲁肃的话,丝毫听不出是赞同还是酸讽。
是夜,大家饱餐了战饭,驱兵赶至涡河沿岸。
这条淮河第二大支流,也算是一条西北东南商路要道。
董袭沿着河岸走了一圈,不禁叹道:“妈的,难怪贼人屡屡得手,此地昏黑雾浓,低洼沼泽密集,船行迟缓、搁浅之众甚多,简直如划行到了案板上一般,任人鱼肉。”
“这是人为的,有人挖坑引了泥沙,准备工作做得很足,狡猾而专业。”
鲁肃反复观瞧后,说道。
“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他们今晚会出现吗?”
许定问道。
“一定会的,今晚有一批从徐州辗转过来的巨货,若能顺利接收,足够抵各路贼寇大半年的买卖了。”
贺齐见鲁肃这样说,不禁笑着接口道:“居然还有能让子敬先生称为巨贾的商船,不知是哪路财神爷?”
“东海糜子仲。”
“哦,就是那徐州第一贾,糜竺?”
刚转行不久的贺齐,依然对当今富甲了若指掌。
“没错,徐州牧陶谦能在黄巾之乱后元气不损,继续吸纳流民,耕织田溉,丰丁富民,全靠当地两家士族:一是陈珪陈登父子,二就是这位财神爷,鲁某这点家当,不过是其九牛之一毛。”
鲁肃说完,慨然一笑。
等待是漫长而不能松懈的——大家决定埋伏于芦苇丛和临岸的树林间,待贼人显现、实施劫掠时一鼓作气将其夹击在洼地中央。
捱了一夜,也不见糜竺的商船经过。只有些零星的渔船和小股丝绸、军械团伙儿在河中央做着黑市贸易。
该来的也自然没来。
“奇怪,按道理今天夜里应该到了啊?”
大家只得悻悻而回。
第二天鲁肃差人打听到了原因。
“有从徐州来的朋友跟我讲,糜竺的商队因为得知谯县聚集了很多****,于是临时在鹿邑县改了道……”
“妈的,害得我们白白等了一晚上。”
董袭以拳击案。
贺齐望着鲁肃,倒是一皱眉:“这伙儿贼人,这么出名了?连徐州那边都知道?”
“相信我那朋友所指的****,并不是这伙儿来历不明的人。”
鲁肃的眼睛也直直地望着贺齐。
贺齐还是莫名其妙,被鲁肃瞅得有点不自在了。
“子敬先生,这……”
“听说甘宁的八百健儿已经开到了谯县,也盯上了这批货……而且有人探知阁下目前也落居此地。”
眼线这东西,从人类有尔虞我诈开始,就已经布满了华夏大地。
而贺齐的洗底之路,必然是漫长的。
“哼,看来老子还真的脱不开这身贼皮了!”
“贺齐大人想站稳自己的离场,那就要做得决绝一点……”
许定把手中的刀抽出一半,亮闪闪的刀背如同镜子一般将其长长的脸清晰地映在上面。
-
-
戏谑篇之三国虚伪论:
曹丕与禅让
大家都知道,早年意气风发的曹孟德打下中土大半江上后,却在晚年逐渐展露出自己内心的欲望与堕落,最明显的就是将自己的地位无上抬高,诸如胁迫汉献帝给自己封公封王,加九锡等等。但其却最终在皇帝名分前戛然止步,而把这天下皆知的窗户纸留给后代来捅。
从没想在有生之年当皇帝的曹操,倒真有一个迫不及待的儿子。
曹**后,曹丕立即安排亲信们落实既定的夺位计划。
首先是一般文人名士跳出来造舆论。
带头张罗人自然是相国华歆,他先是上奏汉献帝,说我们魏王的品行和功绩已经超越了历代贤王圣主,早就有资格做皇帝了。绝对的大势所趋,民意所向。
具体如何腆脸吹曹丕且不谈,而终日过着被幽禁日子的汉献帝,哪里看得到外面的民意呢?
华歆的奏折只是个开场,接下来,这个老家伙又调动了朝廷的气象局主任——负责观天象的太史丞许芝。许芝上奏汉献帝,表示自从曹丕接任魏王以来,麒麟、凤凰、黄龙等神兽纷纷出现,天降甘露,各种珍稀植物也不断生现,种种迹象表明,汉朝气数已尽,该是魏取而代之的时候了。
这些敬畏自然的屁话从特么黄巾之乱就有人说。说到现在,依然不觉得腻。
还有与华歆齐名的王朗也乐颠儿地站出来,以一副饱经世故的长者之态说道:任何朝代和国家都有盛衰兴亡,汉朝坚持了四百年,现在已经差不多,陛下再不退位会招致大祸啊。
汉献帝也不完全是行尸走肉,还懂得挣扎两下,他壮着胆子冲下面那些还假装谦卑低头的魏武老臣们回嘴:大汉祖宗开创基业不易,你们能不能别劝我作亡国之君?
曹丕见汉献帝上来艮劲儿,有点儿急了,当下派了老将曹洪、曹休全副武装进宫抢玉玺,还把保管玉玺的官员祖弼砍死。刘协这个被吓大的皇帝,乖乖儿开始起草诏书。
曹丕刚露出求之不得的喜色,奸雄司马懿站出来说,陛下,冷静一点吧,就这么直接当皇帝,天下少不了说三道四,皇帝是要当,可不能坏了名声,烂嘴于后世。
曹丕也感觉自己的心急弄乱了计划,那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呢?
司马懿笑着说,您要做的,就是谦虚和推辞,其他的,让华歆他们来安排。
八百年没进过言的毒士贾诩站出来献了一计:先把玉玺好好地还给刘协,禅让书写好后,找人去造一个受禅台,举行一个隆重的禅让仪式,过程越曲折越好。
聪明一世而且一刻也没犯过糊涂的老贾诩,把这个美差慷慨地荐给了跃跃欲试的相国华歆,而曹丕称帝后,贾诩也官升太尉,跟华歆一起位列三公。
虚伪,刚刚开始。
禅让这个词儿,最早出现在《尚书》中,但其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
从上古时期就已经有这种看似民主的制度了,原来除了武力夺取政权之外,还有这种更虚伪的招式,不用打架,还可以落个得民心得天下的好名声。
也许,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
作为一个同样有着欲望追求的人来看这几千年华夏炎黄子孙的人性,笔者认为,表面上是让,实际上就是逼,只不过是当事人演的很像“让”罢了。韩非子就曾经在《说疑》中提过:“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人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所以说,我们都是人,不是耶稣。到底上古时这些领袖之所为是千古佳话还是欺世盗名,永远是捕风捉影。
也许有人就愿意承认这是中国产生的最早的民主制度,可掌权者若不把国家社稷首先视为私人物品,又何谈“让”字呢?
汉献帝写完诏书,有人拿给曹丕看,曹丕看完立即驳回,理由是措辞不够诚恳。
哭笑不得的汉献帝只好再写,写完又被曹丕给驳回,理由还是,不够“发自肺腑”。
这本身就是汉献帝这辈子内心阴影面积最大的部分,你还要让他演出真心诚意来,哇塞,大汉朝最后一位皇帝啊,你这种痛苦真不是我们老百姓能理解的了的。
最后一共折磨了三回,汉献帝总算文笔水平上来了,曹丕也勉强同意了。
不过剧本写好了,演员的活儿也是刘协的,而且两件事不仅没酬劳,台上演完后,台下你还要把最后那点名分交出来。
受禅台上,我们的魏文帝垂目低首,一脸恭敬谦和,影视剧中那些诸如在下何德何能,属下无才无德,怎可当此重任之类的词儿已经积压在嘴边,就等你第一遍开口让位,一股脑儿吐出去。
现场一共接受了四次禅让,曹丕三次都坚决避而推辞,激昂慷慨,红脸声泪——我明明不想当这皇帝,是陛下再三地逼我啊,推辞也不是,不受更不是,君让臣上位,臣不得不上位,这节操。
而望着曹丕的汉献帝,此刻的内心表情是什么?你们在国外影视剧中经常看见那种男女行房时男的在上面折腾得热火朝天,而下面的女人双眼直勾勾,无聊地看着天花板,没有一丝满足和触觉。
最后上面的曹丕释放了身体偏下部的快感,而下面的汉献帝也跟着松了口气,总算不用陪着了,终于可以下床了、哦不对、下野了。
这一幕大话剧演完,谁还说我们曹家有称帝的野心?
而汉献帝那边的演技考验真心大,他看看后面凝视着他的虎贲军,那一双双眼睛好像在说,排练了那么多次了,今天你要是敢演砸了......
呵呵,不过话说曹丕的城府,比起他老爹,还是嫩。《魏氏春秋》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曹丕于禅让后说了一句话——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细品一品这八个字,就能品出年轻人在得到这种自己驾驭不了的大权后那种溢于言表的得意忘形了。
这八个字的白话文是:舜和禹禅让的事情,我终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四十六年后,司马炎将曹丕的这一流程,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