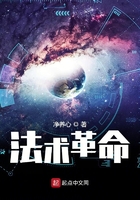大年初二,得到外公的同意,卿墨被秦牧天接到秦家过节,热闹丰盛的晚宴后,两位秦妈妈陈露李梦雅便嚷着手痒要搓麻将,秦池被梁升接走了,逢赌必输的卿墨无奈上阵,和诗诗姐一起凑了一桌。
卿墨专心致志码着牌型,耳朵竖起听陈阿姨细述规则,手上一哆嗦,不小心推倒了两张牌,假装不经意扶起来,暗自肉痛,妈呀,本就不擅长赌博,这麻将又是极费脑力的游戏,盯上家管下家,记住手中的,看紧牌桌上的,赌那么大,不输得倾家荡产才怪。
着一身粉紫旗袍的李梦雅扫了一眼面有忧色的未来儿媳,扬声对桥牌桌上的儿子喊道:“小天啊,你媳妇陪我们打牌,输赢算谁的啊?”
秦牧天战斗正酣,头也不抬地回道:“输了当然算你儿子的,赢了就当给我媳妇发压岁钱咯。”
卿墨这才吃了一颗定心丸,也不能怪她没出息,实在不敢高估她的智商,迄今为止卿墨在赌桌上的战绩为零,连QQ游戏里除了对对碰是正数以外,其余的麻将啊五子棋啊国际象棋之类分数全为负。
麻将声噼噼啪啪四下响起,桌对面的李梦雅一边摸牌一边问:“小墨啊,你姐姐和裴家长子婚期将至,准备得如何了啊?”
卿墨好不容易碰了三张,正思考打哪张牌,被李阿姨打断,禁不住诗诗姐的催促,随便打了张一筒,结果被陈伯母杠了一遭,沮丧道:“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啊,都是伯父伯母在张罗,姐姐想要定VeraWang的婚纱,不过据说很难定到。”
林诗诗出了一张七条,接过话头:“没关系,我认识一朋友和她关系不错,这件事就包在你诗诗姐身上了。”
卿墨摸了张三万,顺手把八筒打了出去,甜笑道:“谢谢诗诗姐。”牌还未落地,林诗诗啪地倒了牌:“胡,小七对。不用谢啦,让小天多给长辈发点红包就行了。”
卿墨傻了眼,强撑着继续“血战到底”,陈露拈起一张牌,大拇指上的祖母绿勾人眼球:“阿墨,一直没见过你父母,听说在国外工作,在哪个国家啊?”
这个问题突如其来,卿墨一时心慌,手下也忙乱起来,“好像在美国吧。”
“好像?这丫头,父母具体在哪儿都不清楚啊?”李梦雅轻责道。
“呃,他们家安在美国,爸爸是纪录片导演,天南海北到处跑,妈妈是画家,有时候也跟着去写生。”卿墨答道。
“真舍得啊,把这么乖的闺女丢在国内。留洋的人作风就是新派,我们这些老古董实在理解不了。”陈露感慨道,听得卿墨心里一阵难过,那些细微的哀伤,悠悠散散自骨头里飘出。
“妈,卿墨的父母是艺术家,创作是需要灵感的,要是把他们圈在咱们这个小地方,哪能收获好的作品,灵感早就被消磨没了,再说,你看卿墨多优秀啊,还不是遗传了父母优良的基因。”林诗诗解围道。
“现代人追求就是不一样,不过小墨,除了你家长辈,记得还有李阿姨疼你,有什么难事尽管开口,秦牧天胆敢亏待你,千万告诉阿姨,我自然有办法收拾他。”李梦雅心疼道。
卿墨羞得脸红:“秦牧天一直对我很好的,没让我受丁点儿委屈。”
“哎哟喂,妹子,瞧你家媳妇儿,多向着小天。”
“妈,我哪点对牧云不好了?”
“哟哟哟,该打,自己的儿媳才是最好的。”陈露笑着说。
四个女人一边说笑一边打牌,事实证明,李妈妈对待卿墨是极好的,才打了不到一个小时,卿墨桌匣里的筹码就流失一半了,三十分钟过后,只听得李梦雅接连向儿子报告喜讯,就冲着这口气,拓拓都能把悍马撞个稀巴烂。
“儿子,你那辆法拉利归我了。”
“儿子,你那艘帆船打明儿起就以我的名字命名吧。”
“儿子,你三藩市的两处房产打水漂了。”
。。。。。。
卿墨揉揉耳朵,不相信自己输这么多,陈阿姨和诗诗姐同情地看着她,“雀神”李梦雅是出了名的“吃肉不吐骨头”,只要能赢钱,坑蒙拐骗无所不能,简直没有豪门贵妇的气质。
秦牧天终于忍不住想来一瞧自家媳妇儿是如何败家的,看了一圈,彻底拜倒,这猪头,眼不疾手不快还胡不来牌,自摸的牌都能打出去,实在气不过母亲欺负新的不能再新的新手,挤开卿墨自己坐下来,一圈就扭转颓势,卿墨看得呆住了,霸王脑袋怎么长的,明明牌型乱得不得了,硬能被他打成什么“清一色”“龙七对”“清幺九”,好多术语完全没听过,早就空空如也的桌匣开始回笼资金。
这晚,先是输得心惊胆战,后又赢得盆满钵满,卿墨觉得像坐过山车般刺激,直到回去的路上,还兴奋不已。秦牧天却想,以后千万不再纵容小败家上赌桌了,若不然即使如他这般做牛做马辛苦赚钱,也抵御不了她挥金如汗洒。
年初四,卿墨就回公司上班了,逢年过节,珠宝玉石的销售情况都特别好,男人送女人,晚辈赠长辈,总之,珠宝是永恒的选择。
过几天,就是2月14号国际情人节,也是秦牧天的生日。这个秦二少,难怪女人缘那么好,情人节出生的,生来注定是个多情贵公子。
情人节一大早,卿墨苦思不已,臭秦二的生日送什么好呢。这时,陈霜姿捧着99朵玫瑰跨进办公室,递给卿墨:“喏,给你的,几年了?”
卿墨掰着指头数道:“8年了。”
陈霜姿惊奇道:“8年了,从来没有见过送花的人吗?”
卿墨低头嗅着花香,胸口起伏,说想见吧又怕见,说不想见吧好奇心定期作祟,为难道:“我想找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从来都没有留下关于自己的一点信息,只一张手写的卡片,每年写着不同的话。”
陈霜姿讶异不已,从花丛中拈起卡片读道:“祝你幸福。咦,这么简单。”看完后,把卡片重新插进花丛。
卿墨回忆道:“刚开始,写的都是极平常的话,比如“万事如意”“天天开心”之类的祝福,字也歪歪扭扭的,像不会写字一样。我读大学以后,就会写些诗句了,摘抄类似徐志摩、仓央嘉措的诗,有一年甚至改写了简祯的一句话,好像是“你甚美丽,你一向甚所有人美丽”,当时把我感动坏了。”
有些秘密,不被人发现也有莫大的价值,比如支撑你走过一段夜路,比如让你相信还不至于那么孤独,生命中的温暖有很多,如果始终有人不问前程默默为你付出,是多么幸运的事啊。陈霜姿从花束中抽出一朵玫瑰,鼻尖轻触,淡淡的花香立刻溢满心田:“卿墨,你真好运,世界上有那么一个执着的人守护着你。这朵花送我了,沾点你的运气。”
卿墨盯着陈霜姿手中的玫瑰,认真地说:“霜姐姐,其实前几天余淼来电话时还问到你,让我给你说一声新年快乐。我觉得他是真心的,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再考虑一下吧。”
陈霜姿捏着玫瑰的底端在掌中转圈,顿了顿:“卿墨,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何况我们不太适合。”
“霜姐姐——”
陈霜姿打断:“别说我的事了,还是帮你滤滤这个人的蛛丝马迹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到花的。”
卿墨撇撇嘴无奈作罢,一手支在腮帮上想了想:“忘了是05年还是06年了,反正之后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情人节那天都能收到99朵花。”
陈霜姿站得有些累了,懒洋洋躺在沙发上,按摩着脖颈:“第一次收到花的前一年,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特别的?”卿墨无意识地用手指绕着头发玩,使劲回忆:“那之前,好像还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倒是17岁我玩得最疯的那年,有一天看到几个小混混在酒吧门口打架,把一个男的打倒在地上起不来,浑身都是血受伤很严重,把我跟佳佳他们吓坏了,刚好手机里有警笛的铃声,我就偷偷点出来,大声喊警察来了,才把他们吓跑的,然后拨了120把那个男人送进医院,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床铺是空的,护士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离开了。”
陈霜姿摇摇头,琢磨道:“这都是之后的事了应该没什么关系,不过,没想到你小小年纪,胆子还挺大的嘛,还有你才17岁,卿总怎么会允许你去酒吧。”
卿墨敲敲脑袋,嘿嘿笑道:“谁没有不懂事的时候嘛,那时候叛逆得很,经常把我外公气得吹胡子瞪眼的,现在想想都很惭愧。”
陈霜姿听卿墨转而讲起自己小时候如何调皮捣蛋,慢慢忘了初衷,不时爆发讥诮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