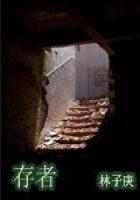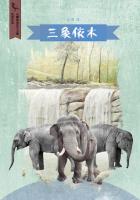丁:当今中国,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空气质量恶化,流行病蔓延,大江大河大湖大海大面积污染,饮水和食品不安全,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已经威胁到广大老百姓的正常生活。无法回避,不得不让人们思考。
谢:生态危机,有全球的普遍性问题,也有中国的特殊性问题。思考中国的生态危机,一般会反省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制度设计。但也有一种说法,把生态危机归结为西方文明的危机、美国生活方式的危机。他们主张,克服生态危机的出路,要靠东方的智慧,要靠中国的传统文明。这种说法,或许能够满足一些人的文化自豪感。
丁:这是一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说法,可以自我安慰,但经不起追问。固然,当今的生态问题和工业革命有直接关系。工业革命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给人带来享受和方便,同时也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走向紧张。工业革命起源于西方,二百年间迅速扩展到全球。全人类都接受了工业文明。如果这种文明出现了危机,已经不仅是西方文明的危机,而是人类文明的危机。
谢:西方一些思想家,意识到文明的危机,想从古代东方寻找智慧和灵感,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无可厚非。但作为中国人,对自己祖先的传统和文化,却应当有清醒客观的认识。古代中国有发达的农业文明,其中包含一些人与自然相对和谐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悟,值得珍视。但切不可以为我们早已拥有解决现代文明难题的灵丹妙药。从采集、渔猎、游牧到农耕,工业社会以前的诸种文明,与其说是当时的人类懂得了与自然和谐相处,不如说是由于人类自身能力还不够强大,不得不顺应自然。同时,也不应低估农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不和谐的一面。中国古代帝王,修长城、修宫殿、修陵寝,使得多少原始森林变成了童山秃岭,从此再不能恢复。
丁:因为能力低下而顺应自然,和自觉地尊重保护自然,不是一码事。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尼克松访华,中国的大门向西方开了一道缝。西方人来到北京,看见长安街上汽车很少,满街的中国人都自行车,称赞不已,以为中国人选择了明智的城市交通方式。殊不知,中国人当时选择自行车,并非环保意识的自觉,而是收入太低,买不起轿车。三十多年过去了,北京也成了轿车的海洋,堵车现象比西方大城市还严重。为举办奥运会只好分单双号上路。倒是一些欧洲市民,自觉地放弃开汽车,将自行车当作首选的交通工具。有能力拥有汽车而选择自行车,才称得上环保的自觉。
谢:中国古代先哲片言只语的智慧闪光,固然能给西方人以启示,但真正能够看清当今世界环境问题症结所在,并提出有效对策的,不是他们,而是现代的思想家和科学家。这些思想家和科学家,几乎都是西方人。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影响,没有人能和美国的生态学家利奥波德、生物学家卡森相比;中国的研究机构,也没有一家能够和提出“只有一个地球”的罗马俱乐部相比,能和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相比。
丁: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在环境保护方面,中国是后来者。当发达国家保护湿地的时候,我们还在围湖造田;发达国家禁止高污染行业的时候,我们还在发展五小工业。中国政府真正认识到环境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已经是1985年,而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已经是二十一世纪。
谢:在发达国家,善待环境,保护森林,爱护野生动物,已经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习惯。客观地讲,中国公众的环境公德,有明显的差距,我们没有妄自尊大的资本。
丁: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要守住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中国一些地方发生严重的生态灾难,不是认识水平问题,不是好心办坏事,而是某些人的利益驱动。一些企业为了发财,破坏环境是明知故犯。某些官员,为了私利,不惜牺牲公共利益和企业达成私下交易。为了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在某些地方成为常态,成为有实力有本事的表现,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立法存在漏洞、司法存在缺位,行政存在不作为和胡作非为,代表公共利益的舆论监督,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软弱无力,倍受牵制。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有也比我们解决得好。回避这些差别,空谈什么西方的危机,东方的智慧,恐怕无助于中国环境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