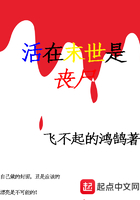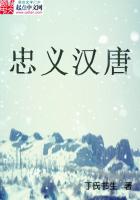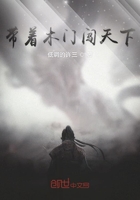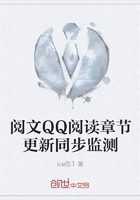通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紧缩政策,实现了1996年软着陆,但是软着陆之后就是长达数年的市场疲软和增长率下滑。与此同时,1997年底到1998年初,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出来。1998年7月,面对经济增长下滑的严峻形势,中国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于同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以适当的货币政策”代替“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9年初又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其效果并不明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所撰写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一文,认为导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政策性“撬动”奏效不明显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性的紧缩效应。
文章说,199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 。8%,基本上达到政府预定的目标,扩张性政策有了效果。但从时间序列看,这是自1992年以来第6个下降年份,1999年预测GDP增长7%,意味着下降之势将持续下去。纵观1998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财政扩张,货币供应和资本市场跟进迟滞;国有部门投资大幅增长,民间投资未相应跟进;消费增长平缓,失业增加和物价下滑无全面改善的迹象;人民币汇率固定不变,出口严重下滑,外资增速下降。1998年政府调整宏观政策,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措施,实行财政和货币政策双扩张,这是改革以来政策力度最强的一次。然而,扩张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样成功,这就表明,经济扩张和收缩的权力已不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那么,什么原因影响了政策效应,是政策工具性原因,还是制度上的原因?
据课题组分析,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一直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1993年7月开始的经济调整,从紧缩国有投资入手,通过拉高利率抑制非国有投资,实现了“软着陆”。间接控制似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际经贸形势骤变,“两头在外”的战略和出口推动的模式受到严重挑战。为了重振内需,政府再次运用扩张国有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但效果递减,特别是民间投资没有跟进,增长的下滑不可避免。国有投资历来是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军。然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主要特征是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经济的份额不断下降,但投、融资体制和银行改革相应滞后,资金供给与产出份额的变动是不对称的。在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部门产出的份额快速下降,从1985年的69%下降到1997年的38%,但国有部门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下降有限,同期从66%下降到52%,1998年国家增大国有投资,其比重还会上升。与此相适应,在用银行贷款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部门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2%和62%。在国有部门产出份额下降的同时,资金供给份额虽有下降,但与前者不成比例。与此相对照,非国有部门的产出份额已占2/3,而得到的资金供给,特别是银行资金仅占1/3.
课题组认为,由于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以前,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而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地方金融机构与城市集体和乡镇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软预算”约束。由于银行是国有的,它承担着国家政策导向性目标,支持国有企业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方面出了问题可以向国家要政策进行冲抵,而对非国有企业贷款的失败却难辞其咎。这就是所谓“肉烂在锅里”的机制。这种体制性“软预算”和特殊的“安全”准则导致了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一方面不以市场准则看待资金的价格,即使在高负债比例下,国有企业仍可不考虑负债成本,在能争到投资时,依然去大规模地投资;另一方面,银行也不断向无效率和无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注入信贷资金,而置效率、预期回报、竞争力、资产负债于不顾。于是,一方面国家为了撬动经济继续加大对国有企业投资,导致国有企业高负债,另一方面,由于民营企业获得资金有限,经济刺激不足。地方政府也跟了上来,纷纷批地建园建区,上项目,搞“开发”,要“振兴”,民间投资也有跟进的趋势。这种投资增加并没有消费的相应增加作基础。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达30%以上,而同期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8.6%,对比之下,如此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必要性和可持续性就成了问题。2003年,钢材、水泥、橡胶、电解铝等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出现上涨,受减产因素影响,农产品价格也开始上涨。引发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因素正在积聚。当时政府调控及时有力,这场通货膨胀没有发生,但由这次投资扩张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在几年内将会凸显。
1998年货币和财政双扩张,着力点放在拉动投资上。扩张的方式是:第一,降低利率、压缩超额准备,扩大货币供给;第二,发行国债,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加大退税力度,促进出口等;第三,财政货币相互配合,用银行信贷配套资金支持财政增加支出,用发行特别国债弥补银行资本金,提高银行抗风险能力,促进放款增加。
从中国经济运行实际看,上述效应是不足的。第一,降低利率没有引致民间投资的增加;第二,国家承诺汇率不贬值,没有出口效应;第三,降低利率未能刺激起股市,利率的杠杆效应不足;第四,由于贷款主要为国有企业服务,尽管可贷资金充足,但中小企业得益不多,消费信贷刚刚起步,虽有进展,但远未达到预期;第五,降低利率,本应抑制储蓄,扩大耐用消费品的支出,但储蓄快速增长,抑制储蓄、刺激消费的作用不大,耐用消费品支出也较平稳。
课题组认为,为了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 年改行扩张政策,启动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回升,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由于政府宏观负债的增长和长期累积的问题需要解决,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在体制上又采取了一些集中化和行政性的安排和举措,形成了宏观政策的工具性扩张和体制性收缩并存的格局,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政策的扩张效应,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新的扭曲。虽然一些体制上的收缩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制度创新相配合,体制性收缩的负效应就显得格外突出。
此外,在中国具体情况下,地区差别的扩大也在制约着宏观调控的效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袁钢明以1993年下半年的宏观调控为重点,讨论了地区增长差距拉大导致经济波动加大和宏观经济调控难度增加的情况。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次大的波动周期。其中,第三个周期自1989年起。第三个周期与前两个周期相比,地区间增长率差异明显扩大,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明显增大。
“软着陆”调控的主导思想是,在控制经济趋热的同时兼顾生产供给的持续增长,随宏观经济的“热”、“冷”波动调整“紧”、“松”力度。在“软着陆”调控中,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酌情调整贷款松紧力度,对于个别地区“点贷”,应当可以起到较好的调控效果。但是,东西部地区“热”“冷”差异很大,对宏观调控的承受能力及反应能力差异很大,使宏观调控在根据经济“热”、“冷”波动进行调整的同时也受到地区“热”、“冷”差异的很大影响。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低,企业融资主要依赖国家银行。银根紧缩对西部企业的不利影响远比对东部企业的不利影响大得多。东部企业的市场融资渠道多,在紧缩情况下企业融资的调整能力较强。西部企业基本依赖国家资金,一遇紧缩便易发生资金断档、生产经营难以为继。当宏观紧缩刚使东部经济从过热状态冷却下来的时候,西部经济却已从正常增长陷入停滞衰退;而调控措施一放松,又会出现东部经济再度趋热及通货膨胀进一步蔓延。宏观调控紧不得,松不得,可调整的空间很小。宏观紧缩常常未达到预期效果便中途放松,有时不是出于兼顾经济适度增长的考虑,而是迫于西部企业经营危机的压力。宏观调控在这种情况下放弃紧缩,不是“软着陆”过程中“紧”、“松”搭配的主动调整,而是地区贫富差异及“热”、“冷”差异压力下的被迫应急措施。
为此,袁钢明指出,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扩大,使宏观调控的制约因素增多,选择空间变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需要研究调整地区发展政策以外,如何实施有效的、与市场化经济改革相协调的宏观调控,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是宏观经济研究及宏观调控操作需要重视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