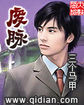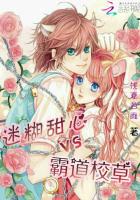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破坏了正常经济生活,迟滞了经济快速增长,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世界各国一直在致力于平抑经济波动,出台了各种政策、措施,有的举措在一定时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经济波动并没有被消除。实践证明,反周期政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经济周期可以被平滑,但是不能被消灭。政府干预作为“看得见的手”,在不同时期采取的方式不同,侧重点不同,作用效果也不同,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调整政府干预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政府调控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1年,这一时期,政府主要采用行政性指令方式进行干预,在经济膨胀过快时,采用限制基本建设投资、限制贷款额度等方法;在经济萧条时,采取扩大政府投资、放松信贷额度控制等方法。第二个阶段自1992年以来到本书出版。自从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南巡讲话以后,国家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最终确立,国家对经济周期进行调控,开始加大市场化调控方式的力度,例如采用公开市场业务、利率调节等方式。
与这两个阶段相适应,我们政府的经济周期调控方式也在发生转型。历史上,在各种反周期理论和政策主张中,凯恩斯的理论及政策影响最为深远。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说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不能自发地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市场竞争必然会产生有效需求不足,只有政府出面,推行膨胀性财政政策和补偿性财政政策,增加有效需求,经济才可能保持稳定增长。凯恩斯这套主张,一度曾经使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得到缓和,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矛盾的深化,凯恩斯主义也难以解决西方新的经济危机局面。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界和各届政府先后采用过后凯恩斯主义、供应学派、货币主义等主张,交替地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推进了反周期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稳定西方经济起到了一定作用。实践说明,包医百病的药方是没有的,适用于任何时期的反周期政策也是不存在的。人们可以采取的方针只能是吸取前人的理论和经验,因时因地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应政策措施,减缓经济周期的破坏。
反周期政策可以分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即期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是长期政策,如产业政策。1978年以前,我国对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干预,较少采用即期政策,更多的是采用长期政策。例如,在1961年的严重衰退中,政府主要是着重调整结构,在停建、缓建一大批基本建设项目,抑制投资过度扩张的同时,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结构,力求扭转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状态。计划经济时期之所以较少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较为重视产业政策,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货币信用关系不发达,行政手段更为可靠。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计划经济时期人们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经济周期,因而没有自觉的反周期意识和反周期干预动作,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储蓄和财政支出占社会总储蓄和总财政收入的比重较大,对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沈坤荣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收缩的主要行为主体。1978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财政分灶吃饭,中央财政的积聚资金作用明显下降,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明显减小。调控方式、调控手段都反映了政府在不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仅仅就紧缩银根或扩张银根来看,1989年紧缩银根采用的是指令性减小贷款额度,1993年以来就动用了利率杠杆;1991年刺激经济回升采用的是政府扩大贷款额度,1997年以来就采用了刺激投资需求和刺激消费等直接市场手段。可以预见,今后政府对经济波动的干预将更多地采取市场化手段和方式,尽可能地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的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对外开放度的提升,我国宏观调控的条件、方式、手段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刘树成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宏观调控进行了比较分析。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不同,共进行了五次紧缩型的宏观调控,时间段分别是:(1)1979—1981 年;(2)1985—1986年;(3)1989—1990年;(4)1993年下半年—1996年;(5)2003年下半年—2004年(此前,1998—2002年为扩张型的宏观调控)。与前四次宏观调控相比,第五次宏观调控在各方面都具有新的特点。
一是调控时所针对的经济运行态势不同。在前四次宏观调控中,针对的都是经济波动中已经出现的超过11%的“大起”高峰,或是通货膨胀。第五次宏观调控针对的不是经济的大起(2003年经济增长率为9.1%),不是已经出现的全面过热或总量过热,不是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而是部分行业投资的局部过热,物价上升的压力开始显现。
二是调控时的经济体制基础不同。前四次宏观调控都发生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型、但尚未“基本转型”的过程中,而第五次宏观调控则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的第一次紧缩型宏观调控。
三是调控时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不同。调控方式上,第一次到第三次宏观调控时,在最初作出调整国民经济决定的头一、两年内,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随后才进行坚决的大规模调整。第四次宏观调控时,汲取了前三次的教训,在作出治理整顿的决定后,实施上表现出雷厉风行的特点。第五次宏观调控因为见势快、动手早,所以采取的方式是渐进式的,由冷静观察、温和预警,到逐步加大力度,注意准确地把握调控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对看准了的问题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调控紧缩面上,第五次宏观调控不是全面紧缩,而是适时适度,区别对待,不“急刹车”,不“一刀切”。调控手段上,第四次宏观调控时,已改变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做法,开始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如开始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市场性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第五次宏观调控,从一开始就注重了采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同时也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四是调控时对外经济联系程度不同。前四次宏观调控国际上均不太关注,而第五次宏观调控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对外经济联系已日益扩大。2003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国。从总量看,我国的进口额只占世界总额的3.4%;但从增量看,我国的进口增量约占全球进口增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采取什么方式调节比较有效,张守一在总结以往宏观调控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一要逆调节,而不是顺调节。过去我们对经济波动一般是进行顺调节,而不是进行逆调节。在顺调节的情况下,波动振幅不是缩小,而是拉大,这是过去经济运行出现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二要掌握好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和时机。随着经济运行进入高峰期,收缩政策的力度要逐步加大,随着经济运行进入谷底,刺激政策的力度也要加大。调控力度过大或过小都不好,例如1989年固定资产投资减少了8 。0%,1990年仅增长7 。5%,说明调控力度过大,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影响。在选择宏观调控的时机上,要考虑到金融手段的时滞因素,适当提前。具体说来,在经济运行达到高峰之前,就要采取收缩政策,在经济运行进入谷底之前,就要采取刺激政策。三要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对策抵消因素。当中央政府采取调控措施时,许多地方政府采取“逆调节”措施。其原因在于两者的利益有所不同,中央政府总是把保持经济增长与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自己的双重目标,而地方政府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改善人民生活,增加财政收入,表现干部的政绩,往往把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作为自己的惟一目标。他们在长期战略确定的增长速度的基础上再层层加码,往往把高速增长变成了超高速增长。地方干部都知道“物往高处走”的道理,哪个地区的物价高,各种资源就流向那个地区,他们宁可让物价高一些,也不愿压低经济增长率。这也是间接调控措施失灵、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直接行政措施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