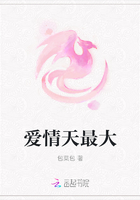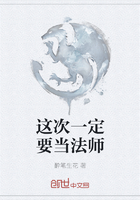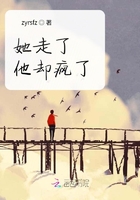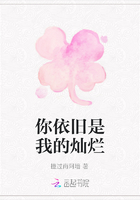传统的经济理论将经济周期划分为萧条、复苏、繁荣、衰退四个阶段,基本上客观地反映了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经济的周期波动显然出现了新的变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袁涌波、汪晓宇(2004年)专题讨论了经济全球化下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特征。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周期具有以下特征: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减小;经济周期波动发生了某些形变,危机相对温和,没有大起大落。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两个特点:一是复苏期延长,经济持续增长;二是周期特征钝化,没有强劲的高潮,也没有明显的衰退。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伴随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
袁涌波、汪晓宇指出,西方国家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减小,首先是因为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实施。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把通货膨胀视为经济发展的头号敌人,把低通胀率下的经济适度增长作为最主要的政策目标,积极而恰当地动用货币杠杆,随时根据经济增长和通胀率变化而调整利率,对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抬头,产生了根本性的作用。其次是因为产业结构进一步软化。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继续提高,且越来越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企业管理体制和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减少管理层次,实行小批量、多品种的“柔性生产”和将库存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精益生产”。
开放经济中的我国国家债务危机为什么没有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杨认为:一是自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国内储蓄剩余与国外资本大规模流入同时并存的现象,这是世界上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它是中国经济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特有现象;二是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不良资产的侵蚀以及资本外流;三是不良资产占用国内储蓄,是国民财富的净损失,它对经济长期发展影响深远;四是在开放调节下,一国政府不可能完全杜绝资本外流。政府应当做的事情是创造吸引资本在本国驻留、生根的各种环境。
2000年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收缩期,世界经济的领头羊美国经济接近衰退,日本经济低迷不振长达10年,中国经济是缘于自身周期波动的原因,即经济还没有彻底走出低谷,还是受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国经济的上升势头遭到了来自外部的打压,这一问题不仅有现实的政策含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全球著名金融机构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2003年就中国经济过热发表看法,认为中国经济2004年将出现下滑,亚洲其他经济体将因中国经济的下滑受到冲击。2003年前9个月,日本总出口的66%输往中国,韩国是40%,台湾地区是97%,东盟国家是20%~30%。2003 年前 8 个月,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占德国出口的56%,美国为21%。
北京大学的秦宛顺、靳云汇、卜永祥就中国经济周期与国际经济周期的相关性进行了专门讨论。他们在介绍国外学者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相关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并对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做一介绍,在分析了中国经济周期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问题后,指出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同步性与发达国家之间同步性存在差异的原因。
首先,他们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周期对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影响。根据 Backus,Kehoe 和 Kydland(1992年)的分析结果,可以把美国经济周期与其他国家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分为以下四种情形:一是强相关(两国 GDP的相关系数在0 。7以上),包括加拿大和欧洲;第二是较强相关(GDP的相关系数在0.3到0.7之间),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奥地利;第三是弱相关(GDP的相关系数在0 。1到 0 。3之间),包括澳大利亚、瑞典、法国;四是不相关或负相关(GDP的相关系数在0 。1以下或为负数),如芬兰为不相关,南非为负相关。
其次,他们指出,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有美国、日本等,他们分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与这些国家经济周期的关系,主要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 Fi唱nancial Statistics)的季度历史数据,时间跨度为 1987 年 1 季度到2000年 2 季度,中国的季度 GDP数据来自施发启、李强的报告(1999年)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他们采用 Hodrick唱Prescott(HP)滤波(设定参数 λ=1600)的方法对不变价格水平的美国、日本、中国季度GDP进行处理,得到 HP滤波的趋势项,不变价格水平的季度GDP扣除这个趋势项后的余额可以看作经济的周期项,计算中美和中日周期波动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 。145 和-0 。254,中美经济周期的联系为弱相关关系,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关系。中美经济周期既不如美国、加拿大那样的强相关,也不如美英那样的较强相关,甚至不如美国和澳大利亚、法国、瑞典之间的相关性。超出多数人们的想象,中日之间经济周期的走势是逆道而行的。
另外,虽然中美经济周期之间在周期转折点上相关性较强,但这种相关性是一种负向的相关性,即中国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周期并不具有同衰退、同复苏的合拍性,不能认为美国经济处在衰退期,必然会把中国经济拖入衰退期。
既然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来自内部,美国经济的衰退期到来并不意味中国经济周期的大势将被逆转,同样也不能把中国经济内部问题归结为国际因素的影响。与之相关联,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面对美国经济的低迷,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美联储2001年以来的9次降息,人民币利率还存在继续下调的空间。但秦宛顺他们认为,全球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很大,加之中国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余地已非常有限,宏观经济政策不应采取任何过激或强烈的反应,宜保持“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利率是否继续下调并不仅仅决定于是否有下调的空间,还应看到利率对广大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号作用,如果央行继续降息,等于向公众发布这样的信号,即货币当局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看好,降息对投资、消费的刺激作用远远不足以抵消因公众预期变坏而产生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