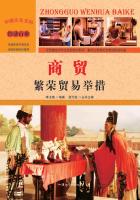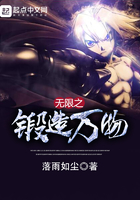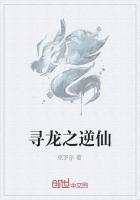陈乐一撰文讨论了经济周期运行中的资源配置失效问题。
陈乐一指出,粗放增长导致增长周期的不稳定性。经济增长率是判断周期阶段的另一个重要变量。经济增长速度可观,但增长质量堪忧。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增长的源泉是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储蓄率高,这是经济增长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劳动力和资本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少,未来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力量是技术进步。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是靠资金大投入支撑,只重视量的扩张,技术水平低,轻视技术创新,现在却面临着对技术进步越来越高的要求,这无疑是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严峻的挑战。同时,资源、环境压力也与日俱增。
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薄弱是通缩导致特种萧条的基因。国有企业3年脱困的目标虽已基本实现,但并不足以说明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当前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仍显不足,扭亏企业完全有可能大面积返亏。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脱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力度很大的政策因素的作用。解困政策除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之外,还包括诸如债转股、核销呆坏账、关闭小企业、鼓励企业兼并破产和资产重组等措施。解困政策的效力一旦释放完毕,脱困企业只怕又有可能重新陷入困境。因此,增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尚有待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经营机制的真正转变,绝对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失业率也是判断周期阶段的一个重要指标。市场经济中,失业率往往随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动而变动,经济收缩阶段失业率上升,经济扩张阶段失业率下降。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十分明显,但是就业率高度稳定,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基本无任何关系。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是末期以来,失业与周期阶段出现基本吻合的趋势。1978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高峰与经济周期的阶段并不吻合,但是,第二、三次高峰则与经济周期的阶段大体吻合。第二次高峰的 1989~1990年,中国GDP增长率分别降至4 。1%和3 。8%,陷入深深的波谷之中(即当时所谓的市场疲软)。1991年中国经济全面复苏和回升,1992年达到波峰,GDP增长率高达14 。2%。但是1993年始,经济持续7 年下滑。第三次失业高峰始于收缩阶段的第三个年头(1995年)。1995年是1993~1999年间经济增长率下跌幅度最大的一年,从1994年的12 。6%降至 10 。5%,降幅达2 。1个百分点。因此,第三次失业高峰开始于1995年,与经济周期的阶段是相当吻合的。1995年以后,失业人数逐年增加,这与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相吻合。失业率高低随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而波动,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正常现象。这时,失业率类似于物价指数,已成为宏观经济景气变动的重要信号和“晴雨表”,这也表明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大大提高。2000年,中国GDP增长率跃升至8%,连续7年的下滑趋势首次被扭转,经济全面复苏和回升。有趣的是,2000年就业局面也开始有所缓和,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国民经济主要行业160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一项用来反映企业劳动力景气的指标,在2000年上半年已经开始明显回升,并呈继续上扬趋势。再就业工程取得新进展,361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失业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吻合又一次得到证实。2000年失业虽略有缓和,但总的说来仍然相当严重,就业形势并无大的变化和起色。从周期阶段角度来分析,这是由于经济复苏的力度并不强,从而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十分有限。治理失业,提高就业弹性,需要出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配套政策,诸如小城镇建设,发展中小企业,打破行政垄断,但是,这些政策措施大都是战略性的,短期内很难见效,因此,今后几年的就业形势仍将十分严峻,高失业率将对经济进一步复苏和回升构成巨大压力。
陈乐一由此认为:加大复苏的力度,进而走向繁荣,应该是当期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只靠继续维持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远远不够,两大宏观政策工具已没有太多的调整余地,从根本上来说,是要利用复苏的机遇,全面推进各项改革。但是,推进改革,谈何容易,难以即期见效,因此,复苏走向繁荣,其道路漫长,任务艰巨,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作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战国]孟轲枟孟子·尽心上枠
作为国民经济整体波浪式运动的表现,经济周期是一种综合运动。而具体部门、具体产业、具体行业又具有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这种部门周期运动可能与整体周期发生谐振,也可能偏离整体波动。考察这些部门周期运动,对于把握整体经济波动的相关因素,发现整体波动对其他行业波动的影响也是必要的。国内学者在考察整体经济波动的同时,也在揭示具体部门波动规律,有的学者直接以部门周期波动为考察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