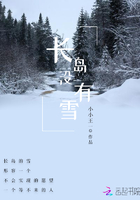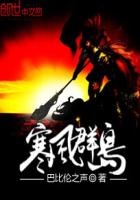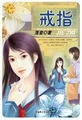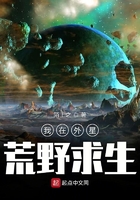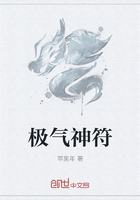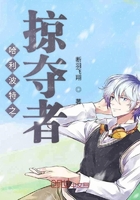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樊明太认为,经济周期波动是经济内在的传导机制和外在冲击机制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中国经济波动的内在传导机制主要包括投资的乘数-加速数机制、产业关联机制和上限-下限缓冲机制。而外在冲击机制主要包括不规则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投资政策。为此,可以证明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是有其“机制的必然性”的;不过,中国经济的强幅波动,主要是由于外在冲击机制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特别是由于财政、货币、投资政策的不规则性。
复旦大学的石磊不同意中国的经济波动具有周期性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经济波动是一种不规则波动。他的理由是,现代经济周期性波动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以大机器生产的产业为主导,一个是商品货币经济充分发展,而中国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中国不具备上述相对稳定的系统循环机制,更不存在向初始状态复归的内在倾向。石磊不同意一些作者的分析结论(栗树和、梁天征合著的枟中国经济波动与增长枠和马建堂、贺晓东、杨开忠合著的枟经济结构的理论、应用与政策枠),即中国的经济周期来自于投资周期、农业周期和政治周期。他认为,在中国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投资冲动是非规则性的,而农业波动是自然性的,至于政治波动更是非规则性的。他指出,一些论者说,从“我国屡次经济高涨几乎都能找到相应的政治背景”出发,证明“在我国,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吻合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不符合我国经济波动与政治波动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况。我们很难从某两事件中找出脱离具体经济背景的周期性规则,倒是可以从事件发生的时间间隔的不规则性和经济背景的具体性中发现不规则的经济波动引起不规则的政治波动,至于时间间隔相对规则的党的各届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是由党的政治文献所规定的,根本不反映政治波动的周期性特征,而且召开会议本身并不属于政治波动之列。
张守一在1996年提出一个理论经济学的假说:对策论、非均衡论、非稳定论、非线性论和经济周期论,表面上各自研究各自的问题,在因果关系上却存在一致性,即经济对策是因,非均衡是果,非稳定、非线性和经济周期是三种表现形式。经济对策造成非均衡,后者是经济系统中的供求关系,在供给超过需求的情况下,产出与物价逐步下降,滑至谷底;在需求超过供给的情况下,产出和物价逐步上升,升至高峰,这就表现为经济周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之间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当经济运行处于谷底或处于高峰时,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在这种情况下,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当实施宏观调控后,经济运行出现回升和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是因,经济运行是果。但是,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实际经济周期论都认为,经济系统不会产生经济周期,由于政府执行宏观调控政策,造成了经济周期。因此,在他们看来,政府政策是造成经济周期的罪魁祸首。这种看法虽然不得当,但是不排除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密切关系。
广东省委党校的张长生分析了体制改革与经济周期的矛盾,提出了“改革要有利于减缓周期性经济波动,要参照经济周期部署改革”的指导原则,并且提出根据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特点,部署相宜的改革项目。例如在所谓“升潮”起点,投资逐步增加,就业率上升,市场销量扩大,国家、企业、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逐渐提高,这一阶段是大多数改革特别是带扩张性改革出台的最佳时机。因此,可以进行较为配套的、全面的、较大的改革;“高潮”阶段,地方和企业投资增长迅速,企业拼命扩大生产、扩大销售,就业迅速扩大,市场繁荣,需求旺盛,国家、企业、居民的收入均有较大增长,但供求趋于紧张,资源瓶颈重新出现并日趋严重。这时,整个经济趋热,供求趋紧,经济形势看险,但由于被表面的市场繁荣所掩盖,不为人们所重视。这一阶段不是大规模改革的良机,尤其不能再推出刺激扩张、增加需求、提高物价等改革项目,只适于推出一些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建立和健全地方、部门、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的改革;“降潮”阶段,宏观经济总量急剧下降,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下降最甚,相当部分企业开工不足,部分企业关停并转,待业率上升,商业销售困难,通货膨胀率下降,企业亏损额增加,资金周转困难,财政赤字增加,银行利率上升。采取紧缩政策,整个经济形势看降。这一阶段只宜推进不花钱或花钱少的改革项目,可以适当推进有利于刺激瓶颈产业、短线产品增长的改革措施,可以对前期改革进行完善,可以进行风险较小的组织创新、规范市场、健全法规等方面的改革;“低潮”是经济周期的终点,在这一阶段,国民经济宏观总量已降到最低点,总供给和总需求趋于平衡,甚至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需求不足,物价水平较低,市场仍较疲软,库存仍较多,销售仍较困难,财政也仍困难,但部分企业开始更新固定资产,不少企业推出了新产品,待业率也停止上升。这时,应大胆推进改革周期较长的改革,可适当推行一些刺激扩张的改革,并积极进行改革试点,以迎接改革良机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