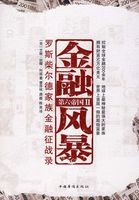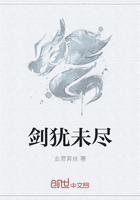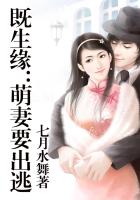1997年底到1998年初,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出来。1998年7月,面对经济增长下滑的严峻形势,我国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于同年11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以“适当的货币政策”代替“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9年初又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
张曙光认为,投资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二者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他用1979—1997年实际投资增长与 GNP实际增长作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 79 。5%,即 GNP 实际增长波动的79 。5%可以通过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 GNP更是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到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投资拉动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投资必须通过带动民营投资才能拉动经济增长。1998年,中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措施,实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扩张,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力度最强的一次。然而,扩张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样成功,这就表明,经济扩张和收缩的权力已不完全操在政府手里。那么,什么原因影响了政策效应,是政策工具性原因,还是制度上的原因?
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一直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在传统体制下,统收统支的集权式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通过财政拨款给国有企业进行投资,直接决定着经济的波动,人称为“计划周期”。随着“分灶吃饭”体制的实施,地方行政性分权的发展,形成中央、地方财政和国有企业共同分担国家投资的格局,但国有企业仍是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的主要承担者,国有投资仍是建设性投资的主体。不过,行政性分权改变了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投资的每一次扩张和收缩,不再由中央计划者单独决定,而是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共同决定,形成了投资的“倒逼机制”。1988 年的经济过热主要源于地方政府过度的投资扩张,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财力的削弱,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张主要依赖银行融资,中国经济从“计划—财政主导”进入“银行融资推进”的发展阶段。这时,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约束依然很软,经济的周期波动仍以国有部门的启动为先导。同时,市场化使非国有部门迅速发展,而非国有部门对市场的反应比较敏感。1993年7月开始的经济调整,从紧缩国有投资入手,通过拉高利率抑制非国有投资,实现了“软着陆”。间接控制似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国际经贸形势骤变,“两头在外”的战略和出口推动的模式受到严重挑战。为了重振内需,政府再次运用扩张国有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但效果递减,特别是民间投资没有跟进,增长的下滑不可避免。形势的变化使得国家再次把财政扩张和增加国有投资推向政策操作的前沿,因此,投资再次成为宏观分析关注的中心。在两次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当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当国有投资收缩结束了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国有投资是国家宏观政策操作和控制的杠杆,非国有投资基本上是随市场景气循环的变动而进退的。1998年国家再次启动国有投资,但未能及时地刺激起经济景气,这说明在制度上尚未创造出非国有部门预期的发展空间时,非国有投资的跟进是困难的。
重新审视投资、经济周期波动和体制变革三者的关联,探寻市场经济体制下阻滞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说明当时情况下,可供选择的宏观政策组合的条件和方向。
以下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波动中国有和非国有投资的作用做一比较。198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转折年,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也有人认为是货币化收益的转折(张杰,1997)。在这之前,中国经济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从1988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需求过旺,价格改革预期加强,当年通货膨胀第一次达到两位数,国家开始采取紧缩政策,国有投资率先回落,其增长速度低于非国有部门;到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回落,回落速度超过国有投资,表明非国有部门对市场反应更为敏感,预期不好就会直接减少投资。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启动,非国有投资存在着滞后反应;到1992年,国有投资仍在大幅增长,增长率比非国有投资高10个百分点。由于市场预期的拉动,1993年非国有投资大幅增长,增长率高达到72%。是年7月,国家通过减少国有投资开始宏观紧缩,国有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但经济景气还未结束,非国有投资依然较为旺盛。随着国有投资的一步步收缩,引致了非国有投资的收缩,当经济景气预期结束时,非国有投资比国有投资的下降更快,到1997年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已低于国有投资。
从上述两次经济波动看,经济增长达到9%以后,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开始超过国有投资;当经济增长低于9%时,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就要低于国有投资。9%的GDP增长率似乎成为了经济景气的判断值。这恰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相符合(左大培,1998年)。据世界银行计算,从1979—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9 。1%,其中46%来自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制度改革的结果(世界银行,1998年)。从增长指标看,9%是目前中国经济景气循环的界限,但从深层次看,经济增长达到9%以上都有巨大的制度变革发生。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实现了两位数的高增长,1989年以后,体制收缩,经济景气降至9%以下。1992年邓小平南巡,市场化改革加快,带来了经济景气预期的上升,经济增长再次达到和超过潜在生产能力。如果缺少制度变革,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大致在5%的水平。可见,中国市场化的空间还很大,增长的潜力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