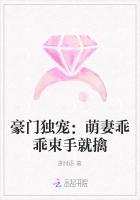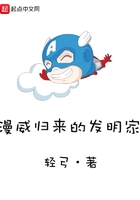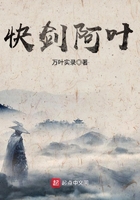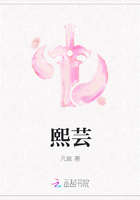当时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调研组任职的卢建(1987年3月)以“我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原因及发生机制分析”为标题撰文,认为投资的周期波动必然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但是,不同历史阶段,投资周期的形成和经济周期的发生机制是不尽相同的。在单一计划经济阶段,投资周期的形成,基本上可以归结为高度集权的行政决策的周期变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生产决策权和投资决策权出现了多元化趋向。1987年第7期枟经济研究枠刊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的文章“改革中的宏观经济:国民经济的增长与波动”。文章集中讨论了工业波动和农业周期的成因。文章认为,在1979年以前,国民经济波动的主导因素是供给方面的。1979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需求的大小成为决定国民经济短期波动的主导因素。当时中央党校在读博士生方加春(1990年)认为,在对外贸易和经济开放的条件下,一国的经济活动可能通过进出口贸易,通过开放经济国家的对外贸易的干扰,汇合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内资源配置的内在缺陷,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的连锁反应,形成对该国国内经济系统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还会通过世界市场价格的变化,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国际人才流动的渠道,以及外债规模等方面对国民经济产生影响。程小农、宋进攻(1989年)不同意用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农业自然周期、货币变动以及价格变动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周期。他们认为整个国民经济是一个大系统,体制、结构、总量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了经济运行过程本身存在着增长中的扩张和收缩机制。并且,他们还认为,宏观调节(包括经济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并不是置身于经济系统之外,并从外部影响经济运行过程,宏观调节本身就是经济系统运行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注意到了投资波动对经济波动的直接诱导作用。回归分析的结果:S=3.9+0.3I,说明投资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投资每波动1%,经济增长将波动0.3%。至于投资周期波动的根源,多数人认为,从生产关系上看,主要源于传统的高度集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计划指令、信号系统纵向配置,投资权乃至企业生产决策权也集中在中央。于是中央的政策周期或政治周期直接转化为全国性的经济涨落。服从于政治需要,计划部门经常产生数量冲动、投资冲动,拟以高指标、高增长实现计划目标,直至比例失调、严重短缺,才被迫压缩投资、收缩战线,稍有缓和又旧态复萌。此外,传统体制下非价格原则和软利益约束,导致地方和企业也不断滋生投资饥渴,于是高指标、高积累—比例失调—调整—再冲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据马建堂测算,我国的经济波动与投资波动存在着惊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 。90以上),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产业结构的机制中,投资波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在投资高涨期,建筑业、设备制造业急剧扩张,加工工业与基础产业间的失衡加剧;而在收缩期,由于投资的萎缩和投资品需求的迅速下降,建筑业、设备制造业增长放慢,它们在整个产业中的比重下降,加工工业与基础产业间的失衡状态有所缓解。但由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几次超前转换、生产要素存量结构的刚性,以及缺乏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协调结构偏差的机制,我国经济周期中产业结构的变动一方面比较剧烈,另一方面又不能在收缩阶段调整到位,从而经济周期中的产业结构变动又具有周期性失衡的特征。要解决我国产业结构的周期性失衡,一是要通过出口结构的高度化建立起有效的结构偏差协调机制;二是通过建立资产、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和促进企业间的新陈代谢形成存量结构的转化和调整机制。
不少人注意到,近些年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生产决策和投资决策出现多元化趋势,在中央决策依然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企业计划外行为和市场收益预期,对经济涨落影响愈来愈大。
对于经济波动的物质技术根源,杜辉、杨青等人明确提出固定资产更新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基础。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固定资产周期性退役报废高峰,是引起周期性投资高峰和增长高峰的物质技术动因。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又将固定资产更新分为四种周期:投资周期、投产周期、周转周期、替换周期。如能透彻地揭示出我国固定资产更新的规律,势必可以把中国经济周期研究大大深入一步。遗憾的是,限于我国统计资料的缺陷,至今没有重大突破。
综合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诸因素,有人将它们概括为制约经济周期的内在机制,其周期性扩张机制包括投资乘数效应、结构校正效应、总需求扩大效应和体制改革释放效应等,周期性收缩机制包括固定资产周期性减退机制、部门滞后机制、技术更新机制和总量失衡机制等,两类机制交替作用,制约经济周期性涨落。
上述分析都力图证明“天灾人祸”不是经济涨落的根本原因,虽然它们的发生有可能导致经济波动的提前或延缓、强化或弱化,但体制运行机制和大生产运行节奏才是决定因素。因此,中国经济周期是有规律可循的。今后对中国经济波动起因的研究似应对技术创新周期、产业兴衰周期加强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