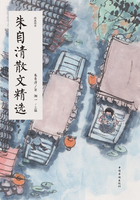在见到他的塑像之前,我们早已经知道他的事—在几千年以前的一个夜晚,也许有一点冷风,冷风里夹杂着秋天的冻雨,风里也有风尘仆仆的长途旅行者的气息。他们从前线应召回朝,中途歇息,那些随行的军士默默地跟从他们。父与子下马离镫的一瞬,马忽然没来由地嘶鸣起来,鼓起的眼泡和张大的鼻孔都呈现惊愕的表情!凭借多年来的战事经验,他们当然也在私底下嗅到了一股不祥的气味。
那十几名军士背上的兵器冷冷地,月光下冒着寒光。他们的命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当然也有他自己的命。“回去吧,帅。”他们忧心忡忡的眼神和深沉的脸被尘土和疲惫覆盖,从不同角度试试探探地朝向他。事情明摆着,回来就是将高贵的生命投送到粪土与败类的腻歪中,零零碎碎地屈尊,失去男人的体面。
“回去吧,父亲。”儿子说,“趁这里距京城尚远。”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几千年之后,人们站在他的墓前,试图理解他的心。他当时的思虑究竟是怎样地勾回呢?往往,人性在客套和平庸中都显得彬彬有礼,但在最尖锐的矛盾中才呈现最后的本真。他的灵魂、性情、信仰、抉择和取舍,是怎样经过了几百几千回的博弈和锻炼,才在十二次召回的阴险通知之后,在最后的一刻,驱使他踏上赴死之路?
他的军队黑压压的一片。那些旌旗和兵器没有了统帅的命令,都显得有些垂头丧气。他们才是他的亲人和家园啊,他在他们中间才可以驰骋和欢悦啊。像树在森林里,像水在山泉里。脱离开他们,他的生命的蛋壳就显得薄和脆,会被一些陌生人蹂躏和糟蹋。那些人会充分利用朝廷的规则折磨他,使他难受。他在金国人面前的赫赫战功非常妨碍他们的心情。他难道不知道,他的存在就是一个威胁。对于君主来说,忠贞的心看不见也摸不着,而局势是可以想见的。那些他所终生努力的事业,在他们看来,不单是无关要紧的尘土和风月,更是插在他们肉里的利刃。他是一军之帅,他难道真的不明白这一点?回去凶多吉少,在命与一些规则之间,他怎么会选择了一个软件?!
“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空悲切。”也许在他少年的记忆中,有一种记忆被命名为忠诚—为了一个国家的荣誉,也为一个人。多少年了,两者合而为一,国家是以那个被称为帝王的人为图腾和象征的。于是忠诚就成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信服和听任。才华、情感、韬略和性都不重要,命令和规则是空前的。在那些暗红的城墙深部,是华丽和繁华的宫殿。那么雄伟和不可侵犯,不可知,不可测。宫殿外面有那么多令人眼晕的台阶和等级。秩序,是这里唯一的语言。它将人的血脉一切两断,不留一点情面。而小人们恰恰利用了这一点。
他抉择的最后时刻,如果他的母亲还在,会劝阻他,还是鼓励他?
事情紧张起来。在汤阴岳王庙的草地上,风那么好,阳光那么妥善,墙壁粗糙,石凳安闲。人们不愿意想象他被折磨时的惨烈,也不能体会他当时心情的恶劣。他们激烈地讨论着衣冠冢的存放省份问题,遗址的修缮问题,空气的湿度问题,历史细节的考证问题,等等。那些辽远的话题与他的心事无关。冤屈就是一个人虽然没有被堵上嘴,但是语言全无用处。他和他的儿子都曾经是烈兽,是猛虎,是图腾,像鹰一样呼啸,像浪一样席卷和奔腾,像狼群中的头狼,牙齿锋利,威武无比,一呼百应。怎么就瞬间被剪了羽翅,屈就在一间茅草屋里。他们的血羞辱地流向湿地,骨头几乎被刑具压酥了。他们虽然靠信念和意志硬挺着,但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使他们痛苦得咬碎了牙齿,唇边的血殷红了垂下的乱发。
他们此刻不能杀人。在疆场上,手起刀落,那些冷兵器作用于人体造成“噗噗”的声响、血花飞溅,曾经使他们何等快意。但那些是侵犯的敌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阴匈奴血。”战场上的逻辑是清晰的,单纯的—我与敌人,杀与被杀,胜与败,追击与逃跑……虽然也会有冷箭,但军人们对局面了如指掌。而现在,英雄们处于他们完全陌生的阴霾里,那是他们的不擅长—能够感觉到阴谋家们的暗中推手却看不见他们,需要对君心反复地揣摩和期待,面对的“莫须有”的罪名认与不认都是错误,男人的力量完全派不上用场。进退两难,举目四野,四边全是黑暗。与其这样活着,真不如死了痛快。
悲剧是选择决定的,选择是意识决定的,意识是命运决定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性格是什么决定的?是历史吗,是风吗,是少年时代母亲的话语吗?
他们不知道,在几千年以后的若干时段,冤屈时时上演。他的故事换了装束,换了缘由,换了主角,依然不绝于世。比如“文革”。许多人如他一样惨。唯一不同的是:他是一个人和一个家族,但他们是一群人,一代人,是成千上万的家庭。这样的不平的事情一直持续了十年。十年之后,那些被恶之刀锋腰斩的人性和道德再被接续的时候,出现了令人惊讶的畸形,毒素在看不见的地方蔓延。人们习惯了攻歼和撕咬,以为动物生存的原始规则,也是人类生存的必须。
我不能够看见那些猛虎被人圈养在动物园里的惨景,也不能看见孩子被父亲打而无力还手的眼神。我不能够看见那些无辜的难过和没来由的伤。就是由于愚昧、自私和狠心肠吗?据说,历史常常由恶人推动着。动物界中,谁的牙齿锋利、四肢粗壮,谁就能活得好一些,拥有的异性多一些。据说,人类的文明超越了动物的原始性。这是人之为人、区分于动物的分界,是高级人区分于低级人的标志。所谓文明,就是以规则维护生命的权利、生存的权利、尊严的权利,就是对恶的限制和对善的哄护。几千年之后的微雨的这一天人们想起了一种叫做物质规则的法制和一种叫做精神规则的道德。光靠那些诠释生命存在的哲学是不够的,哲学往往都是最空洞和苍白的。岳飞庙前的石壁强调了这一点。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悲情故事。切·格瓦拉也是这样。他在玻利维亚的游击战后期那么沮丧。他被叛徒出卖,他被一些平庸的人俘虏、折磨和羞辱。他奋起反击不让他们打他的脸,而他们先打断了他的腿。他被枪杀以后,神态是安详的,像个孩子,雪茄和军帽也失去灵魂—从审美角度看来,他的生和死那么震撼与美丽。戏剧和小说最爱干这种事情—讴歌失败的强者,聚光被糟蹋的美丽,记录曲折的悲剧,反复吟诵着被命运玩弄的才子佳人故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大历史中间,他们以生命为代价点缀着精神世界的夜空。在冤魂四野的世界里,在极端的两极中,你选择伤逝的审美,还是不择手段的存在,还是不惜代价的逃亡?在命与规则中,你选择硬件和还是软件!
在世界上的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条街道的一个角落—汤阴的岳飞庙—我们的人环绕着里面的每一间房屋,复印着历史的生硬的记忆。因为同是生灵,所以感同身受。窗外的一树高高的花开着,香着,美着。穿梭着绿色中间的人们默默行进。有一间是他的小女儿的。那个孩子知道父亲的冤死,就在十三岁上结束了自己。“真是烈女。一家都忠烈!”同行的人说,咬着牙槽,绷紧嘴。当时的太阳浓烈得要命,我们低着头看见自己树下的影子,历史就在瞬间恍惚起来。我在这个时候总是看见人生的悲观一面。
岳王庙外边,就是一条繁华的县城街道。有灰色的墙砖,有小摊,过路的行人横七竖八,没有规律。汽车的喇叭声尖厉。“让开,让开。”那些官员们的司机冲行人们嚷着。岳王庙里面,人们讨论中,罪人们跪在地上。有人朝秦桧吐唾沫,然后以手做千夫所指状,照相留念。
在慌乱的街道上,有一个孩子张着手跑过来。世界还在按照一种逻辑运行。
记得一个土耳其作家说,动物最重要的有三件事:食物、地盘和性。而人类把它们美化为另外三件事:金钱、权力和爱情。说得真对。生存是绝对的真理吗?否则为什么人们注重食物、钱、职位、运程,否则为什么有算卦和占卜,无非是要生存和生存得好一点吧。生存高于一切,这是一条绝对的真理。马克思也说过“生存决定意识”的话。
这一座叫做汤阴的城,存留着一个英雄的遗迹,流传着他的故事。许多人来,许多人走,许多人看他念他思考他钦佩他,许多人忘记他,回到自己生活的洪流和旋涡中去。如果关于他的传说,能在人们抉择善恶的时候演化为一个砝码,影响了今天,增加一些厚道和良善,减少一些奸佞和阴谋,他也不枉一死,人也不枉一悲。审美只有在发挥作用之后才显示力量。
当我们离开,这座城市在火车的呼啸声中越来越远的时候,黄昏渐冷。情人们,请珍重加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