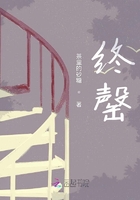我的摇篮靠着书库——这阴森森
巴贝尔塔,有小说,科学,词话,
一切,拉丁的灰烬和希腊的尘,
都混和着。我像对开本似高大。
两个声音对我说话。狡狯,肯定,
一个说:“世界是一个糕,蜜蜜甜,
我可以(那时你的快乐就无尽)
使得你的胃口那么大,那么健。”
另一个说:“来吧!到梦里来旅行,
超越过可能,超越过已知!”
于是它歌唱,像沙滩上的风声,
啼唤的幽灵,也不知从何而至,
声声都悦耳,却也使耳朵惊却。
我回答了你:“是的!柔和的声音!”
从此后就来了,哎!那可以称做
我的伤和宿命。在浩漫的生存
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所在,
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世界,
于是,受了我出神的明眼的害,
我曳着一些蛇——它们咬我的鞋。
于是从那时候起,好像先知,
我那么多情地爱着沙漠和海;
我在哀悼中欢笑,欢庆中泪湿,
又在最苦的酒里找到美味来;
我惯常把事实当作虚谎玄空,
眼睛向着天,我坠落到窟窿里。
声音却安慰我说:“保留你的梦:
哲人还没有狂人那样美丽!”
编后记:对于我,翻译波特莱尔的意义有这两点:
第一,这是一种试验,来看看波特莱尔的质地和精巧纯粹的形式,在转变成中文的时候,可以保存到怎样的程度。第二点是系附的,那就是顺便让我国的读者们能够看到一点他们听说了长久而见到得很少的,这位特殊的近代诗人的作品。
为了使波特莱尔的面目显示得更逼真一点,译者曾费了极大的、也许是白费的苦心。两国文字组织的不同和思想方式的歧异,往往使同时显示质地并再现形式的企图变成极端困难,而波特莱尔所给予我们的困难,又比其他外国诗人更难以克服。然而,当作试验便是不顾成败,只要译者曾经努力过,那就是了。显示质地的努力是更隐藏不露,再现形式的努力却较容易看得出来。把alexandrin,décasyllabe,octosyllabe译作十二言、十言、八言的诗句,把 rimes suivies,rimes croisées,rimesembrassées都照原样押韵,也许是笨拙到可笑(波特莱尔的商籁体的韵法并不十分严格,在全集七十五首商籁体中,仅四十七首是照正规押韵的,所以译者在押韵上也自由一点);韵律方面呢,因为单单顾着pied也已经煞费苦心,所以波特莱尔所常有的rythme quaternaire,trimétre便无可奈何地被忽略了,而代之以宽泛的平仄法,是否能收到类似的效果也还是疑问。这一些,译者是极希望各方面的指教的。在文字的理解上,译者亦不过尽其所能。误解和疏忽虽竭力避免,但谁知道能达到怎样的程度?
波特莱尔在中国是闻名已久的,但是作品译成中文的却少得很。散文诗Le spleen de parris有两种译本,都是从英文转译的,自然和原作有很大的距离;诗译出的极少,可读的更不多。可以令人满意的有梁宗岱、卞之琳、沈宝基三位先生的翻译(最近陈敬容女士也致力于此),可是一共也不过十余首。这部小书所包含的比较多一点,但也只有二十四首,仅当全诗十分之一。从这样少数的译作来欣赏一位作家,其所得是很有限的(因而从这一点作品去判断作者,当然更是不可能的事了),可是等着吧,总之译者这块砖头已经抛出来了。
对于指斥波特莱尔的作品含有“毒素”,以及忧虑他会给中国新诗以不良的影响等意见,文学史会给予更有根据的回答,而一种对于波特莱尔的更深更广的认识,也许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见解。说他曾参加二月革命和编《公众幸福》这革命杂志,这样来替他辩解是不必要的,波特莱尔之存在,自有其时代和社会的理由在。至少,拿波特莱尔作为近代classic读,或是用更时行的说法,把他作为文学遗产来接受,总可以允许了吧。以一种固定的尺度去度量一切文学作品,无疑会到处找到“毒素”的,而在这种尺度之下,一切古典作品,从荷马开始,都可以废弃了。至于影响呢,波特莱尔可能给予的是多方面的,要看我们怎样接受。
只要不是皮毛的模仿,能够从深度上接受他的影响,也许反而是可喜的吧。
译者所根据的本子是一九三三年巴黎Editions de cluny出版的限定本(Lo Dantec编校)。瓦雷里的《波特莱尔的位置》一文,很能帮助我们去了解波特莱尔,所以也译出来放在这小书的卷首。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