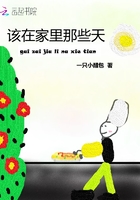法国瓦雷里
古修辞学将诗的继续的洗练所终于显示为诗的目的的本质的那些诗藻和关联,认为是装饰和矫作;而分析的进步,却总有一天会发现它们是深切的特质的效能,或那可称为形式的感受性的东西的效能。
两种韵文:已知的韵文和计算的韵文。
计算的韵文是必然地在待解决的命题的形式之下表现出来的那些——它们的主要条件第一是已知的韵文,其次是已经由这些已知量所包括的脚韵,章法,意义。
即使在散文中,我们也往往被牵制着被勉强着去写我们所不愿写的东西。而我们之所以如此做者,是为了我们所曾愿写的东西要如此。
韵文。模糊的观念,意向,无量的意匠的冲动,撞碎在有规律的形式上,习例的韵文法的难以战胜的禁令上,孕成了新的东西和意料之外的辞采意志和情感之与习惯的无感觉性的冲突,有时会生出惊人的效果。
韵有着这个大成功:那便是使那些愚蠢地相信天下有比习例更重要的东西的单纯的人们发怒。他们有着这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某种思想可能比任何习例……更深长,更经久……这并不是韵的至少的愉快,为此之故,它最不温柔地悦耳。
韵——形成一种对于主题独立的法则,而可以与一口外表的时钟比拟。
意象之滥用,繁杂,对于心的眼睛,发生一种和调子不相容的骚乱。在万花缭乱中一切都变成相等了。
作一首只包含“诗”的诗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首诗只包含“诗”,它便不是作出来的了;它便不是一首诗了。
幻想,如果它巩固自己而支持一些时候,它便替自己造出器官,原则,法则,形式,等等;延续自己的,固定自己的方法。即与被调协起来,即兴之作被组织起来,因为没有东西能够存在,没有东西能够确定而越过瞬间,除非那结算诸瞬间所需要的东西是被产生出来。
韵文的品位:一字之缺就妨碍全部。
记忆的某一个混杂产生了一个字眼,这字眼并不是适当的,但却立刻变成了最好的。这个字眼创了一种流派,这种混杂变作了一种体系,迷信,等等……
一种令人满意的修正,一种意外的解决显露了出来,——全靠了在那不满意而舍置在一边的稿纸上的突然的一瞥。
一切都觉醒了。以前没有着手得法。一切都重复生气勃勃了。
新的解决透出一个重要的字眼,使这字眼自由——好像下棋似的,一着放了这“士”或这“卒”,使它们可以活动。
没有这一着,作品便不存在。
有了这一着,作品便立刻存在了。
当一件作品的完成——认为它已完成的判断,是唯一地依附于它讨我们喜欢这条件的时候——这作品是永远没有完成。
比较着最后状态和终结状态,novissimum和ultimum的判断,有一种本质的变迁。比较的标准是无常的。
成功的东西是失败的东西的变形。
因此失败的东西只是由于废弃而失败的。
作者方面。别说。
一首诗是永远也不完成的——往往是一件意外结束了它,那就是说把它拿出去给读者。
那便是疲倦,出版者的要求,——另一首诗的生长。
可是(如果作者并不是一个痴人)作品的现在状态永远并不显得它是不能生长,改变,被认为最初的近似,或被认为一个新的探讨的出发点。
我呢,我以为同样的主题和差不多同样的字眼可以无穷尽地拿来再写而占据一生。
“完美”便是工作。
如果人们想得出创造或形式的采用所需要的一切探讨,人们便永远不会愚蠢地拿它来和内容对立。
因为处心积虑要使读者的分子尽可能地少——并甚至要自己尽可能少地剩下游移和任意,人们才趋向形式。
坏的形式便是我们感到有更换的需要而我们自己更换的形式;我们复用着,模仿着而不能变得再好一点的形式,便是好的形式。
形式是本质地和复用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新的偶像崇拜,因此是和形式之关心相反的。
真的和好的规则。
好的规则便是那些重提起最好的契机的特质并强使人用它们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从对于这些顺当的契机的分析中取出来的。
这是对于作者的规则,尤甚对于作品。
如果你是常常有识别力的,那么就是你从来也没有冒险深入到你自身之中去。
如果你没有,那么就是你曾冒险深入而一无所得。
一件作品的每一个部分都应该“动作”。
一件作品的诸部分应该由许多条线索互相联系着。
定理
当作品是很短的时候,最细小的细部的效果之伟大是和全部的效果之伟大相同的。
凡有一个可以用别的文章来表现的目标的文章,是散文。
对于作者的忠告
在两个字眼之间,应该选最小的那个。
(这小小的忠告,但愿哲学家也接受。)
(载《新诗》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七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