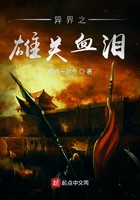顺帝至元十三年,春。
沙砾和粘土在千万年来风雨时光的锤击下,化成一段段坚地,万马踏上去蹭蹭作响,马蹄下是稀稀落落的篙草、鹫苇草,这里是蒙古人口中的“荒凉沙湾”,位于杭爱山和阿尔泰山间,无数年来,悠远贫瘠荒凉是这里永恒的主题。而此时,却多了一只延伸到天尽头的苍莽铁骑。
万千旌旗遮蔽了视野,在风中轻微招展,烈烈作响,大军全副仪仗,整肃缓行,一路向西。
在大军的中间,是一辆无与伦比的大车,大车由百匹一色的白马拉扯,气势雄礴的无与伦比,车上是一个蒙古式的毡包,毡包鎏金,远远望去,仿佛天地间多了一顶缓缓移动的金色宫殿。
这座被皇帝钦命为“金狼”的华盖大车,是由皇帝亲手设计,再命人施工建成的,他则在一旁当起了监工,这几乎成了皇帝整个冬日里除了玩女人,唯一的乐趣了,再一次向天下验证他“鲁班天子”的不世糗名。
这座移动的宫殿,被三千铁甲骑士簇拥,整个蒙元帝国的重臣贵族云集,若此时天降陨石砸中此车的话,相信整个大元天下立马陷入群雄割据,相互攻伐的乱世。
“金狼”车内,顺帝拖地妥懂·帖木儿高居首位,睥睨四顾。
自西行起,皇帝便陷入了不绝的兴奋中,他在巨大华丽的“金狼”大车里不断的听着帝国重臣大贵族们的奉承,自继位以来,他何曾受过如此拥戴奉承,这种一睁开眼就被各种各样的吉祥话和谦恭讨好的笑脸包围,哪怕初始皇帝在心里告诉自己,他们是在故意讨好你,在拍马屁,他们心都不在皇家,你要小心,不要被他们虚假的面孔迷惑啊。可是人啊,哪有不喜欢谄媚的,日子久了,同样的话听的多了,多到脑袋和耳朵一起结茧子了,渐渐的,皇帝眼里的戒心越来越虚弱,骄傲自大的笑声倒是洪亮起来了。
那笑声中,早已忘记了昔年自己跪在狼臣脚下被怜悯的悲哀,有的只是大元天下远超古今的广袤疆域,只是他是苍穹下唯一主人的那份骄傲,在他的眼中,所有人都变成了一种人,芸芸众生,明眼人一看便摇头失笑,区区奉承,竟使这个之前还曾有几分血勇骨气的皇帝飘飘然,“金狼”大车,他是真把自己当作神了啊。
……
……
“去年九月,我的儿女奴伦,于察罕尔家玩耍时被人掳走,朕曾一时糊涂,竟想诛杀察罕卿,如今想来真是汗颜的很,来,请爱卿满饮此杯。”巨大的金狼毡包内,顺帝早已没了当初的锐利戾气,熏红的脸上满是酒渍油光。
金碧辉煌的大车内,年过五旬的李察罕抱爵而起,他一领红黑披风,扎着蒙古人常见的麻花辫,连鬓胡须,倒刺而生,气度威猛,他是车内里年龄最长,掌权最长,只是到底年纪打了,发已白,刀痕似的皱纹,惊心动魄,纵横交错,这是一个已经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土里的老人,只是那双显得有些狭长的眼睛,还是很年轻时一般,锋利如刀。
“老臣李察罕万死难救其过,我大元帝国从一代天骄横扫天下以来,历时百年,从未有过帝国公主被人掳走,老臣深感愧对皇上信任,给祖宗之血蒙羞,万死难辞其咎啊。”
李察罕说着,竟痛哭流涕,伏地大哭,哭声悲怆难耐,声震人心,皇帝大为动容,竟离座扶起这个手握数十万悍勇大军的重臣,好一番安慰,方作罢。
目睹这君臣相宜,和睦相亲一幕的那些大贵族,蒙元帝国的将军重臣们,却自顾自吃肉喝酒,竟是不约而同的冷笑。
“万死难得其咎?李察罕啊,你名字改成汉名了,现在连虚伪也如汉人了,万死甚么的就不必了,若真心想死,一次便可了,”李察罕家天生的死对头孛罗嘿嘿冷笑,随手扔出手里银光森冷的小刀,“不嫌弃就用我刀吧,我不嫌弃你的血污了我的刀。”
王保保重重的放下自己的酒爵,“砰”,对面的孛罗眉眼微挑。
“闭上你的臭嘴,大家还在用食,不想闻你的狗屁。”王保保冷冰冰的哼着。
孛罗勃然色变,拍案而起。
“两位爱卿都是我之臂骨,理应一同打理我大元天下,纵使有甚么分歧,也当静下心来细细讨论,且不要动刀动枪嘛。”
皇帝乐呵呵的劝着,一脸幸灾乐祸,对所谓的“左膀右臂”的内斗,欣然无比。
正是焦灼时刻,车外入口处,司礼大臣悠扬高宣:“丞相脱脱,皇太子殿下求见!”
“哦,丞相和皇儿来了,让他们见来吧。”
“是。”
见跟自己不对路的丞相和皇太子来了,孛罗憋屈的哼了一声,腾的坐下来,一口把酒杯里的酒倒进嘴里,怒气冲冲的把酒爵拍在案前。
司礼大臣引导着丞相和皇太子不如金狼毡包。
脱脱还是那一副德性,身着花花绿绿的丞相官服,头戴白玉冠,面色枯黄的悠悠而来,对这个丞相,皇帝是打心眼里尊重的,近些年朝政能一日好似一日,多亏他的维持,只是私下里,皇帝确实不太爱见这位丞相,实在那张终日愁苦的老脸,看久了太扫兴了。
而与脱脱并肩而立的正是当今奇皇后的长子,大元的皇太子殿下,想必脱脱的面苦似头陀,这个年轻的皇子倒是一身的矜持气度,踏着极度有节奏的步伐,高高的蓝玉冠,目不斜视,坦然直入大帐,随意打量着群臣看过来的复杂目光,嘴角永远挂着着轻蔑的笑意,只是在看见一身白衣,恰似卿相的王保保时,嘴角的弧线倒难得的柔和了三分。
“臣见过陛下。”
“儿臣见过父皇。”
“不必拘礼,入座吧。”
“是。”
皇太子爱猷识(全名:爱猷识理答腊)坐下来,身手不动,旁边自有侍女将案前肉切好递于起口中,他细嚼了几口烤鹿肉,嘴角一撇,盯着对面的孛罗悠然开口:“刚才在外面,远远就听孛罗将军要李察罕将军自裁,不知本太子可曾听错。”
“说笑而已,太子殿下不必在意。”孛罗冷冷的说。
皇太子最腻歪这个孛罗,冷冷哼了一声:“说笑?若是我父皇说笑让你自裁,不知你自裁还是不自裁,也以为这是笑话?”言外之意明显不过,你孛罗就是一乱臣贼子。
皇帝很怕惹怒了这位同样手握重权的大臣,笑着圆场:“好了,到此为止了,一句玩笑话,怎么老抓着不放啊,太子,你是大元储君,要有朗阔天下的气度。”
“父皇明鉴,儿臣同样只是开个玩笑。”皇太子笑了声,没在说话了。
李察罕自始至终只是悠然饮酒,似乎一切都与他无关,一言不发的看着场中微笑,等太子玩笑过后,他才朝下座自己的养子王保保递过一个眼神,对他结交皇太子甚为满意。
丞相脱脱起座:“汉人常说国不可一日无君,然陛下为了寻奴伦公主西行北疆,唯恐朝政在陛下离开时皇妃,以老臣愚见,此次北疆之行还需双管齐下,一则呢,陛下通告北疆各族,但有发现奴伦公主,及时通报的,朝廷与其官爵金银,任其所取;二则,李察罕祖籍北疆,当有不少亲朋故友,也当策动,如此只要奴伦公主确实在北疆,旬日便会被发现,到时以我雷霆之师,顷刻便破,也好解救公主,早日还朝。”
“你说的也有道理,就按你说的办吧,李察罕,没问题吧?”皇帝好言问道。
“秉陛下,犬子保保日前已经发动李察罕家在北疆的势力,相信等我们到北疆之日,便有消息了。”李察罕说道这里顿了一下,然后激动难耐,胡子发颤:“到时老臣亲自为陛下斩贼,以正老臣清誉。”
皇帝兴奋的举杯:“列位,为李爱卿宝刀未老,请满饮此爵。”
“干——”
皇帝仿佛想起了甚么,满脸笑意的看着皇太子:“为何你母后不曾过来啊,朕还等看她新编的胡璇舞呢?”
“回父皇,母后说她长途旅行,身体稍有不适,在自己的车内歇息,让父皇不用担心。”
“唉,可惜了,回头朕去看看。来来来,歌舞姬呢,不能没有张屠夫,就吃带毛猪,没了奇皇后,就不看歌舞啊。”
这句粗话,顿使这些骨子里本来就粗俗透顶强壮大雅的蒙元贵族大臣将军们惹得哄然大笑。
只是下面的脱脱摇头一叹,一国之母,如此糟践,唉。
至于皇太子,面色复杂难看至极。
……
……
皇后的香车内。
一阵低沉的笑声隐隐传出,那笑声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三个人的。
隐隐约,竟像是一女二男。
如果此时有灯光便可看见,黑暗里,车内两个身影正一前一后的躺于奇皇后的身侧,皇后一身华贵衮服早已经脱得干干净净,她****着玉体,娇哼哼的被两个男子夹在中间,任他们肆意的在自己香唇雪白躯体上亲咂,鼻腔间的呻吟声绵延不绝,娇躯扭动,颤抖地迎合着两人的动作,胯部撞击雪白裸体,啪啪有声,此起彼伏。
过了一会,几乎是同一瞬,那两个粗俗的男声一下子断了,奇皇后也长吁了一口气。
一阵“索索”声响起,像是有人在穿衣,过了片刻后,车帘被掀开,从车内走出两个衣衫不整,一脸红光的两个男人。
皇后香车旁是宫里的侍卫和宫女,只不过每个人对此都视若无睹,似乎司空见惯,甚么也不曾听见看见。
那两个男人,其中一个头上寸草不生,一身红色袈裟,看其相貌,乃是一个吐蕃和尚。
另一个,也不简单。
“国师,本宫一路颠簸,这两日身体不甚康健,你明日再来为本宫整治一二吧。”
国师闻言贼眼眯成一条细缝,喜笑颜开:“皇后娘娘,但有所命,贫僧敢不屈从,阿弥陀佛。”
“莫非娘娘嫌弃为臣了,也不叫为臣明日过来。”
车里那个曼妙的声音又响起,异样的魅惑:“中书右丞大人若是有空,但来便是,只是万一被你那个老对手发现,我倒是不怕甚么,右丞大人危矣。”
哈麻(蛤蟆?)的脸冷了下来,昔年,脱脱曾一度恢复汉人科举,博得了一个“贤相”之名,汉人士子赞其有国士之风,让哈麻大为嫉妒,脱脱也不是仁厚之辈,后来看出哈麻心怀不甘,干脆把他调为宣政院使,让他堂堂一个中书右丞当了刀笔吏,从此以后,脱脱一直被哈麻视为欲处置而后快的眼中钉,如今听皇后如此一提,那憋屈的邪火又窜了起来。
“等着吧,臣总有让他哭的时候。”
车内那个女声好似听到一个笑话,咯咯的笑起来,这让哈麻脸色又一变,以为她在嘲讽自己,暗道明日非******这****不可。不过对自己能够皇帝戴上一定大大的绿帽子,哈麻还是得以非常的。
“大师,回头你那个龙虎金丹可得给我留几枚。”
“好说好说。”
两人心照不宣的呵呵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