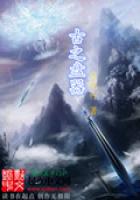慕夫人果然开始为安常大人物色佳偶,阳京府又掀起了不小的骚动。安常大人在慕夫人面前态度不冷不热的,慕夫人在苏信春面前说:“好好劝大人,他是懒怠惯的,对正事向来不上心,尤其是关系到自己身上的事。原以为皇上会指婚,哪里能想到他这个脾气,肯定对皇上说了什么。现下要寻一段美满姻缘,靠我一人怎么能行呢?你日日跟在大人身边,知不知道他可有爱慕且尚好的人?”
“大人日理万机,也鲜少出门,说爱慕的人恐怕没有。聘求夫人是大事,由您出面想必大人非常放心。只是——对于婚事,夫人,信春有话要讲。”
“孩子,你直说就是,大人的事你没有藏着的必要。”
“大人的心思是否曾告知过您?”
“怎么,他和你说了什么?”
“并没有,信春也无法忖度,只是想大人心思有他,恐怕有事在怀难以释然,若夫人知晓,或许能解之。”
慕夫人听苏信春讲到这里,便默然无语了,自己呆呆坐了半晌,才叹口气,让苏信春回去了。
苏信春眼看安常大人要有新夫人了,不晓得自己将来怎样处在他身边。若新夫人贤德宽厚,容她继续伺候在侧,才是好事,但容不下她,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想到这些,苏信春都要独自落泪一番。虽说安常大人心思不在娶妻之事上,但也没有心系她身,并不是非她不可。苏信春可恨自己不是富贵之身。
南疆平乱,果然如元统帝所说,兵到乱即止。群臣于朝堂之上,对元统帝歌功颂德,谓战将军知人善用,谓出兵的两位将军年少而英勇。安常大人却暗讽此次出兵只是孩子家家的玩意儿,引得战将军对他口出粗话。这次,元统帝反倒为战将军说话,说定要重赏。
下朝时,战将军在宫门外拦截住安常大人,瞪着他:“你这小人,诓骗本官,能耐你不惧五马分尸凌迟万死!”
安常大人镇定自若,笑道:“将军到底是军人,讲话大声,也不避讳,这地界儿是能这样讲话的么?”
战将军斜睨他,“少和我打官场话,你狡猾奸巨,行事做派类叛奸,圣上迟早看清你的面目。”
安常大人听罢大笑,“驸马爷这是和下臣赌气呀,来来来,纡尊到寒舍,咱们把酒详谈怎样?”
战将军退后一步,“和小人同席,莫不如立死!”便拂袖而去。
对于此次周世珩等立功之事,安常大人不以为然。有人传言元统帝私底下问安常大人对这次嘉赏的意见,第二日圣旨传下,周世珩提官从二品监都尉,景珽世子得四品少尉。
一日安常大人朝去未回,慕夫人来到东庭院,时值苏信春在清洗茶具,正准备为安常大人煮茶。慕夫人说:“你只管你的活,不用顾我。”
苏信春为慕夫人泡了茶,便仍旧坐在茶炉边。慕夫人在旁观望,问:“还是吃那个茶吗?”
“是,夫人。大人仍旧饮洗血红。”
“自从你呆在他身边,我也懒怠摆弄,一切丢给你,也甚少过问大人的饮食习性,不知他平日里吃得多还是少。”
“夫人放宽心,各膳食大人都能足量用下,平常点心也是信春亲手做的,都合大人口味,所以多少也能吃些。”
慕夫人点头,“好在有春丫头你伺候着。”
“夫人,信春会尽心尽力的。”
慕夫人对苏信春温慈一笑,“好丫头。”见苏信春行举娴熟,又看她不在身边的两年里风姿变得更加庄雅迷人,十分美丽,便知道安常大人和她琴瑟相合。安常大人虽位高权重,目中无人,然而内心里未必有富贵之心。元统帝赐婚扶音郡主,他竟毫不理会,可见其并不追求姻联贵廷。在慕夫人这里,如果安常大人一心一意对待苏信春,娶之为妻,生儿育女,不见得是坏事。门庭之见自古有之,慕夫人倒可放下这一层,可是安常大人是不是只需要苏信春呢?肯定不够。
“丫头,你看这洗血红,茶色莽撞,味苦而涩,不是个好茶,却是好药。”苏信春第一次听说洗血红不是茶是药。此茶虽不受捧,也不吉利,但产自南域,价格昂贵,寻常人不见得吃得上。慕夫人亲自拣了茶叶放进罐中,说:“大人性寒,易华大夫言此茶可滋补调暖,日日饮,假以时日,效力可观,所以要吃这个。”
“原来如此。”
“大人自小命苦,能有今日成就是吃了许多苦熬过来的。你看他今日风光,可哪里安稳,外人看不见,我们自己是知道的。大人常常精神不济,这个药那个药地调理,这个年纪落魄如此恐怕也就他一人了,也不知来日数。”
慕夫人一番话让苏信春动了心思。几年来苏信春呆在安常大人身边,自然知晓慕夫人所言一丝不假。虽然安常大人时常需医药调理,可是苏信春认为那是大人为天下事谋虑以致神思劳累之故,况且易华大夫来诊,病情也只和安常大人说,她是一点也不知晓的。今日慕夫人如此说,那么安常大人的身体令人堪忧,再者,无论是安常大人,还是慕夫人,对安常府的荣耀都表现得淡淡的,从不高兴,让人费解。
午后安常大人回来,苏信春命摆膳,安常大人说已经在办事处和各位卿尚用过了。苏信春便伺候安常大人歇午觉。他抽出一封信递给苏信春。苏信春纳罕,只见信封上刚劲有力几个大字:尊姐亲启。
“是渐东的信!”苏信春又惊又喜,急急拆开,“大人,什么时候送来的?”
“刚回府,进门来,门房就递进来了。你看你高兴的,汗都下来了。”
“大人,请您读给信春听好不好?”
“拿来。”安常大人接过信笺,一目览尽,对苏信春笑道:“渐东说人已在阳京,明日来访。”便开始诵读给苏信春听。
苏信春真是高兴得昏了,忙不停开始打点,收拾出一片厢房,拟出膳食单,预备明日迎接苏渐东。
次日辰时,苏渐东骑马至,苏信春在府前东侧门迎胞弟入府,两下相见,互泣互诉。
苏渐东是来参加武试的,离试期还有一个月,苏信春让他在安常府住下。苏渐东恐打扰安常府,并且心内寻思姐姐不是府里的主人,贸然住下也不妥,故推脱说已在阳京朋友处借住。安常大人考虑到苏渐东将来会是战将军那边的学生,在自己门庭出入不方便,也没多留。所以苏渐东只是偶尔来一趟,看望苏信春,一同用膳。
一次安常大人和苏信春在歇午,两人似乎为事情闹口角,在那你一句我一句地争执,苏渐东来了。这样撞见两边没意思,尤其是苏信春,暗悔自己失了尊卑。
苏渐东见安常大人没有厉色,仍如常给他看坐看茶,问候他,才放心。
“后天就是试期了?”安常大人问。
“是,大人。”
“你且宽心应试,不会错的。”
“大人教训渐东记下了。”
“不必这么客气,渐东。”安常大人知道苏渐东是个忠厚重礼节的人,今日他格外严谨是因为方才目睹苏信春放肆的行举,便更加欣赏他。
“你是哪里学的功夫?”
“张灵山,师从泓方师父。”
“倒是位人物。”安常大人对此事向不关心,他哪里知道天下何处学武好何处学文佳,只是随口一赞罢了。苏渐东是认真的。
“大人过奖了,我想天下武学,出自司域宫。渐东苦无在那修炼。”
苏信春看安常大人脸色突变,担心起来,擅自接话道:“渐东,后天就考试,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和这边说,知道吗?”
“姐姐,你说过很多次了。”苏渐东羞涩地回答苏信春。
安常大人后来神思恍惚,根本接不上苏渐东的话,连苏渐东什么时候告辞走的也不知道。
掌灯时分,奇善从外间匆匆归来,递给安常大人一封密信。他念着信,不知不觉坐在了椅子上,奇善看出安常大人反复读信上的字,知道事情严重至极。只是安常这个样子,既像满心仇恨的杀手又像失魂落魄的乞讨者。
收信人是司域宫主人,落款人是宝嘉郡王爷景尚俞。信中依旧在找郡王府公子景瑢,说宝嘉郡王妃病重将薨,日夜思念长子,如果景瑢还在人世,希望宫主送其回来见母亲最后一面。言词间急迫,确有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