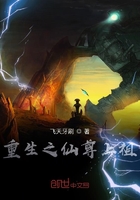“张大志,这么点事,你都能搞得这么复杂?看看你这熊样,身子板就这么点斤两,什么人不惹,偏偏招惹一些身强力壮能跟拳王泰森对垒的角色,你说你是不是犯贱?”赵玉茹近乎咆哮的怒视张大志,被训斥的人苦着张脸,为了挽回颜面,张大志将金的模样特意渲染一番,可没想到非但没能博取同情,反而招来一身晦气,张大志十分后悔先前的愚蠢。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滚回去休息。”见张大志只会干笑,也不吭声,赵玉茹愤怒指着大门,送客之意昭然若揭。
“臭婊子,迟早让你蹲我胯下唱征服。”关上门后,张大志整张脸彻底沉了下来,一路上骂骂咧咧。
“真是头脓包,当真流年不利,竟然沦落到要跟这种人合作,徐静生,这一切都怨你,若不是你,爷爷不会气得犯病,爸爸也不会整天愁眉苦脸,弟弟更不会整天闷声不吭!”赵玉茹红着眼怨恨着某个身处牢笼中的男人,但一道人影悄悄闪过,让赵玉茹略显死气的俏脸有了神采,呢喃道:“即便我清楚你是无辜之人,但若是牺牲你,换来整个赵家的欢声笑语,我会义无反顾做一次恶人。”
陈杨静静看着窗外,夕阳西下,自从踏足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就有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觉悟,但与阳延庆的会晤,让陈杨嗅到一股不太寻常的气味,似乎他的价值远远不止让徐家动心,似乎作为徐家对立面的政敌宿敌,也视他为奇货可居。
望着躺床上倒时差的金,还有在角落拆枪装枪却能一声不发的埃尔南德,原本焦躁不安的心也渐渐平复,是呀,有他们在,还会怕谁?若他们都敌不过,陈杨自问也没本事逃脱这场针对他的血光之灾。
“听说那孩子回国了?”依然是那片僻静的庭院,依然是那片遥望可‘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瀑布,杨清照沉稳的坐在岸边,手中握着一支钓竿。
“老爷,他回来了。”铁公鸡安静的立于旁侧,听杨清照问起,怕惊扰到渐行渐近的鱼群,低头小声道:“这次闹出的动静不小,应该是有备而来,传真按照老爷您的吩咐,已经发到他的办公室,而且听说前天他的办公室被人强闯,不过明显有了防备,不像上次那样颗粒无收,根据安插的眼线回报,似乎抓住了五名作案者,其中一个人您还认识。”
“哦?是谁?”杨清照不咸不淡道,似乎注意力全然集中在鱼线处的浮头上。
“高升,就是把国斌带进那所监狱的退役特种兵。”铁公鸡生硬道。
“真想不到最先按耐不住的竟然会是姓徐的。”当听到国斌两个字后,杨清照微微一怔,好半晌苦中作乐道:“三才者,天地人合。三光者,日月星辉。记得老家伙活着的时候,最喜欢跟我念叨这个词,他有一个孙子还不知足,还从我手里抱走一个,当真好不讲理。”
铁公鸡只是应着笑着,但愣是不敢发表独到的见解,在杨清照身边做事多年,最清楚这个老人的脾性,自然而然也养成谨慎小心的性子,铁公鸡沉默寡言惜字如金的习惯,很大程度上就是被杨清照耳根清净给活生生逼出来的,关于当前的主题,铁公鸡知道很多内情,也清楚记得,二十多年前,一个叫陈玄易的老人家,就在这瀑布前,用龟壳铜板卜卦后,从杨清照手里带走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当时还不到五岁,是杨清照的直系血亲,亲孙子,而那一年,也是铁公鸡正式在杨清照身边做事的一年。
孩子的名字,叫杨国斌。
“陆言,你说说,国斌像谁?”杨清照突然望向铁公鸡。
“像老爷。”铁公鸡貌似诚实道,但这话却引来杨清照一阵苦笑,之后归于平静,仿佛一切都未谈起忆起。
“爷爷,该吃饭了。”一位玲珑剔透的少女,轻盈的迈着小碎片来到杨清照身边,手里端着一个竹篓,里面有着一碗饭、一盘菜,还有一壶温酒。
“树静,还记得国斌吗?就是小时候经常带你抓蝴蝶的哥哥。”杨清照端着温酒,先是喝了一小口,这才笑道。
“记得,但爷爷似乎说过,国斌哥去了很远的地方,他,还在吗?”赫连树静有过那么一瞬间的迟滞,但终究还是开了口,自从那个印象中渐渐模糊的大哥哥突然失踪后,国斌两个字,就彻底成了杨家的禁词。
“在,要不了两年,他就会回来了。”杨清照笑眯眯夹了口菜送进嘴,话中有着发自内心的笑意:“始终是远离故土的远方游儿,总会有着落叶归根的时候,当年老家伙说过,十六年岁月蹉跎,换来六十年福泽安康,老杨家不求门第显赫,只求缘聚缘散生死相依,或许老家伙口中的十六年岁月蹉跎不起波澜,但与他孙子的命格比,老杨家知足了!”
“爷爷,饭菜快凉了。”老人仍在闭着眼感慨,但赫连树静却在铁公鸡的眼色示意下,催促杨清照动筷,铁公鸡的想法很简单,该知道的,不怕知道,但只要与老爷有关的私事,尤其是杨家的秘辛,铁公鸡根本没胆量探知,甚至入耳:“爷爷,您快看,鱼上钩了。”
杨清照豁然睁眼,手臂本能朝上抬,一条鲜活大鱼便被溜进了渔网,这条鱼被放进网中后,杨清照突然平静道:“一条鱼只要够聪明,就懂得撑开口子跳出渔网,可惜,每条鱼似乎都只会偏执的在网中乱窜。”
“爷爷,您有心事,是不是外面有什么事,让爷爷不开心了?”赫连树静疑惑道。
铁公鸡想要吱声,却被杨清照不动声色给制止了,笑眯眯道:“树静,红尘三千世界,任何大是大非,都要以局外人的心态看待。或许,这样的生活会枯燥乏味,但若有朝一日,爷爷死了,你若敢轻易踏足红尘俗世,在地底下,爷爷也会死不瞑目。”
“爷爷,您不会死,树静不会离开这里。”赫连树静红着眼道。
“孩子,别怪爷爷狠心。”杨清照拍着赫连树静的肩旁,落寞道。
“爷爷,树静从没怪过任何人。”赫连树静身体有着颤抖,此刻,玉人早已成了泪人。
望着这个自始自终都被压制着无法入世的女孩,杨清照一瞬间有着不可抑制的负罪感,及笄之年的女孩子,芳华正茂,却要死死困守在这片社会的缩影角落,肉眼常年不变的,无疑是这处意兴阑珊的一草一木,一叶一枝,一山一水,一天一地。
这是一只被困在井底的鱼蛙,看不透天地的辽阔,却大智若愚般固守着旁人垦勤的土地。这是一个被命运抛弃的女子,无法拥有常人的酸甜苦辣,却苦中作乐带给旁人会心的微笑。这是一个本该沦为浮漂的女人,宿叶无根,依山伴水,没有大树依靠遮风避雨,却总能朝气勃勃顽强独立。
但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却在襁褓之年流落他乡,这是一个本该遗世独处的方外之人,这是一个本该被是非善恶羁绊的菩萨,这是一个本该长满业障的编年人!
编年人,本不该拥有感情,但一个叫陈易玄的老人却坦言,编年人本就该尝尽世间冷暖,但这一点,杨清照不愿苟同,他始终认为,不让这个女孩入世,是对这个女孩的残忍,但他只是扼杀了一个人历程的凶手。但若让女孩入世,却会引领整个世界走向黑暗,到时候,他会欠下整个世界,成为彻头彻尾的刽子手。
“什么?怎么连你也这样?”房间内,赵玉茹对着电话筒,近乎咆哮道。
“赵小姐,不是我不愿意帮这个忙,而是圈子内不少人都听到风声,说他跟阳少喝过茶。”电话那头的人有些焦急,语气更是压得低低的。
“喝过茶又怎么样?喝过茶能代表什么?难道阳延庆已经公开说要保这小子?”赵玉茹不可理喻道。
“这倒没有,不过听不少人说,甄洋现在替他办事,这家伙你知道的,算得上阳少的心腹,阳少舍得让他的心腹替一个外人做事,而这个人恰恰跟阳少喝过茶,赵小姐,这忙,确实不敢帮。”这人似乎语气有所松懈,显然也听出赵玉茹开始临阵退缩,趁热打铁道:“知道阳少邀请这个人去哪喝茶吗?”
“哪?”赵玉茹下意识道。
“长城,夜晚的长城,那座烽烟台。”这人的话,仿佛一记闷雷重重轰在赵玉茹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我知道了,先这样吧。”赵玉茹说完便挂掉电话,眼中有着颓废,因为那座烽烟台,是阳延庆父亲的葬身之所,具体死因至今不明,但能当着阳延庆踏足这座烽烟台的,尤其还在夜晚时分,至今不过寥寥数人尔。
坐在沙发上的赵玉茹数次想重拾电话,但现实的残酷让她不得不终止这类无济于事的执拗行为,喃喃自语道:“不会的,一定能想出办法,一定能!”
作为被谈论的焦点,陈杨倒是没有太大的烦恼,伴随着手底下能用的资源越积越多,陈杨有信心打赢明天北京的首场胜利,这其中就包括黛安娜这位娇滴滴的床上美人的到来,陈杨很意外卡琳娜会这么大方,但换个角度,又有些苦笑,恐怕卡琳娜也担心陈杨耐不住寂寞,在中国胡乱采摘,不过,陈杨对此,倒是不太在意。
望着渐渐暗下来的天色,陈杨暗想,在这座梦里花飞香四溢的北京城中,会不会再度锦上添花,绽放更美丽的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