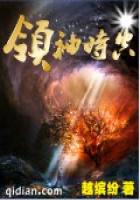星空清晨跑完步回来,趴在爸爸星野的床边,看着他的脸,那是一张曾经英俊而坚毅的脸,十五年前这张脸就等于荣誉、成功和霸气,而如今这些早已不在,上面憔悴的纹理变得如此清晰而深沉,油红的底色上是无尽的疲惫、无奈、苍凉和绝望。
星野从梦中醒来,睁开双眼,“小空,怎么了?”
然后他发现眼前的星空一脸迷惘,像极了七岁时期的那个孩童,看不出的伤心,无助的目光,还有眼底隐隐的仇恨,那时刚刚没了妈妈。
“没有,爸。”星空立起来,坐在床边。
星野坐起来,“是不是和信心闹矛盾了?”
星空动动嘴唇,不知道该怎么说。
“吵架没什么,男孩子多让着点。”星野说道。
“爸爸,你先喝了这杯茶,我给你热早饭。”
“不知怎么地,这两天老是梦到她。”吃早饭时,星野讲到。
“不要多想了,回来陪你看比赛。”
星空没有去学校,而是到了星城网吧,他自己的网吧。他在主机上随便浏览了一下管理员页面后转到网吧中的一块草坪上,这里阳光充沛,他栽了数根翠竹,几颗紫薇,翠绿和粉红错落有致,在草坪一角他修建了一个小亭,亭中安放了石桌和石凳。而他在草坪中间的露天石桌旁的漆了和石桌一样颜色的木制靠椅上坐下来,合上一夜未闭的双眼,阳光抚着他的温和的脸庞和整齐的长睫毛。网管小李端来一杯咖啡,轻放到石桌上。星空睁开眼睛,嘱咐这个十七岁早当家的孩子:“把旁门锁起来。”旁门是到这里的唯一通道。
三年前,一个炎夏的午后,炽阳异常火辣,信心要拉着冷秋去学校的无名湖游泳,然而在冷秋耳边的飙声犹如宇宙中遥远的星系的一次爆炸——冷秋听不见。最终她一个人去了。太阳烧烤的无名湖蓄势待发,以几何倍数递增的能量一旦积聚充足,它可能马上会以巨大的以至于超出人类听力范围的声响“刷”的冲向云霄。她信心满满,这样的大热天“不会活见鬼的。”
她躲进树丛,换一身泳衣裤,阳光下修长的双腿如牛奶般白皙。若不是担心紫外线揪出一大批黑色素来,她一定会持续自我陶醉下去。突然一声冷不丁的蝉鸣传来,她受到了惊吓,来不及准备就一头了扎进湖里。她扑腾了两下,伸出鼻孔,调整一下气息,恋恋不舍地跟修长的双腿暂别。湖水通过劲道的波动向肌肤传递着贼爽的凉意,她闭着眼睛回味着久违的的享受,忍不住格格笑出声来了。然后感觉水波有些异样,不情愿的将双眼扯出两道缝来,“啊”震地三尺,轰轰烈烈。一个带泳镜泳帽的露着半张脸的男生在不远处的水中气定神闲的望着自己。她憋一口气沉入水中,想原来热的不仅自己。
当呼气肌扩张到极限,她无法再在水中待下去时,探出脸,抹一把水,视线刚好落到星空仅一条底裤的身体上,她深吸一口气。就在那一刻她深陷于结实的躯体肌不能自拔,并且事后对冷秋发誓也要长出那么一身帅气的肌肉。她肆无忌惮的盯着毫无瑕疵的躯体直到它被衣衫遮住。接着星空才摘下泳镜,甩掉发梢的水珠。而在那一刻那张宁静的面容尽现眼底,很熟悉,那张面容向给她一个嘴角上扬的微笑,拎起背囊,悠悠离去,发稍垂下遮盖了眉眼。
星空回忆着他们的初见,信心真是傻得可爱。
信心不知道的是他当时的心情,怎么会忘记?朝思暮想的人儿终于以这种别开生面的方式正式出现在自己的生命里。
“我好想你,你的笑声。”
电话响起时,他正在温暖的阳光下微笑,嘴角上扬,像弯月。
他不情愿地接起电话,是齐子打来的,“星空哥,你没来上课吗?我在511了。”
“哦,…大一有王教授的课吗?”
“今天我们刚好没课,我想和你在一起…我等你好吗?”
王教授的课总是人满为患,他讲授神经科学,而用心理学来穿针引线,他喜欢以这样的角度剖析人的思想和行为,包括正常的和奇怪的。听过他课的同学都会有一个基本思想:世间万物没有对错之分,有的只是不同内外环境下的不同状态。所以他们对未来社会人人关系的一个猜想是:和谐将是一种自然状态,因为个人的思想将受到公平对待,因为主观本来就来自于客观。
大家喜欢上他课的还有另一个理由,风趣的谈吐以及幽默的打扮,没人知道他的颇有复古和欧范的艺术造型灵感来自于何方。他捋着两簇浓密的上翘的小胡须走进来时,大家就报以了嘿嘿、哈哈、格格的笑声,然后这些笑声将持续两节课的时间。当然除了怀里揣着心思的同学,今天其中一位是冷秋,她从各个角度使劲探出头去,寻找那个也许会以同样努力的姿势探寻她的信心。她跟左边的上官飞交流“我跟你说,我不怀疑我哥抽烟的事实,男生抽烟很平常,并且才体现男人味儿,你说呢?”上官飞回答是的。“可是我从没见过他抽,真的,他真抽吗?”上官飞回答是的。“我跟你说,这回绝对有问题,你说呢?”上官飞还是回答是的。“你改名了,什么时候改成上官是的了?”冷秋双眼瞪着她。上官飞听到火药上膛的声音,点点头又摇摇头,然后赶紧转移话题,用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来淡化局势,问她找见信心了没。她一紧眉头,问上官飞旁边的兄弟,那兄弟回答没见,然后建议她问问她旁边的同学。她试着将希望寄托到了右边那位同学上,然后她瞬间无语了。
那位同学扭过头来,一脸坏笑。
“哎呀,额的神那!怎么改头换面了?”冷秋向后一个趔趄,坚硬的头盖骨撞上上官飞的鼻梁。
“上官飞,今年是大四吧?”
上官飞揉着鼻子回答是的,这反应有点过激了吧。
“我没有时光倒错吧?”
上官飞回答没有,你比大一更加出人意料。
眼前的信心没了柔顺的长发,取而代之的刚上大学时的那一头清爽的短发,只是加入了发梢微卷、额发碎而不乱的时尚元素,显得很干练。
“都来了啊?”王教授那一头卷发与小翘须朝相辉映,很多人怀疑他应该是英韩混血,比较不帅的那种。
“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的课程,我很开心。信心”王教授低下头在多媒体上按下几个按钮,投影上页面置换着。
“这是奖赏中枢的功劳。”
王教授听到回答抬起头来,“恩,这个问题先搁下,怎么剪头发了?”
“这要归于理发师的功劳,我对他说的是请帮我剪个卷发,然后我睡着了,他成功的为我剪了个短发。这其中错误大致出于三个层面:其一是声音的传播途中,外界杂音扰乱了‘卷’的波形;其二是耳膜到内侧膝状体,原因同上;其三就是皮层,接收信号的复杂通路存在成千上万的会聚与发散。因此,‘卷’便于短混淆了。当然不排除那位帅哥的恶作剧。”
“也不排除你说的其实就是短发。”冷秋小声嘀咕。
“额,美丽的错误。咳咳,恩,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围绕‘被爱时感到开心展开’。”
信心的回答使得后排的齐子和几个低年级的同学目瞪口呆,“她准备好了的吗?”有同学问,“她不用准备”旁边的忻州和低声回答,但他悄悄皱起了眉头,是突然决定剪得吗?
下半节课星空从后门闪进来。星城是一座神经科学之城,人们热爱神经科学,将它应用到了生活中,比如人们都知道睡眠是一种主动过程,他们知道将一个细微的技术性动作反复练习使之成为本能;当然也有许多人远离这门复杂之至的科学,星空就是其一,他的人生准则很简单,仅是:爱和责任。比如对于家人那是‘爱’,而对于现在的齐子那是‘责任’。而这两个词深层次的涵义就不必多讲了。
两节的公共课很快结束,王教授被围堵在讲台上。
冷秋,上官飞,信心各怀心思前后从白炽灯的光亮中走进逐渐褪尽温度的阳光里,冷秋打声招呼奔向女厕。
“说吧,什么事?”信心说。
“你先说说你头发怎么回事。”上官飞回道。
“这不关你事。”
“咱俩交换”
信心瞪向上官飞,她的目光中有某种不妙的暗示,已然面露凶相。
有人及时制止了暴力的发生,星空和齐子牵手的画面越过信心的肩头进入上官飞的视野,一瞬间情况明了了。与此同时,对面的两人也就看到了他们。
齐子拉着星空走过来,要星空介绍她和信心认识,她说信心是她的偶像。信心回头,那张面无表情的脸,那深邃的如星空的眼眸,缺少了嘴角上扬的微笑,他那双充满了力量的大手此刻握着的不是自己。他的心是否落寞,有再伤感吗?
信心又成了大一时无名湖边的那个短发假小子,不羁的眼神、狂妄的表情,脸蛋不算漂亮,去总是很迷人,可是代替往日在阳光中张开双臂笑着投向自己怀中的是转瞬间的漠然,她的眼眸中有泪光在闪动,难道是自己在心流泪吗?
为这个场景增添了一笔的是冷秋,这个丫头跑过来看见星空,然后非常大方的送上一句:“哥,你的手拉错人了。”上官飞差点昏死过去。
化解尴尬的人即时出现,看见他们的忻州和跟过来,先是看了一眼信心,又瞥见了星空和齐子,齐子紧握着星空那双大手。忻州和的大脑皮层自主地迅速做出判断,又建立了新的关联,转向齐子:“今晚把星空借我用一下。”
齐子害羞的的抿了抿嘴,将如孩童般纯真的目光投向星空。
星空没有说话,只是用眼睛询问忻州和什么事。
“星叔最近不是设计了一个新游戏吗?”
“改天吧,我专门找时间。”
“也行”他又看向信心“你来一下,王教授找你。”
信心径直走向教室,去找王教授,被忻州和从背后拽住了了手臂,信心回头。
“王教授没找你”忻州和看一眼远处的四人,星空正把目光投过来,“是我找你,有问题要问你?”
“什么?”
“现在还不知道,等我想起来吧。”
“神经病。”信心在心里暗骂。
忻州和看向远处的四人,他们已分开,上官飞和冷秋站在原地,显然是等信心。
“去吧”他松开信心的手臂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