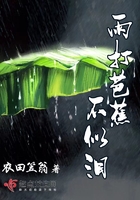想念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就像是身体里循环流动着的血液,反反复复地萦绕在心间;失去一个人又是什么感觉?仿佛是从身体里抽出了肋骨,有切肤之痛,同时又空乏其身。刚刚还好好的,放个鞭炮回来,发现就独剩自己一个人了,说不见就不见的离别最揪心,郑茹的不再联系,让袁莱的心时时刻刻悬在着半空中,浮躁、急切、痛惜,心神不宁。生活处处,措手不及,不辞而别,又无缘无故,再加上哪怕是一星半点有关郑茹的消息都没有,所以袁莱像一个精神白痴,也像一个行动侏儒,束手无策,诚惶诚恐,只能陷入幻想。此时此刻的幻想犹如一个难忘的,天长地久的情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袁莱想郑茹想得活眼见,可这一切都被袁莱压在心底,生活还是生活,工作还是工作。日子就像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地机器,一天一天的重复,偶尔报警亮亮红灯,等待人的处理。没有人会同情机器的命运,也没有人会关注机器的感受,人人都认为机器就应该要工作,这也成为现代常识,甚至历史上不还曾经有人抗议劳工待遇去捣毁机器,埋怨是它让自己跟着受牵连受疲困的吗?袁莱不讨厌机器,相反他还较喜欢机器的嗡鸣声,因为外界的干扰能暂缓思想的争鸣,他得以有时间休息与清静,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想看到郑茹无影无声,机器心跳骤停的报警红灯。这个报警一声惊醒了梦中人,吓得袁莱屁股尿流、失了魂,这个红灯闪烁着当咛当叮呀咛当叮铃铃贴铃贴铃贴的落魄一幕。
朱自清曾说过:“我是个懒人,平心而论,又不曾遭过怎样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力索,又未亲自体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处也只是廉价的,新瓶里装旧酒的感伤。”袁莱喝下得不是感伤的烧酒,而是难以自拔的疼痛,痛定思痛,仍是无法入睡,他倚躺在床上,拿过记事本写道:“
《迷路》
习惯了走羊肠小道
就会有可能混淆曲直
就会有可能淡忘捷径
所以说习惯有时是可怕的
习惯有的时候也是悲哀的
突然有那么一天
眼前出现两点一线
这是最短的路程呀
这是最直的直线啊
这是几何书中所手绘过的定理
沿着这条人人渴望的云中路
省时省力省心
省去了无尽的等待
省去了婉转的距离
省去了平庸的想象
省去了等等等等...
但再也感受不到新鲜的味道
已再也寻觅不到熟悉的角落
及再也触摸不到葱翠的草木
在回家的方向上
风呼呼地迷路了
风呵,你可真是自由飘荡的情种
你带着蒲公英飞
你携着萤火虫游
你伴着启明星唱
你跟着先驱者走
风呵,你可真是虚怀若谷的君子
你推举波澜为大海助兴
你煽动水雾为高山增气
你鼓噪圆月为夜色添彩
你教唆沙丘为荒漠翩舞
你现在老眼昏花
看不到归去来兮
终还是会迷路吧
。”袁莱羡慕风的轻畅与拂动,也尊重它的狂吼与脾气,袁莱曾一度追随过风的洒脱与飘逸。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历史风云中灭六国统一华夏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何其壮哉,他想留千秋帝业,结果是秦二世就亡国改朝,什么是他的?焚书坑儒的罪名吗?相比较来看,还是司马迁的《史记》更长远更实在更有价值,因为《史记》是完完全全属于司马迁个人的,史家之绝唱啊,是司马迁留给后人的礼物,也是司马迁本人对历史的贡献。所以,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个人相对国家是渺小的,国家相对历史也是渺小的,历史相对永恒更是渺小的。袁莱对思想家老子提出万变不离其宗的“道”佩服不已,这也许就是袁莱心中苦苦期盼的“不变”吧。大人物、大追求、大道理,袁莱也略知一二,但心痛还是焦灼的疼,他整个脑海里全部都是郑茹过去的一颦一笑和点点滴滴回忆。郑茹,你知道袁莱在想你吗?你知道他有多想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