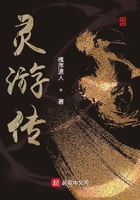此刻秀女们正列站在太极殿外宽阔的广场上,西斜的夕阳已无法驱走些许初冬的寒意,只在殿顶明黄色的琉璃瓦上洒满殷红似血的光泽。
我似听非听着钟粹宫总管太监张德叙述的宫中礼仪,感觉与中学每周一的升旗仪式大同小异,校长在讲话,底下的人都在发呆……
两个月前,我在神武门领了名牌,接着便是正黄旗和我所属的镶黄旗初选。
秀女们按照宫中后妃的亲戚、满族、蒙古、汉族的顺序依次进入顺贞门至御花园钦安殿候选。康熙去了南巡,主选的是皇太后,我们排在最初的她看都没看一眼,就说了句“留”。
不管是留了牌子还是撂了牌子的参选秀女都是立刻归家的,我回到马车边,见有个太监正等着我,说贵妃吩咐复选之前都让我留于宫中。
我才知马车上的包裹意义为何,临别时香慧又为何哭得肝肠寸断,大抵是隆科多出于保护我的目的,虽说我怎么想也不觉得宫中会比他都统府舒心,但性命无忧倒是真的……
之后以贵妃为首的一众妃嫔进行了两轮复选,如今只剩下六十余人,一同住在钟粹宫中,每日由太监嬷嬷授以规矩礼仪,我也由承乾宫搬了过去。
我开始遗憾自己读史书的时候太过专注政治,若能背下各皇子宗室王公有哪些福晋,完全可以挂上招牌专司为秀女算命,铁口直断,赚他个盆满钵满!
胡思乱想中,张德终于结束了今日的长篇大论,我又需要横穿紫禁城回东六宫,一路埋怨为什么非要挑这么远的地点培训,还不提供交通工具!
————————————————————
太极殿的东门连着西六宫的甬道,偶尔会遇见一些无聊的宫中妃嫔,我嫌那些无意义的行礼问答麻烦,便总是从南门出,由外围走。
尚未出门,就瞥见东南角的铜缸边站着一个身量不足丈的小鬼,我叹了一声,又来了!
我径直走过去,问:“今日师傅出了什么难题?”他嘻嘻一笑,摇头道:“没有,皇阿玛刚来查问我们功课,师傅拿出我上次作的咏菊诗,皇阿玛称赞了我呢!”我暗道作弊得来的有什么好高兴的!
十五阿哥胤禑今年九岁,额娘是康熙二十八年南巡时带回来的女子王氏,是康熙晚年最宠爱的庶妃,由于出身不高,只封作密贵人,十五自小是交由德妃、即雍正和十四阿哥的额娘抚养的。
清朝皇子六岁起读书,他天资不高,四书五经尚未通晓,师傅便开始教授他诗词歌赋。一个月前我初次见他时,他就是沮丧不已地站在这里苦思着咏菊诗。
我心忖着咏菊也得对着菊花想啊,对着铜缸想有什么前途!可怜他愁得眉毛都打结了,便抄袭《红楼梦》里的一篇教了给他,他竟食髓知味,遇到功课上的难题就躲在此处等我。
我曾想措辞劝他不应该凡事都仰赖旁人,但我不是为人师表的好材料,完全不觉得我有教育他成才的义务和本事,便由着他了。
我想了想,问:“皇上这么快就回宫了?”他点点头,说:“嗯,太子中途病了,皇阿玛中断了南巡。”我“嗯”了声,与他随意闲谈了两句,便折身回去。
康熙回来了,那么大选之期也不会远了……
这些日子以来,与其说是从早到晚学习繁琐的宫中规矩累,更是思虑太重,我自负聪明绝顶,在此却满是力不从心的感觉!
有对比才有发现,不经此一役,我还没意识到现代社会是多么的自由民主!
————————————————————
明日又将有一轮复选,一众秀女不停悄声议论着不知会不会见到康熙,康熙是怎样的龙貌、龙气,要不是我心情奇差,实在是想放声大笑!
回程途经御花园,我懒散地踱了进去,此时虽值冬季,园内却于山石间布满松、柏、竹等长青植物,绿意盎然。
我走进浮碧亭,站在深红色的方柱前,暗想要不要刻下“安新惠到此一游,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初七。”若百年后得以留存,或许就是我开创了景点涂鸦的先例也未定……
以往在亭下池中畅泳的游鱼,冬季已不再浮上水面,若我是变成一条鱼,此时就能一路游到护城河,逃出生天了,不过鱼也有难念的经,比如干旱,或被更大的鱼吃掉……
我苦笑一声,转开了目光,亭外一棵不知名的古树盘虬卧龙,叶已凋零,正伸着光秃秃的枝桠,张牙舞爪地妄图染指天空。义无反顾,却萧索之味弥漫。它也如我一般,在追求些不切实际的梦想么?可讽刺的是,我如今连什么是切实际的梦想都不知道!
时常一觉醒来,意识朦胧地看着周遭华美的床幔,仍会觉得荒唐透顶!自己早过了小女生做梦的年纪,真有这种穿越的机会是不是该让给别人?或许就会懂得享受,而非这般无助……
人生始终并非戏剧,我当年拍的电影轻松有趣,只为取悦观众,可如今身在其中,方知这根本不是凭想象所能体会到的茫然与绝望……
自怜自艾了片刻,起身前行了一段,瞥见丈外的假山罅隙里露出一截粉红色的衣角,便于路经时转眼瞟了一下,见一个小小的身影正埋头蹲在石缝间低声啜泣,肩膀不时微微抽动,从衣着看来同是秀女。
我停下步子,站到她跟前,淡声问:“怎么了?”一张梨花带雨的小脸闻声抬起,两弯娥眉深蹙,小巧的鼻尖微红,唇不点而朱,水汪汪的美目眨巴眨巴地望着我。
我纵是铁石心肠也软了三分,抽出手帕递给她,说:“擦擦,别哭了。”她迟疑着接过,却只是攥在手里揉捏,复又埋头抽噎起来。
我等了一会,见她没有开口的意思,便转眼四下打量,天色已开始昏暗,四下的太监宫女正忙着掌灯。听见她哽咽着问:“姐姐,你想被皇上选上么?”我眯了眯眼,没有答话。
她慢慢停止了哭泣,吸了吸鼻子,低声说:“她们说,你一定会被皇上选中,可是我……”我侧回头盯了她一会,平声道:“你容貌姣好,要被皇上选中也并非难事。”
她连连摇头,嗫嚅道:“我就是因为不想……”我挑了挑眉,问:“为什么?”她脸色一红,垂下了眼睑,沾着泪珠的长睫微微颤动。
我顿时了然,到此时、此地还挂念着心上人,看来也是个追求不切实际梦想的孩子……想了想,压低声音道:“若你还指望着见到他,以后‘不想被皇上选中’这种话,绝对不能宣诸于口!”
自打搬进钟粹宫,看在眼里、听在耳里的不少。这些秀女虽不乏有个别聪明的,但绝大多数才十四五岁,懵懵懂懂的年纪,又谈不上历练,连最基本的祸从口出都不明白,一丁点心思就嚷嚷得人尽皆知,若我是她们,比起什么荣华富贵,先担心自己的小命要紧……
话说起来,这年代真是鼓励近亲结婚,这些秀女背起族谱来,恨不得随便找两个出来三代内都能沾亲带故……
————————————————————
张德正在钟粹宫东厢巡视,见到我,满脸堆笑地嘱咐:“翎兮小主好生休息,您身子矜贵,有事尽管吩咐奴才们!”我淡淡一笑,颔首进房,心下暗忖,难怪自古以来人们对的权力的追求如此孜孜不倦。若非我的命运实在堪忧,宫里人全力的逢迎差点令我这个现代人都飘飘然起来……
康熙的生母是我爷爷佟国维的胞姐,而我父亲隆科多的一个姐姐是已过世的孝懿皇后,一个妹妹是当今佟佳贵妃,我二哥舜安颜是康熙朝唯一的一位满洲和硕额驸,两年前娶了康熙的五公主温宪公主。
佟国维既是康德的舅舅亦是岳父,隆科多既是康熙的内弟、大舅又是亲家翁,单此一支,便可见佟佳氏的地位如何尊崇。
此时是佟佳氏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我可谓躬逢盛世,这年代讲究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女以父贵、父以女贵,人人知我是隆科多的掌上明珠,庶出与否根本就不再重要,依然是身世显赫。
而相对的,佟佳氏必定在想着,应该如何利用我,令原本的荣耀再攀上新高度。我的婚姻含着许多政治考虑,康熙绝不会独断,而会结合家族的意愿,我却根本不知佟佳氏作何打算。
但孝懿皇后和贵妃都未有所出,较大的可能是要我为佟佳氏留下皇嗣,隆科多才会担心佟佳.翎兮的性子无法适应勾心斗角的宫廷……
————————————————————
用过晚膳,我的手指习惯性地在桌面上轮番轻点。复选之期早就定下了,但如今应该只会走个形式,毕竟康熙提前回京,不如直接等他亲自大选。
外间偶尔传来那些天真女孩的谈笑声,她们还不知这宫廷的可怕,今日的荣华富贵,便是明日的万丈深渊!
我已无心力同情怜悯她们,难道我真的要嫁给比现在这副身子老上三倍有余的康熙,二十年后去慈宁宫烧香等死,将一辈子埋在这里么?
夜间辗转反侧不能成眠,迷迷糊糊睡去,未觉片刻便有丫鬟过来喊着起身梳洗。我昏昏沉沉地任由她摆弄,对自己的以后连想亦不敢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