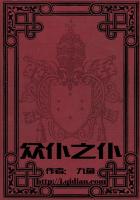第二日天明,刘三便来向戚寿国和郑森辞行。紫儿嘴唇撅起老高,眼眶中红红的,拉着戚盈盈的手不肯放开,戚盈盈也心中不忍,只好勉强安慰。盖问天却乐呵呵的,和周围群雄纷纷抱拳拜别。郑森也是舍不得众人,见刘三征袍破旧,便将自己身上的披风批在刘三身上,送去数里,众人依依惜别。
从江阴经长泾,走无锡,只见沿途人烟稀少,虽不是哀鸿遍野,但也是满目沧夷。刘三叹道:“人言道江浙富庶,却不料如今也是如此风景。”
紫儿道:“这些年天下灾害频发,大旱之后便是蝗灾,饿殍遍野,疾疫横行,流民四起。家父虽联络江浙富商开仓济民,但也是杯水车薪。”
刘三道:“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但放眼天下,哪有一寸乐土能安身立命?也难怪四处流民揭竿而起,只是为了活命。这满清鞑子也实在是可恨,趁天灾人祸之际侵我中原,无异于趁火打劫,更陷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三人正叹息间,几匹快马从身畔疾驰而过,扬起一片尘埃,众人皆以袖掩住口鼻。
盖问天待尘埃散去,连连呸了几口唾沫,怒骂道:“呔!哪里来的混账儿子王八蛋,会不会走路?!当这官道是你自家院子么?”越骂越火气越大,策马便追了上去。
刘三道:“盖大哥,不必追,你我赶路要紧!”
这盖问天正怒火中烧,哪管得了这么多,头也不回,叫道:“待我把这几个混小子揪下马来,跌他个七荤八素再说!”
刘三无奈,只得和紫儿策马追了上去。
三人辞行之时,郑森见盖问天身材高大,只恐平常马匹驮不动盖问天,便将自己胯下的那匹彪壮的千里马送与了盖问天,刘三和紫儿的坐骑不过普普通通,如何追得上?追了三、四里地,前面便是一条三岔路口,盖问天已是人影全无。
刘三摇头道:“唉,我这个大哥,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紫儿抿嘴而笑。刘三望着紫儿道:“任性难缠,与你无异。”紫儿笑道:“我倒觉得姑父很可爱,天真烂漫,率性而为,何等无拘无束,逍遥自在?”
两人下了马,查看路上的马蹄痕迹,只是两条路都有马蹄的踏痕。刘三问道:“这条三岔路口,如今该走哪一条?”
紫儿道:“右边这一条吗,走上四、五十里,便可到我家,左边这条吗,那是可以到姑父家去的,大概也是四、五十里的路程。要不,我自己送自己回去,刘师傅便去姑父家,探听情况,如何?”
刘三摇头道:“你这丫头古怪精灵,别又想什么歪主意到处乱跑,免得跑丢了让我担心,还是一起去吧。”
紫儿一双美目脉脉地望着刘三,道:“师傅,你是在担心我吗?”
刘三脸一红,道:“唉,这个……你若跑丢了,我如何向苏大侠交差?”
紫儿眼睛一转,道:“刘师傅,你送我回家,交了父亲的差,然后我再和你跑出来,如何?”
刘三大吃一惊,道:“这个,这个恐怕有点不妥。”
紫儿噘着嘴,眼圈一红,道:“我回家后,无聊得很,肯定会跑出来的,你就不怕我一个人偷偷跑出来,无依无靠的,被人欺负吗?”说罢背过身去,肩头微微颤动。
刘三心一软,道:“紫儿,我不会让你受欺负的。不过,你若想出来玩,还是得禀报令尊令堂大人,免得他们担心,如何?”
紫儿回过头来,破涕为笑,道:“师傅,这么说,你可是答应了!”
刘三苦笑,不知该点头,还是摇头。
路边有一个供行人歇脚的亭子,刘三道:“紫儿,我们先到那亭子歇歇脚,兴许盖大哥教训了那几个行路人,便赶了回来。”
紫儿笑道:“恩,不错,姑父把那几个人扔得七荤八素,就会回来的!”蹦蹦跳跳的,自个便去田野间四处盛开的梅花。刘三坐在亭中,望着田野间奔跑的紫儿,心中不禁很是羡慕,唉,这丫头,真是不识愁滋味。
来路上又奔来几匹快马,乘客和先前那些人是同一般装束。奔到亭前,马上乘客喝问道:“呔!那位客官,苏家庄该如何走?”却不是本地口音。
刘三见那人甚是无礼,不去搭理他。紫儿听得有人问苏家庄,心中一怔,见这几人身着劲装,甚是彪悍,便指着左边那条,却是去盖家庄的道路,答道:“走这边,约莫六、七十里就到啦。”
眼见那几匹快马朝左侧道路奔去,紫儿赶紧回到亭中。刘三似笑非笑地望着紫儿,道:“你这丫头,说谎话不用打草稿。”
紫儿道:“师傅,这几个人凶巴巴的,要问去我苏家庄的路,只怕是有些不妙。我们这就先回家看看吧!”
二人走出亭子,正待上马,只听左侧那条道路马蹄声阵阵,一位骑高大黑马的蒙面汉子返了回来。紫儿说了谎,心中紧张,将身子躲在刘三背后。那蒙面汉子骑着马绕着两人转了一圈,冷笑道:“好个刁钻古怪的丫头,凭你这番谎话,便要骗我手下白跑几十里路程!”
刘三不知该如何应答,胯下那匹劣马在黑马的逼迫之下不禁后退几步,黑马却嗅了嗅刘三,喷了几个响鼻,摇晃着尾巴,踏着碎步,似乎很是兴奋。那蒙面人缓缓解下蒙面,刘三一见,惊喜地叫出声来,道:“啊,没想到是你,你是谷寒!”
的确,那人正是谷寒,那黑马也正是草原上难得一见的汗血马!只是人世沧桑,那匹马身上也刻下无数痕迹,却显得更为彪悍成熟。
谷寒依旧是那幅冷冰冰的模样,只是嘴角微微泛起一丝笑意。只见他从身畔解下一个皮囊,扔给了刘三。刘三接过,拔出塞子喝上一口,辛辣如刀,随即全身暖洋洋地,说不出的惬意,不禁又惊又喜地道:“这不是顿珠大哥的青稞酒吗?谷大哥,顿珠他们如今也在江南?”
谷寒下了马,走入了亭中,坐下道:“顿珠他们如今在北京公干,这壶酒便是他们送的。”
刘三和紫儿也走入亭中坐下,紫儿见刘三和谷寒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便也不再畏惧,扭捏道:“谷大哥,真是抱歉,我不知道你和师傅是好朋友,给你们指错了路,请你不要计较。”
谷寒望着紫儿,又望望刘三,道:“怎么,刘兄开山立派,收徒儿了?”
刘三脸一红,道:“谷大哥休得取笑!小弟这点本领,谷兄岂有不知?实不相瞒,这位姑娘便是苏家庄苏大侠的千金,也是在下的好朋友,见谷兄的朋友问去苏家庄的路,只恐有所不利,便另指了一条道。”
谷寒道:“其实刚才我就认出了兄弟,只是人多,不便和你相认罢了,暂且让他们白跑几十里地,好让我们兄弟有时间叙叙旧!”说罢莞尔一笑。
刘三道:“不知谷兄如何碰到了顿珠他们,顿珠他们在京城有何公干?”
谷寒正色道:“刘兄,你我相识之时,我尚未探查清楚自己的身世,这凌峰虽然可恶,拆散了与我相依为命的兄弟,但毕竟于我有二十年的养育之恩,因此曾以先师所起之名凌孤寒示人,与刘兄相交于西域时,在下正值彷徨之际,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只说自己叫做谷寒。如今在下身世已然明了,当正名耳!”
紫儿大惊,这凌孤寒据说最喜欢撕烂别人的裤子看屁股的!便躲到刘三身后,颤声道:“你,你便是那西域凌峰的传人凌孤寒?!”
刘三也点了点头,道:“月前我曾与老刀客去青石铺,有幸拜会了智正长老和清虚道长,他们业已知道谷兄就是凌孤寒。二人也是为调查谷兄身世而来。”
谷寒冷笑道:“这两个老家伙,二十年前衡山绝顶两人联手斗西域凌峰,胜得不明不白,如今行将入木,尚有闲暇管在下的身世!”
刘三摇头道:“二十年前,长老与道长皆年近六旬,俗话说,拳怕少壮,若论单打独斗,如何赢得了正值壮年巅峰的西域凌峰?但二老前去青石铺,只是想化却这场纠纷,谷兄怕是误会两位高人的好意了。”当下便把与二人会晤的情形告知谷寒。
谷寒摇头道:“你当这两位高人的一番言语,江湖人士便能听进去?刘兄有所不知,兄弟出道这一年来,江湖中人皆欲以在下的头颅为扬名立万之物,什么寻仇之举,全是为名为利罢了!哼哼,只是在下的这颗头颅,却不是那么好拿的!”语气冰冷,刘三不禁感到一丝寒意。只听他又道:“只是如今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有家有业之人皆寻求自保,无暇顾及在下这颗头颅,否则在下岂不是又得远赴西域或是关外避祸?”
刘三沉默片刻,道:“江湖人心险恶,这是不错的。只盼谷兄好自为之,以德报怨,化干戈为玉帛。”
谷寒道:“刘兄,日后凌孤寒和谷寒这等名字,是不能再叫的。在下姓杨,祖父姓杨名讳涟,曾任左副都御史,因弹劾魏阉宗贤蒙冤致死,家父乃其二子,名讳之举,外祖王图,曾任礼部尚书,与祖父同为东林党人。天正四年,外祖被阉党陷害,被贬出京师,流落到那青石铺,那以后的故事,大家都是知道的。在下自当继承祖姓,以后便叫杨孤寒。”
紫儿惊讶道:“你祖上便是东林六君子的杨忠烈公?小女曾听家父多次提及忠烈公忠心报国,力战阉党之举。读忠烈公狱中血书,更是振聋发聩,有感恢弘正气塞于天地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文天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之于谦,也不过如此。小女虽为一介女流,但对忠烈公也是敬佩至极。”
杨孤寒苦笑道:“清廉忠义又有何用?先祖拥戴熹宗皇帝朱由校上位登基,但那皇帝还不是宠信阉党,忠奸不辩,以致先祖冤死狱中?外祖为国鞠躬尽瘁,还不是落得个罢官离京,客死他乡的凄惨下场?皇帝昏庸无道,朝纲败坏,祸害百姓,如今这天下大乱,我看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三点头道:“谷兄,不,杨兄见解独到,如今只盼有人振臂而呼,拨云见日,解救这天下苍生。”
杨孤寒道:“刘兄,放眼天下,你觉得有谁堪当此大任?”
刘三道:“李自成虽曾率众攻陷京师,但自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后,经山海关大战,民军损失惨重,放弃京师转战陕西、河南,尚有数十万之众,但身陷明、清大军重围,孤军奋战,形势堪忧。张献忠偏安于四川,虽与李自成相约共抗清兵,但自身应接不暇。如今弘光帝建国于南京,延续我朝的宗庙社稷,万民归顺,当能成就一统大业。”
杨孤寒摇头道:“刘兄错了,这福王虽已建国,但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桂王朱由榔等岂甘心北面称臣?更何况先帝的太子下落不明!福王朱由崧本昏庸无能之辈,更何况朝政被马士英、阮大铖等把控,史可法独木难支,只得退守扬州,如何能持久?若福王能与李闯联手抗清,当不乏明智之举,可叹大明遗臣皆视李闯为篡逆,势同水火,连史可法朝廷第一重臣都如此短视,如此必被大清各个击破,何来一统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