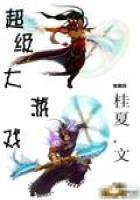记得那时我还是小女孩。大伯家摆酒席,来来往往的很多人。大伯家门前有厚厚一层的鞭炮纸。妈妈带我坐在靠窗的一桌。整个吃饭时间我一直看着旁边的那一桌,很多女孩子坐那一桌。她们都比我大,说话声音很细,吃饭很慢。她们大多数时间都低着头。那时我心里热切地想坐到那边去。那是一个小女孩所有的心思。我看着她们笑着交谈,看着她们眼神婉转,看着她们低头,头发倾泻而下,她们都有长长的头发。除了院里我认识的几个姐姐,还有我不认识的一些女孩子。那天的酒席,她们就那样点燃了整个厅堂。明眸皓齿,顾盼神飞。
据说那年住在我家上头的王叔叔,在春天的桃树上折了一段长长细细的枝条,再折成长短不一的几段,用红布包着桃枝的下端,上端露出来,看起来是一样长。他把院里的姐姐都叫来。大家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她们不知道。他握着红布裹着的桃枝的下端,让姐姐们每人抽一支。他还说你们看反正都是一样长的。随便抽吧。于是她们一人抽了一支。才发现桃枝是长短不一的。然后围在旁边的叔叔阿姨们开始比较,按从长到短的顺序排列。之华姐姐的最长,其次是清清姐,再是思媛姐姐,再然后是秧秧姐,最后是月菲姐姐。据说当时她们看着叔叔阿姨的笑容都莫名奇妙。王叔叔终于严肃地宣布:妹子家呀,以后你们都是要出嫁的,抽的签最短的最先嫁出去,最长的最后结婚。就是这个顺序了,再也错不了的。之华姐姐说:啊,这样原来我要最后才嫁哦。之华姐姐是那群女孩子里最好看的。王叔叔说:是的啊,你要最后嫁啰。月菲是王叔叔的女儿,很委屈地的说:哎呀,爸爸,我不要最先嫁。叔叔阿姨们大笑着说:这个可由不得你,这都是命呢。那时她们都是十五六岁,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不到一岁。她们是我记忆里的姐姐。
那时都是大家庭,她们家里兄弟姐妹少的都有四个,多的有六七个。家乡有一条大河。常见她们相约去河边洗衣服,拎着很大的桶。桶里是一家人的衣服。尤其是春天刚到的时候,有很稀薄的阳光。她们还要拎着全家的床单,被单,再加上寒冬来不及洗的厚衣服,在河边一蹲就是一个下午。据说邻村的叔叔在河里撑船,看见这群女孩,总是感叹,看见她们来河边洗衣服,就晓得,已经开春啦。她们从不单独去,每次都是约好的,在周末不去学校的时候。最是惊叹她们洗球鞋。因为上学要走很远的路,球鞋会弄得灰尘扑扑,白球鞋变成了黑球鞋,但是她们坚持一周洗一次,因为只有周末才有时间,每次都洗得刷白刷白。她们会把球鞋晒在一块,往往是猪圈的顶部,因为那个她们刚好够得到。记得有一次,大伯母去喂猪,回来后在晒谷场上跟大家说到:果些妹子家啊,鞋子洗得纸一样的白,晒在我家屋猪栏上,我去喂猪眼睛晃得只是眨。叔叔阿姨们又是一阵大笑。我也见过她们洗过的球鞋,跟新买的简直没有什么区别。家乡是一片片无尽的菜田,中间夹杂着一片片的水稻田。没有机械耕作,全是乡亲们自己亲手亲为。一年四季都很忙。连老人都很忙,每天都要看牛。女孩子们也很忙,要帮忙卖蔬菜,我们那边简称为卖菜。帮忙割草,帮忙煮饭。
月菲姐常常帮家里卖菜的。据说有一次在出桔子的月份,她帮家里卖菜,也捎带着卖一点桔子。她挑着菜与桔子走在黄土马路上,碰上了院子里一位叔叔,他顺便从她菜筐里拿了一个桔子,很快地吃掉。于是月菲姐大哭。这个故事在院子里传了十几年,现在还在传。叔叔阿姨们总说最老实的是清清姐姐。她是我大伯的女儿。我在大伯家里不经意地翻照片,看到清清姐17岁时候的照片,幽幽地站在阳光下,很白很温婉,那时她已经在很遥远的地方了。妈妈说清清姐其实是喜欢呆在家里,她不喜欢出门,话也很少,总是安静的模样。思媛姐姐住在我家隔壁,是真的只隔了一扇墙壁。我们住在晚清一位地主的宅院里,据说当年厅堂里还有慈禧太后赐的牌匾。但是我们住的时候院落已经很破败。我们住在正厅旁边的厢房里。思媛姐姐书读得很好。爸爸说我家安了电灯以后,她常常来我们家看书。她家是我们院子里最后安电灯的家庭。思媛姐姐家前有一棵很高大的桃树,当年王叔叔用来做签的桃枝就是这棵树上的。从我有记忆起那棵桃树就在屋前。到春天花瓣不时会飘落到我家窗前。思媛姐姐在桃树旁又种了葡萄树,藤蔓爬满了整棵桃树,以至于我长大了还总以为桃树和葡萄树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只是后来,桃树与葡萄都消失了。之华姐姐的美丽是远近闻名的。据说他们家总是出美女。她姑姑很美,却没有嫁人,和父母住了一辈子,四十多岁的时候离家,再也没有回来。很小的时候听人说,之华姐姐长得太像她姑姑,也许没有很好的命。我见到之华姐姐时总是觉得她有点神秘,不敢靠近。秧秧姐姐是在插秧的季节生的,所以叫秧秧。她总是笑,有两颗虎牙。小时候去放牛,有一次碰上了秧秧姐姐,寒冷的冬天早上,在河边,风很大。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忘了是怎样开始,她向我说出她很喜欢的一个男生的故事。大部分内容我都已经不记得。只是后来隐隐觉得其实那个男生也很喜欢她。后来我不经意地去过她家,看见一大丛芦荟。宽大的叶子,一片化不开的淡绿。
那些时光,有那么多女孩子。姐姐们成群结队。我有次去看闹热,是夏天。我家乡那边称有很多人参加的活动为闹热。结婚时红喜事,丧礼是白喜事。我那次去看的闹热是白喜事。出殡前一晚,办白喜事的人家照列要请一个戏班来唱戏。一般都是要唱整个晚上。我在戏台下,看见我们院里的姐姐们也在,就很开心。再仔细看看原来那边有一堆女孩子。都是临近的院落的姐姐们。她们坐在角落边,戏台强烈的灯光反射到那边就只是昏黄的光影了。她们轻声交谈,有时候笑声传过来,如银铃般。有个姐姐忽然笑着往我这边瞟过来,如惊鸿。她们穿着布裙子,胳膊露在外面。戏台上的戏当年是看不懂也不记得,却记得她们如花开般的笑声。
家乡有座小山,种满了桔树。每年都有人承包。承包的人需要交钱给村里。然后他要管理好桔树,秋天丰收了卖桔子的钱就归他。秋天来的时候,姐姐们是摘桔子的主力。承包桔园的人会上门去请她们。每年摘桔子的时节刚好也是放农忙假的时候。大叔大伯们则帮忙把一筐筐桔子挑下去。漫山遍野都是金黄金黄的桔子,搭配着青绿的叶子。姐姐和阿姨们轻快地爬上桔树,用小剪刀剪下一串串的桔子,递给桔树下的人,下面的人再递给站在筐边的人,筐边的人再把桔子放进箩筐。小孩子们则在树下来来往往地飞跑。桔子像是摘不完,也吃不完,满目都是金色。姐姐们在高兴地时候会唱起在学校里学的歌谣。她们在桔树上此应彼呼。在金秋的阳光里,那简直是姐姐们的盛会。
思媛家是姐姐们常去的地方。冬天的晚上她们围着火炉烤火,火炉在我们那边简称为灶。她们聊天,内容我也大都忘记,只记得当年我硬是要挤进去,听她们小声说话。冬天每家每户都有吃不完的白萝卜。霜降以后萝卜很甜。思媛姐姐的妈妈总是及时地削几个萝卜,分给大家吃。萝卜冰凉,丝丝浸入心田。思媛姐姐的妈妈叫行娘,爸爸叫行爷。行业的行。行娘不识字,肚子里却有一大堆的故事。姐姐们总是撺掇比她们小的女孩子唱歌。我总是唱《千年等一回》。那时奶奶家有了院子里唯一的一台黑白电视机,是遥远的舅爷爷寄回来的。我为电视机里的白娘子着迷,边唱边表演白娘子。惹得姐姐们咯咯直笑。有时候行娘也讲故事,讲大妹小妹的故事。大妹小妹的爸爸妈妈外出,叫她们在家栓好门。谁也不准进来。但是一只狼来了,披着她们外婆的皮。大妹小妹误以为狼是外婆,就让狼进来。然后是大妹小妹智斗大灰狼的故事。我是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百听不厌。听完故事姐姐们会很有兴致,有时候她们会模仿电视里的戏曲唱段。最让我忘不了的是之华姐扮宝玉,清清姐扮黛玉,唱那段:天下掉下个林妹妹,似朵彩云刚出浮。花鼓戏是她们都会唱的,唱《刘海砍樵》。唱着唱着屋里的人会越来越多,温暖热闹的冬天夜晚。外面则是大雪纷飞。
当年的我是如此沉迷于姐姐们的年华。总是想快点长大,快点拥有姐姐们那样的一笑一颦,点点滴滴。
后来,人总是要长大。那是90年代初的光阴。姐姐们十五六岁的年华。她们终于到了初中毕业。南方有了大发展,广州深圳的信息终于流传进了我们那深不可测的内地。没有争论没有比较,她们纷纷去了南方,远离家乡。总之有一天,姐姐们都不再在我身旁。我总觉得我的世界不再那么缤纷。去学校,再回家。与同学交谈也不多。时光就忽然变得很安静。我知道她们去了南方,知道她们去打工。当时打工一词,在家乡那边完全是褒义,完全是一种职业的称呼。比如说:你在做什么?打工。你在做什么?当老师。这两个回答没有任何区别。后来妈妈跟我说:你清清姐一点都不想去打工的。她还想继续读下去啊。但是贤哥哥要读书啊,后面还有两个妹妹。她必须出去打工的。我听到这里总是无语失神。小时候我也常常借思媛姐姐的语文书看,看里面的故事。思媛姐姐总是带回来一张张奖状。但是思媛姐姐也去了南方。后来,我去读寄宿高中,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也渐渐有了自己的世界,离那些姐姐们越来越远。我也以为自己会有美好的容颜,会有优雅的一笑一颦。小时候那桌酒席,那些美丽的往事,都埋在了记忆里。
她们去了远方。中间有好些年,我对她们全无了解。
但是记得那年年关,她们第一次从远方回来。买了很多的东西也买了很多糖果。小孩子一家家跑,去了这家去那家,兜里塞满了糖。她们又一起聚在思媛姐姐家里。于是她家里挤满了人。我在人群外,有很多大人向她们问题,她们一一回答,声音不大,我在人群外听不到。妈妈塞给我糖,让我回家。我退到门外,固执着不愿离开。终于人散尽。我看见她们都瘦得不得了的样子。看见了她们沾满风尘的鞋子。还是白色球鞋,只是尘埃显见。
高中偶尔回家,听到关于她们的只言片语,总是默然。妈妈有次说:贤哥哥读书要钱,伯伯问清清姐姐有没有,清清姐还没发工资,向同事借了800块钱寄了回来。我在桌前吃饭,感觉心里堵得慌。也听到说月菲姐姐在南方的某保龄球馆做得很好,交到了很有钱的男朋友。说行爷病了,思媛姐姐一次寄了很多钱给她爸爸治病。我不知道很多钱到底是多少。后来听说之华姐姐家里变得很有钱,之华姐姐的爸爸于是昂首挺胸阔气起来。说秧秧姐姐在南方有人给她做媒,但是她总是不愿意,不知道她到底在挑什么,自己本身条件也不是很好。我总是默默听着,默默吃饭。
后来。月菲姐姐带回一个黑黑胖胖的男人。妈妈说那人是南方生意人,很有钱,想快点娶月菲姐姐。我忽然想起那年在王叔叔家看月菲姐姐寄回的照片,照片里的月菲姐姐清雅如白月光。王叔叔是很愿意的。只是月菲姐姐的妈妈,哭得很伤心。她有两个儿子,却只有这一个女儿,她不想女儿远嫁。妈妈说:但是王叔叔已经点了头,哪由得她不答应。于是月菲姐姐顺理成章地嫁到了远方。月菲姐姐妈妈去参加婚礼回来,打扮成了城里太太的样子,被大家嘲笑了一番。王叔叔两夫妻还是院子里第一次坐飞机的人。于是大家又很羡慕。只是月菲姐姐为了一个桔子大哭的故事还在院子里流传。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月菲姐姐,她是回来过的,但是我在学校不在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她。
清清姐姐写信回来说她有了男朋友,就是邻村人。大伯有点不知所措。于是去调查。说原来那个男子的爷爷辈还在乞讨,这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嫁给这样一个人。清清姐姐说,他对我好,我就是要跟他。在城里的姑姑回家来说,等清清回来,我给她做媒,让她嫁到城里去。我不知道清清姐姐的男朋友是什么模样。后来大伯收到一封字迹清丽的长信,是那个男子写来的。里面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从此大伯就不再反对清清姐姐与那位男子在一起。大伯说字能写得这样的人,一定坏不到哪里去。我见到那位姐夫,清秀如枫树。贤哥哥比清清姐姐大两岁,但是清清姐姐比他先结婚。清清姐姐后来生了一个女儿,跟她长得一模一样。
行爷病重,思媛姐姐赶回来。据说行爷想在自己临终前让思媛姐姐嫁掉,于是催着她结婚。一时间做媒的人简直要踏破思媛姐家的门槛。我见过一位很帅气的男子帮思媛姐姐家挑水。妈妈说那个伢子家很愿意和思媛好呢。我们那里称还未结婚的男孩子为伢子家。有一次那位男子敲我家的门,问妈妈知不知道思媛姐姐去哪里了。妈妈说不知道,怕是走亲戚去了。然后他就问去哪位亲戚家了。妈妈说去她舅舅那里了吧。于是他急冲冲走掉。他走后,妈妈说思媛又去相亲了,行爷嫌这伢子家太好看,不可靠呢。思媛姐姐第二次相亲的男子长得不好看。但是行爷说男人长得好看有什么用。思媛姐姐就嫁给了那位很不好看的男子。她结婚不多久,行爷就去世了。行爷去世以后行娘嫌桃树在门前挡了太阳,就砍掉了它。桃树砍掉后,没过多久葡萄树也枯死了。多年后我再见到思媛姐姐的丈夫,满脸的黄斑,思媛姐姐却还依稀见当年秀丽的影子。妈妈说当年那位长得很好看的伢子家还真的跑到思媛舅舅家呢,闹了个笑话。
有年冬天,王叔叔在我家。说起那年让女孩子抽签的事。感叹道:之华现在嫁不嫁反正没事,但是秧秧为什么挑来挑去呢。25岁的人了,再不嫁就没人要了啊。我们那边不在读书的女孩子超过24岁就已经算是大龄女子了。秧秧姐姐的妈妈当时很是着急,不准秧秧姐出去打工,专门留在家里相亲。说有一次秧秧姐姐被逼急了,在楼上一个多月没下来,不愿见人。大家都不理解,秧秧姐姐到底在想什么。终于秧秧姐的妈妈还是放了她走。她说:我的事,不用你们操心。后来她还是嫁掉,嫁给谁我不知道。妈妈说是个不错的伢子家。妈妈还告诫我说:你以后找男朋友不要挑三挑四,大人难操心。后来读大学每次春节回家,爸爸都去秧秧姐家摘芦荟叶子。于是我就用芦荟叶子搽脸。这是后来我跟秧秧姐唯一的联系。
只有之华姐姐,还是未嫁。之华姐姐多年来只回来过一次。但是却有源源不断的钱寄回家。于是她家修了院子里最漂亮的房子。妹妹上了一所本科大学,弟弟则去很贵的电脑学校学了电脑。大人们提到之华姐姐时总是说:之华啊,见惯了外面的花花世界,怎么得愿意回来我们这个小地方。叔叔们说:之华在做什么,大家心里有数,只是不说出来罢了。她二十七岁那年回来。说是不再去南方。她还是以前那么好看。皮肤白得像雪。他们说这是因为长期没有见到阳光的原因。我不明白为什么长期见不到阳光,去外面晒晒就可以了嘛。但是我不敢问。她总是神情凛冽,与人打招呼也是淡淡的,微笑一下下。有次我和妈妈在路上遇到她,她问我在做什么事,我说在读书。她就很高兴地说读书好啊,要好好读,要加油。我只是呆呆望着她美丽的脸庞,那张对于我来说还是很神秘的脸。不断有人为之华姐姐做媒。据说她一般连正眼都不看人家一眼。她好像谁都看不上,人啊,如果见了大世面,再回到这种小地方,过温开水一样的日子,是很烦心的。王叔叔这样说。我觉得没有人能配得上之华姐姐。但是总要嫁人的啊,妹子家不嫁人是不可能的。妈妈总是这样感叹。
大三那年寒假我回家,妈妈问我要不要去参加酒宴。我问谁家摆酒席。她说之华姐姐要出嫁了。我忽然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摇摇头。那个下午,我站在窗前,阳光透进来,洒在房间。我闭着眼睛,想象我去参加酒宴的场景。踏过红红的鞭炮纸,坐在靠窗的那一桌。那一刻,桃花纷飞,如我记忆里的小时候。
杨斑斓
2015年6月26日于深圳
这是斑斓写的第一篇小说,其实也算不得是小说,这是关于故乡的真实记忆。
斑斓出生的时候,窗前的桃花树开了满树的桃花,正是初春季节,南方阴冷潮湿,杨家老宅高高的拱形院墙在晨光中露出简洁的轮廓,似在发出轻微的叹息。斑斓的姐姐,关斓,守在里屋门外,好奇地听着屋内的一切声响。关斓才两岁,听见孩子的啼哭声,蹦跳着跑去对坐在灶房的父亲杨盛说:妹妹出来了。杨盛神情淡漠,哦了一声。
除去出生的地方,斑斓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就是上海。上海总是下雨。斑斓已经习惯那种绵绸的雨,细细的冰冷的,结成轻薄的雾气,把天空渲染成深青色。上海的天空总是空气沉沉的样子,天被压得很低,潮湿清冷压抑。
所以现在斑斓很不习惯深圳这炎热的天气。斑斓走到窗前看着窗外叶子广阔肥大的棕榈树,忽然就哗啦啦下起了大雨,玻璃上瞬间就挂满一道道水珠。阵阵泥土的气息传出来,斑斓想起小时候,家乡仙南镇的夏天,暴雨过后空气中青草的味道以及菜田里魔法般蹦出来的蘑菇。
来深圳的第一晚,斑斓做了一个梦。梦到了自己无拘无束地在老家仙南镇上空飞翔,盛夏时节,斑斓飞在空中,越过大片金黄的农田,越过荷叶亭亭的池塘,越过水草丰美的慈江,越过漫山的桔园,停在了杨家老宅的破败的大门前,望着年久失修泛着青色的高高院墙,盯着看老宅上空的白云朵朵,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梦里斑斓很快乐,看到了老宅东厢房正厅的雕花木门前,长长的盛开着淡黄色小花的丝瓜架下,爷爷摇着蒲扇坐在藤椅上,看着鸭子在大门口吃稻谷。
在梦里见到爷爷,斑斓惊醒了。爷爷早已经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