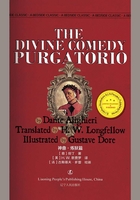“捉着了吗?打!打死他!”这时孩子的母亲带着几个女人也来了。她们都动手打起来。万福便跨在他的头上,两腿紧紧的夹住了他的头。
“饶了罢!饶了罢!下次不敢了!”
打的人完全不理他,只是打。阿长只好服服贴贴的伏在地上,任他们摆布了。
但智慧是不会离开阿长的脑子的。他看看求饶无用,便想出了一个解围的计策。
“阿呀!痛杀!背脊打断了!腰啦!脚骨啦!”他提高喉咙叫喊起来,哭丧着声音。
“哇……哇!哇……哇哇!”从他的口里吐出来一大堆的口水。
同时,从他的裤里又流出来一些尿,屁股上的裤子顶了起来,臭气冲人的鼻子,——屎也出来了!
“阿呀!打不得了!”妇人们立刻停了打,喊了起来,“尿屎都打出了,会死呢!”
连万福也吃惊了。他连忙放了阿长,跳了开去。
但阿长依然伏在地上,发着抖,不说一句话,只是哇哇的作着呕。
“这事情糟了!”万富嫂说,牵着一个妇人的手倒退了几步。
“打死是该的!管他娘!走罢!”万福说。
但大家这时却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只得退了几步,又远远的望着了。
阿长从地上侧转头来,似乎瞧了一瞧,立刻爬起身来,拾了空盘,飞也似的跑着走了。一路上还落下一些臭的东西。“嘿!你看这个贼骨头坏不坏!”万福叫着说,“上了他一个大当!”
于是大家都哈哈大笑了。
在笑声中,阿长远远地站住了脚,抖一抖裤子,回转头来望一望背后的人群,一眼瞥见了阿芝的老婆露着两粒突出的虎牙在那里大笑。
“我将来报你的恩,阿芝的老婆!”他想着,又急促的走了。
约有半年光景,阿长没有到史家桥去。
他不再卖大饼,改了行,挑着担子卖洋油了。
一样的迅速,不到两个月,他的两肩非常适合于扁担了。沉重的油担在他渐渐轻松起来。他可以不用手扶持,把担子从右肩换到左肩,或从左肩换到右肩。他知道每一桶洋油可以和多少水,油提子的底应该多少高,提子提很快,油少了反显得多,提得慢,多了反显得少。他知道某家门口应该多喊几声,他知道某家的洋油是到铺子里去买的。他挑着担子到各处去卖。但不到史家桥去。有时,偶然经过史家桥,便一声不响的匆匆地穿过去了。
他记得,在史家桥闯过祸。一到史家桥,心里就七上八下的有点慌张。但那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闯了这样的大祸,是谁的不是呢?——他不大明白。
就连那时是哪些人打他,哪个打得最凶,他也有点模糊了。他只记得一个人:露着两粒突出的虎牙,在背后大笑的阿芝的老婆!这个印象永久不能消灭!走近史家桥,他的两眼就发出火来,看见阿芝的老婆露着牙齿在大笑!
“我将来报你的恩!”他永久记得这一句话。
“怎样报答她呢?这个难看的女人!”他时常这样的想。
但智慧不在他的脑子里长在,他怎样也想不出计策。
“卖洋油的!”
一天他过史家桥,忽然听见背后有女人的声音在叫喊。他不想在史家桥做生意,但一想已经离开村庄有几十步远,不能算是史家桥,做一次意外的买卖也可以,便停住了。
谁知那来的却正是他的冤家——阿芝的老婆!
阿长心里有点恐慌了,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只是呆呆地望着阿芝的老婆。
阿芝的老婆似也有点不自然,两眼微微红了起来,显然先前没有注意到这是阿长。
“买半斤洋油!”她提着油壶,喃喃的说。
“一百念!”阿长说着,便接过油壶,开开盖子,放上漏斗,灌油进去。
“怎样报复呢?”他一面想着,一面慢慢的提了给她。但智慧还不会上来。
“啥啥!还有钱!”阿芝的老婆完全是一个好人,她看见阿长挑上了担子要走,忘记拿钱便叫了起来,一只手拖着他的担了,一只手往他的担子上去放钱。
在这俄顷间,阿长的智慧上来了。
他故意把肩上的担子往后一掀,后面的担子便恰恰碰在阿芝老婆的身上。碰得她几乎跌倒地上,手中的油壶打翻了。担子上的油泼了她一身。
“啊呀!”她叫着,扯住了阿长的担子。“不要走!赔我衣裳!”
“好!赔我洋油!谁叫你拉住了我的担子!”
“到村上去评去!”阿芝的老婆大声的说,发了气。
阿长有点害怕了。史家桥的人,在他是个个凶狠的。他只得用力挑自己的担子。
但阿芝的老婆是有一点肉的,担子重得非常,前后重轻悬殊,怎样也走不得。
“给史家桥人看见,就不好了!”他心里一急,第二个智慧又上来了。
他放下担子,右手紧紧的握住了阿芝老婆攀在油担上的手,左手就往她的奶上一摸。阿芝老婆立刻松了手,他就趁势一推,把她摔在地上了。
十分迅速的,阿长挑上担子就往前面跑。他没有注意到阿芝老婆大声的叫些什么,他只听见三个字:
“贼骨头!”
阿长心里舒畅得非常。虽然泼了洋油,亏了不少的钱,而且连那一百念也没有到手,但终于给他报复了。这报复,是这样的光荣,可以说,所有史家桥人都被他报复完了。
而且,他还握了阿芝老婆的肥嫩的手,摸了突出的奶!这在他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女人的肉是这样的可爱!一触着就浑身酥软了!
光荣而且幸福。
三
有趣呀面孔上的那两块肉——可恼恶狠狠的眼睛——乘机进言——旁观着天翻地覆——冤枉得利害难以做人阿长喝醉了酒似的,挑着担子回到家里。他心里又好过又难过,有好几天只是懒洋洋的想那女人的事。但他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一会想到这里,一会又想到那里去了。
“女人……洋油……大饼……奶……一百念……贼骨头……碰翻了!……”他这样的想来想去,终干得不到一个综合的概念。
然而这也尽够他受苦的了,女人,女人,而又女人!
厌倦来到他的脑里,他不再想挑着担子东跑西跑了。他觉得女人是可怕的,而做这种生意所碰着最多的又偏偏是女人。于是他想来想去,只有改行,去给撑划子的当副手。他有的是气力。坐在船头,两手扳着桨,上身一仰一俯,他觉得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新的行业不久就开始了。
和他接触的女人的确少了一大半。有时即使有女人坐在他的船里,赖篷舱的掩遮,他可以看不见里面的人了。
但虽然这样,他还着了魔似的,还不大忘情于女人。他的心头常常热烘烘的,像有滚水要顶开盖子,往外冲了出来一般,——尤其是远远地看见了女人。
其中最使他心动的,莫过于堂房妹妹,阿梅这个丫头了!
她每天坐在阿长所必须经过的大门内,不是缝衣就是绣花。一到大门旁,阿长的眼光就不知不觉的射到阿梅的身上去。
她的两颊胖而且红,发着光。
他的心就突突跳了起来,想去抱她。想张开嘴咬下她两边面颊上的肉。
在她的手腕上,有两个亮晶晶地发光的银的手镯。
“值五六元!”阿长想,“能把这丫头弄到手就有福享了——又好看又有钱!”
但懊恼立时上来了。他想到了她是自己的族内人,要成夫妻是断断做不到的。
懊恼着,懊恼着,一天,他有了办法了。
他从外面回来,走到阿梅的门边,听见了一阵笑声。从玻璃窗望进去,他看见阿梅正和她的姊夫并坐在床上,一面吃着东西,满面喜色,嘻嘻哈哈的在那里开玩笑。
“我也暗地里玩玩罢!”阿长想。
他开始进行了。
头几天,他只和她寒暄,随后几天和她闲谈起来,最后就笑嘻嘻的丢过眼色去。
但阿梅是一个大傻子,她完全不愿意,竟露着恶狠狠的眼光,沉着脸,转过去了。
这使他难堪,使他痛苦,使他着恼;他觉得阿梅简直是一个不识抬举的丫头,从此便不再抬起头来,给她恩宠的眼光了。
阿梅有幸,她的父母很快的就给她找到了别的恩宠的眼光,而且过了两个月,完全把阿梅交给幸福了。
他是一个好休息的铜匠,十天有九天不在店里,但同时又很忙,每夜回家总在十二点钟以后。阿才赌棍是他的大名。他的家离易家村只有半里路。关于他的光荣的历史,阿长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最不喜欢他左颊上一条小刀似的伤疤。他觉得他的面孔不能再难看了。
“不喜欢人,却喜欢鬼!”阿长生气了,他亲眼看着阿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头上插着金黄的钗,两耳垂着长串的珠子,手腕上的银镯换了金镯,吹吹打打的抬了出去。
“拆散你们!”阿长怒气冲冲的想。
但虽然这样想着,计策却还没有。他的思想还只是集中在红而且胖的面颊,满身发光的首饰上。
“只这首饰,便就够我一生受用了!”他想。
一天上午,他载客到柳河头后,系着船,正在等候生意的时候,忽然看见阿才赌棍穿得斯斯文文,摇摇摆摆的走过岭来。阿长一想,这桩生意应该是他的了。于是他就迎了上去,和阿才打招呼。阿才果然就坐着他的船回家,因为他们原是相熟的,而现在,又加入一层亲戚的关系了。
“你们到此地有一会了罢?”阿才开始和阿长攀谈了。
“还不久。你到哪里去了来?”阿长问。
“城里做客,前天去的。”
“喔!”
“姑妈的女昨天出嫁了。”
“喔!”
“非常热闹!办了二十桌酒!”
“喔,喔!”
阿长一面说着,一面肚子里在想办法了。
“你有许久不到丈人家里去了罢!”阿长问。
“女人前几天回去过。”
“是的,是的,我看见过!——胖了!你的姨丈也在那里,他近来也很胖。有一次——他们两人并坐在床上开玩笑,要是给生人看见,一定以为是亲兄妹喽!”
“喔!”阿才会意了。“你亲眼看见的吗?”
“怎么不是?一样长短,一样胖……”阿长说到这里停止了。智慧暗中在告诉他,话说到这里已是足够。
阿才赌棍也沉默了。他的心中起了愤怒,脸色气得失了色,紧紧咬住了上下牙齿。在他的脑中只旋转着这一句话:“他们并坐在床上开玩笑!”
懒洋洋地过了年,事情就爆发了。
那天正是正月十二日,马灯轮到易家村。阿梅的父母备了一桌酒席,把两个女婿和女儿都接了来看马灯。大家都很高兴,只有阿才看见姨丈也在,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他想竭力避开他,但坐席时大家偏偏又叫他和姨丈并坐在一条凳上。阿才是一个粗货,他喝着酒,气就渐渐按捺不住,冲上来了。他喝着喝着,喝了七八分酒,满脸红涨,言语杂乱起来。
“喝醉了,不要喝了罢!”阿梅劝他说,想动手去拿他的酒杯。
“滚开!狗东西!”阿才睁着凶恶的两眼,骂了起来,提起酒杯就往阿梅的身上摔了过去,泼得阿梅的缎袄上都是酒。
一桌的人都惊愕了。
“阿才醉了!快拿酱油来!”
但阿才心里却清醒着,只是怒气按捺不住,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便佯装着酒醉,用力把桌子往对面阿梅身上推了过去。“婊子!”
一桌的碗盆连菜带汤的被他推翻在地上,连邻居们都听见这声音,跑出来了。
“你母亲是什么东西呀!”阿才大声的叫着说,“你父亲是什么东西呀!哼!
我不晓得吗?不要脸!
“阿才,阿才!”阿梅的父亲走了过去,抱着他,低声下气的说,“你去睡一会罢!我们不好,慢慢儿消你的气!咳咳,阿才,你醉了呢!自己的身体要紧!先吃一点醒酒的东西罢!”
“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我醉了吗?一点没有醉!滚开!让我打死这婊子!”
他说着提起椅子,想对阿梅身上摔去,但别人把他夺下了,而且把他拥进了后房,按倒在床上。
这一天阿长正在家里,他早已挤在人群中观看。大家低声的谈论着,心里都有点觉得事出有因,阿才不像完全酒醉,但这个原因,除了阿长没有第二个人明白。
“生了效力了!”阿长想。
许久许久,他还听见阿才的叫骂,和阿梅的哭泣。他不禁舒畅起来,走了。
但是这句话效力之大,阿长似乎还不曾梦想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祸事愈演愈大了。阿才骂老婆已不仅在酒醉时,没有喝酒也要骂了;不仅在夜里关了门轻轻的骂,白天里当着大众也要骂了;不仅骂她而且打她了,不仅打她,而且好几次把她关禁起来,饿她了;好几次,他把菜刀磨得雪亮的在阿梅的眼前晃。
阿梅突然憔悴了下来,两眼陷了进去,脸上露着许多可怕青肿的伤痕,两腿不时拐着,随后亲家母也相打起来,亲家翁和亲家翁也相打起来,阿梅的兄弟和阿才的兄弟也相打起来——闹得附近的人都不能安静了。
阿才是一个粗货,他的嘴巴留不住秘密,别的人渐渐知道了这祸事的根苗,都相信是阿长有意捣鬼,但阿才却始终相信他的话是确实的。
“是阿长说的!”有一天,阿才在丈人家骂了以后,对着大众说了出来。
“拖这贼骨头出来!”阿才的丈人叫着,便去寻找阿长。
但阿长有点聪明,赖得精光。阿才和阿梅的一家人都赶着要打他,他却飞也似的逃了。
那时满街都站满了人,有几个和阿梅的父亲要好的便兜住了阿长。
易家村最有权威的判事深波先生这时正站在人群中。阿梅的父亲给了阿长三个左手巴掌,便把他拖到深波先生的面前,诉说起来。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天在头上!冤枉得好利害!我不能做人了!”阿长叫着说。
深波先生毫不动气的,冷然而带讥刺的说:
“河盖并没有盖着!”
这是一句可怕的话,阿长生长在易家村,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不能做人——跳河!
“天呀!我去死去!”阿长当不住这句话,只好大叫起来,往河边走去。
没有一个人去扯他。
但阿长的脑子里并不缺乏智慧。他慢慢的走下埠头,做出决心跳河的姿势,大叫着,扑了下去。
“死一只狗!”河边的人都只转过身去望着,并不去救他,有几个还这样的叫了出来。
“呵哺——呵哺!天呀!冤枉呀!呵哺——呵——哺!”
岸上的人看见阿长这样的叫着,两手用力的打着水,身子一上一下的沉浮着,走了开去。——但并非往河的中间走,却是沿着河塘走。那些地方,人人知道是很浅的,可以立住脚。
“卖王了!卖工了!”岸上的人都动了气,拾起碎石,向阿长摔了过去。
于是阿长躲闪着,不复喊叫,很快的拨着水往河塘的那一头走了过去,在离开人群较远的地方,爬上了岸,飞也似的逃走。
他有三天不曾回来。随后又在家里躺了四五天,传出来的消息是阿长病了。
四
其乐融融——海誓山盟——待时而动——果报分明阿长真的生了病吗?——不,显然是不会的。他是贼骨头,每根骨头都是贱的。
冷天跳在河里,不过洗一澡罢了。冻饿在他是家常便饭。最冷的时候,人家穿着皮袄,捧着手炉,他穿的是一条单裤,一件夹袄。别人吃火锅,他吃的是冷饭冷菜。
这样的冬天,他已过了许多年。他并非赚不到钱,他有的是气力,命运也并不坏,生意总是很好的。但一则因为他的母亲要给他讨一个老婆,不时把他得来的钱抽了一部分去储蓄了,二则他自己有一种嗜好,喜欢摸摸牌,所以手头总是常空的。其实穿得暖一点,吃得好一点,他也像别的人似的,有这种欲望。——这可以用某一年冬天里的事情来证明:
那一年的冬天确乎比别的冬天特别要寒冷。雪先后落了三次。易家村周围的河水,都结了坚厚的冰,可以在上面走路了。阿长做不得划船的买卖,只好暂时帮着人家做点心。这是易家村附近的规矩,每年以十一月至十二月,家家户户必须做几斗或几石点心。这是有气力的人的勾当,女人和斯文的人是做不来的。阿长是一个粗人,他入了伙,跟着别人穿门入户的去刷粉,舂粉,捏厚饼,印年糕。
有一天点心做到邻居阿瑞婶家里,他忽然起了羡慕了。
阿瑞婶家里陈设得很阔气,满房的家具都闪闪地发着光,木器不是朱红色,就是金黄色,锡瓶和饭盂放满了橱顶,阿瑞婶睡的床装着玻璃,又嵌着象牙,价值总在一百五六十元。她原是易家村二等的人家。阿瑞叔在附近已开有三爿店铺了。
阿长进门时,首先注意到衣橱凳上,正放着一堆折叠着的绒衣。
“绒衣一定要比布衣热得多了!”阿长一面做点心,一面心里羡慕着。绒衣时时显露在他的眼前。他很想去拿一件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