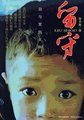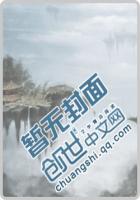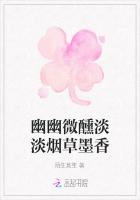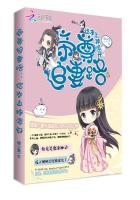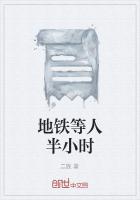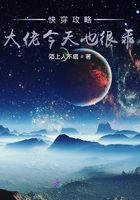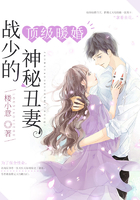让我们看看他在邢台县一天活动的日程。十月十日上午九点钟,按照头一天的约定,高扬一行乘坐的“面包车”,由临城县来到邢台县野沟门水库的大桥上,与********白少玉的吉普车会合了。吉普车引路,他们径直前往胡家楼大队的寺沟。当年,这是一条乱石滚滚的“光屁股沟”,从五五年开始综合治理,成功地经受了六三年特大洪水的考验,被省报赞为“暴雨摧残处,百花依然红”的奇迹。
如今在这三里长沟行走,可以人不出树萌,脚不沾泥土,地表全被树木和海绵般的草皮所覆盖。高扬一边察看,一边兴致勃勃地同治山的带头人、当年边区的劳动模范马聚山老汉交谈……
已经十点多了。县里的同志提议到公社去吃午饭,髙扬说:“接着走。”于是沿山沟上行到了稻哇村。在供销社值班打更的小屋里,高扬邀请几位老党员开了座谈会。之后,顺着佛堂沟,察看了县社队合营的万亩林场,看望了当年的边区劳动模范郭爱妮老大娘。等他们赶到浆水公社吃午饭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
十月的天气还相当炎热,火暴暴的太阳晒得人们不住地沁出汗水。已经一上午没歇脚了,吃了午饭,高扬紧接着又驱车前往最边远的水门大队。他沿着盘旋山路,徒步登上山头,察看了他们在六三年洪灾之后重建的古城堡似的梯田。
离开水门,他们访问了抗大总校住过的前南峪大队。在这里,高扬走访了三户老干部、老烈属和十几户农民家庭;乘车察看了大队重点治理的三条“经济沟”。党支部书记郭成志是个能干的年轻人,他们以感人下泪的热忱和优厚的待遇,从唐山请来“板栗大师”王金章,大力推广先进技术,使本队果品产量连年大增。坐在果园的树荫下,高扬饶有兴致地听取了他的汇报,直到傍晚才罢。
头一天,********白少玉曾请示高扬一行到邢台的食宿怎样安排,高扬让人答复:不要安排,走到哪儿住到哪儿。现在走到浆水公社了,怎么住呢?公社连个招待所也没有,只是供销社有几间供过往购销人员住的客房,实在太寒碜。白少玉说:“回县里住吧,汽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明天可以再去。”
高扬说:“时间都扔在路上了。就住这儿。”保卫干部为难了:“这儿连个围墙也没有,不好安排警卫呀。”
高扬说:“别管那些。当年我在这儿,整天走沟过涧的,也没人害我,今天还有什么问题!”
他就在这儿住了两宿,利用晚上时间,开了两次老党员、老干部座谈会。
供销社的食堂是个半面没墙的棚子,饭菜一端上来,苍蝇蜂拥而至,碰头碰脸。司机小陶一次就从醋瓶里倒出三只苍蝇。高扬在这里吃了六顿饭;四菜一汤,还特意按高扬的嘱咐,捎带蒸了些山药蛋、胡萝卜和莱窝窝,他每样都尝了尝。由于连日奔走和饮食不善,秘书和一位随行人员病倒了,中途返回了邢台。七十二岁的第一书记却依然精神饱满,在太行山里越走越深……
“十二大”以来,经过三个地区近二十个县市的调查研究,他觉得心中有点“数”了,召开一次地市********会议,研究如何开创农业生产新局面的时机已经成熟。开始,农业部门提出要在会上讨论八个议题。高扬说,议题多了,就没有议题。回到省城,他根据自己的调査所得,会同调査回来的省长刘秉彦、常务书记张曙光等同志的意见,亲自拟定了“促进联产承包责任制向横宽纵深发展”等三个专题。经常委会讨论后,责成有关部门抽调得力干部,按三个专题分头下去调査。高扬同时又再次下去调査了十八天。三个文件起草出来后,又派调查组带上文件草稿分三路下去征求广大基层干部和重点户、专业户的意见。
这在当时还是三个新鲜的课题,是在河北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三棵新苗,其中有些提法在上头文件里是找不到的,有人担心会不会与中央精神不一致。会议开幕前夕,中央一九八三年一号文件下达了。大家一对照,省委的文件与中央文件的精神丝丝入扣,对上“口径”了!
这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它不仅为河北农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在人们心理上引起了微妙的震动:省委的作风变了!河北的干部和群众开始有了自信,他们正走在中央指引的道路上。他们为此而感到踏实,感到自豪,不象前几年,只在大标题上与中央保持“一致”那样,令人惴惴不安,啼笑皆非。
这次会议之前,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八二年十一月,高扬到邯郸市研究中小型工业企业问题。十天之内,他看了十个厂矿,昕取了市委及下属四个部门的汇报。这天晚上,他同千部谈完话,已近十点了。他向秘书甄树声打招呼说:“晚上我要写稿了。”预定第三天他将在干部大会上讲话。
十二点,他房间的灯还亮着,秘书先睡了。第二天早晨,秘书走进他的房间,见他的灯仍亮着,不禁有些吃惊。髙扬解释说:“啊,早晨起来我又写了一会儿。”上午他还要开会。小甄把他昨晚写的抄出来,共有三千五百字,这就是后来在全省中小工业整顿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五条意见”。
定稿之前,小甄提了条意见。稿中原有一句:“不要盲目提翻番”。小甄说:“这句话是否改一下,或者不要?”
“为什么?”高扬问。小甄说:“十二大刚提出翻番的口号,现在叫得正响,这样提……”不言而喻,有“唱反调”之嫌。高扬说:“我这个翻番,前面是加了限制词盲目的嘛。中央提翻番,是以一九八〇年全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起点的,是经过了计算的。可是具体到某个单位就不同了。比方说:刚生下来的孩子,五岁以前身高、体重可以翻一番,到了十八岁还能翻吗?那不是假、大、空吗?”
下午,他召集当地一些负责同志,念了稿子,征求了意见,之后又让随行的“秀才”们再推敲一下。不料省委副秘书长肖风又把这句话划掉了。高扬摇摇头说:“你们哪,就是怕我和中央不一致,怕我犯错误。好吧,少数服从多数。但是你们这个思想不对头。”
这里也许可以套用一下“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句老话。“******”年代,高扬以中央工业工作部副部长身份下去检查工作,曾对所谓“大炼钢铁”等违背科学的作法提出异议,而且诉诸文字,据理力争,他因此得了一顶“****机会主义分子标杆”的帽子。下放两年之后,担任化工部长期间,仍不“改悔”,看到上送的报告中某些在什么“指引下”、“鼓舞下”、“照耀下”之类套话,他就说:“这是给中央看的工作报告,罗列这些干什么!”于是动笔划掉。这些时髦的“铁证”又使他戴了十一年“****分子”的帽子。看来,五九年反****和“**********”两次被打倒,并没有教这位刚正的共产党员学会“见风使舵”,甚至没有学会起码的世故和圆滑。他是那么自信,就象农民坚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样,他坚信,实事求是的种子点进哪里的泥土都不会长出别的苗儿来,虽然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难怪肖风多次感慨:“高扬同志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和善于把中央精神和河北实际高度结合。”他说这话是经过对比的。他在省委机关工作几十年,可算是秘书班子里的历代元老。他曾亲见有的领导专靠揣摸上级喜好来决定自己的态度。上级喜欢听什么,他就讲什么;上面讲八分,他就讲十分,上面讲十分,他讲十二分。上面开个什么会,他也开个什么会,甚至到会人员的身份、会议程序都照套不变。他从这种“领导方法”中得到孓不小的甜头,至于老百姓得到的是否也是甜头,那他就管不着了。
“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当高扬抱定“走到哪儿就住哪儿”的方针,在太行山里越走越深,在浆水供销社那样的“客房”下榻的时候,有人已经在邢台地委的招待所门前等他了。“这是一位五十六岁的老太太,叫徐秀英。象山里的多数农妇那样,她将花白的头发用一块褐色头巾裹着;这头巾是件宝,遮荫凉、挡风寒、提东西、擦眼泪……都是它。她走路有点蹒跚,不难看出,她的鞋尖有一半牽空的——那是一双“解放”牌的缠足。
十月十日,高扬没到市里来;十一日,他还没来……徐秀英叹息一声,扯下头巾擦擦眼泪,第二天又来……她在这样的路上,已经奔走五年了……
一九四七年,这位二十一岁的山里姑娘就当了村长,第二年入了党。一九五六年,她已是邢台县手工业联社组干科的副科长了。从一九六一年起,她参加调查一桩牵涉到某些领导干部的贪污腐化案,案子未结,“**********”开始了。一些心里有鬼的人要她交出材料,她恪守职责就是不交;她一日不交,人家就一日不舒服。祸根儿就从这埋下了。
一九七二年,她发现二轻局经理部仓库保管员陈XX有盗卖钢材、私吞货款行为,七三年、七四年、七五年,她和其他同志又多次将陈XX査获。作为政工办公室负责人,她多次向领导反映,某位副局长却一再阻挠,不让深究。
陈XX为什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贪污盗窃而又不被追究呢?群众洞若观火。有人说:陈XX想捞一千元,他就得贪污两千元,留出一千打通关节。不然人家那么卖力给他打掩护?
一次,一位同志对徐秀英说:“明摆着,咱要再查,就得受打击。”徐秀英答道:“咱们都是老党员了,宁可受打击也不能昧良心,丢原则。”不久,经理部为了同东北林区拉关系搞木材,违反规定动用库里钢材换来白面、香油、花生米、自行车等去送礼,徐秀英坚决反对,并向上报告了这件事。这又在旧帐上加了新“债”。显然,一场“明摆着”的打击报复正等待着他。
天遂人愿,“机会”送上门来了。一九七七年五月,二轻局的卡车在外县轧伤了人,局里派徐秀英和曹济川去处理善后事项。执行任务时,徐秀英被歹徒打成脊椎骨折,衣食不能自理。这是工伤,本应由局里负责护理,局里不管;派个人去找肇事者所在单位,由他们负责总可以吧?连这事也不管。徐秀英的老伴,原地区农业局副局长胡芸阁,“****”中被毒打致伤,七四年从干校回来不久就去世了。七六年,她的小儿子又在唐山地震中遇难夭亡。如今大儿子在部队服役,女儿在十几里外的工厂上班,谁能照顾她呢?她孤独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以泪洗面。多年来,她已经习惯于把一切希望都寄托给党了。七四年到七七年,一连串的不幸没有把她压倒,她忍着悲痛,为揭发坏人,为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四处奔波,调査材料。可是今天,她觉得再没什么可依靠了。她毕竟是个女人哪!她想到了死,想到了自杀……
她的心思被女儿看出来了,被一些老同志知道了,局里的群众也偷偷地来看她。人们劝她:“老徐,你可不能死啊!你一死,那案子的材料不就落在人家手里了?人家正盼你死哩!”一句话把她震醒了:“就为了这场斗争,我也得活下去!”她终于敖过来了。
但是,这年十月:徐秀英刚能活动,局党委便做坦决定,让徐秀英交出了陈XX的全部材料。材料一交,公开的打击报复就开始了:政工办公室另派了负责人,她实际上已被剥夺了职务。紧接着,他们又利用揭批“******”的第三战役的机会,在办公楼里贴满了“揭批”徐秀英的大字报,说她“****”中“踹人两皮鞋”,(徐秀英是小脚,一辈子没穿过皮鞋。)又说她从一个老干部家里抄走“八双象牙筷子”。(此人年年吃救济,他买得起象牙筷子吗?)并说这标志二轻局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组织全系统的人来参观。此后又扣发了她上访期间的工资,取消了她的奖金~这种“奖金”每人都有,包括贪污分子陈XX,唯独“反贪污分子”徐秀英没份儿!
不法横行的当权者,用自己的双手垒起了债台,逼得徐秀英不得不把揭发陈XX放在一边,而为控诉打击报复,维护一个共产党员和共和国公民的合法权利而斗争。从七七年到八二年,她写的告状信底稿摞起来足有尺把高。她那双脚印早盖严了从二轻局到地委的三华里路。她找过地区工办、经委、纪委,找过前后几位地委书记、副书记和专员,也找过中央和省里派到邢台的调查组,上过省城也上过北京。她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她曾经感动得流泪,也曾经伤心地痛哭。她究竟流了多少眼泪,只有那块褐色方巾有数。
在她上访的五年间,上级先后派出了五个调查组。其实案情早已查清,地委领导也曾多次指示二轻局给徐秀英“落实政策”,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为什么?这些领导同志大概忽略了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却被打击报复者看透了“不管谁的指示,最后都得通过本单位的当权者,而这些当权者正是“被告”本身。某局长曾多次叫号:“你告吧!告到哪儿也得回来找当地党委!”某经理气魄更大:“你告到联合国我也不怕!”
多少富有正义感的老同志和普通群众,都以种种曲折的方式同情过她,声援过她,久而久之,也觉得胜利无望了。一位老同志去世之前对她说:“秀英啊,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不是斗争胜利的准备,是失败了回家种地的准备……”
回家种地她不怕,连她的孩子也有这个准备。可悲的是:
按着组织系统,该找的她都找了,该办的都办了,却一事无成。她担心自己没有力量再斗五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