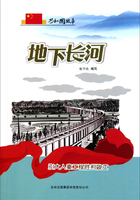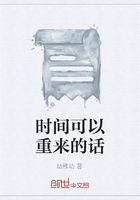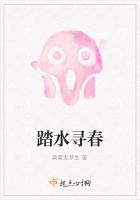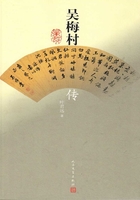区政莳明确规定:机关分房,转业干部不受分房“杠杠”限制;新转业的无房户,要优先照顾。暂时无法分到住房的,各接收单位要采取腾、挤、租、借、让等办法,让转业干部先安顿下来,“先过渡,后定居”。区卫生局从建局以来就没建过宿舍。一九八二年初接收了四名转业干部,局党组专门开会研究,同下属卫生院协商,腾药房,,腾仓库,由局里付租金,解决了两名干部的住房问题:另外每月拿出一百二十元,为另外两名转业干部租招待所。区检察院从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共接收十四名转业干部,其中十二人是无房户。该院宿舍楼建成后,党组专门召开各科室负责人会议,介绍转业干部的住房困难,并在群众中做了大量的说服、解释工作,结果在总共二十套住房中,分给转业干部十二套。区法院也在宿舍楼建成后,给十四名转业干部中的十一户分了新房。
一九八四年转业回来的部队女护士陈文君,带着两个孩子,无房住,娘三个只好分开0游击,在亲戚家东住一天,西住一天,陈文君和她所在医院领导都很着急。眼看一九八五年春节要到了,组织部和义事局下决心要在春节前解决,让她们娘三个过个团圆年。先是汪部长亲自出面,找熟人租私房,没有成功。最后人事局又与房管局协商,买一套住房。房管局的领导了解情况后,也很感到,破例每平米降低一百元卖出一套。按陈文君的条件和入口,本来只应住一间半,但组织上考虑到她丈夫也快转业回来了,索性一次解决,结果出资一万八千元——相当于国家拨下来的九个转业干部的建房费,为她买了两室一厅共约六十平方米住房。春节前夕,人事局的同志亲自把钥匙交到她手上。一家人热泪盈眶。
当然,尽管区委、区政府和下属单位尽了极大的努力,仍然不能保证每一个需要房子的转业干部都能如愿,但是他们能够理解地方政府的困难,并且切实感受了领导上真心实意的关怀和照顾,因此并无怨言。他们以一个革命军人、革命干部所应有的觉悟,以吃苦耐劳和先人后己的精神,同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一起分担着困难,以努力工作、发展生产的实绩为解决困难创造着条件。
徐建民在转业后的头两年,一家四口住在父亲帮他用了日厨房改造的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里,由于阴暗、潮湿,墙上爬满蜗牛,家具也抠烂了。他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励精图治,在车队创造了出色的成绩。
一九八五年转业的环卫局党委书记张观长,住过仓库,住过水泵站的工房。后来局里分房子,他看到许多地方干部住房也很困难,主动提出不要房子。区委知道此事后,对张观长同志所表现的高度觉悟和风格十分赞赏,但他的实际困难,还是要解决,亍是交待局里其他干部,即使他提出不要,组织上也要想方设法解决他的房子问题。
象这样区委主动关心转业干部实际利益的事例,许多转业干部都向笔者介绍过。红钢城街党委书记刘校堂同志说,在他转业后的经历中,有两件事难以忘怀。他是一九八四年转业的,原部队在河北宣化。从部队临出发时,妻子突然患急性喉炎住进医院,接着孩子又发烧住院。刘校堂操劳搬家又加照顾病人,又累又急,也病倒了。此时东西已经启运,人却不能出发,全家人都担心东西丢失,只好写封信寄给青山区红钢城街道办事处。后来他才知道,到红钢城街去工作,当时还只是区里的打算,因为还不知道他是否同意,要实地报到之后才能确定。红钢城街逭办事处的同志接信后,也很替刘校堂同志担忧,于是专门开了一次会,大家说不管这位同志将来是否到这工作,总之是转业到青山区的,既然他把信寄到红钢城,我们就该替他救这个急。于是当场做了分工。组织干事田竞洲和一位会计带卡车到江岸车站去拉东西,赶到时车站巳快下班了,天又下着雨,他们好言好语相求,说明情况,车站的同志得知他们是为素不相识的转业干部拉东西,也延迟下班,给以方便,帮这两位同志从货场上一件一件地认领出来,装上卡车。运到街道办事处,天已黑了,家里早有一批人等候卸车,他们把东西暂时放在仓库里,指派会计负责保管。忙完之后,巳经八点多钟了,人们才备自回家。后来刘校堂报到之后,看见东西一件不少,没磕没碰,比他自己在场料理得还周到,心里感动不已。
刘校堂转业前是副团职,但已代理了两年正团职务。离队前,组织上已经上报了拟调为正团的报告,尚未批复。因此,区委按档案上的副团职,安排他担任街道党委副书记。两个月后,他得到部队提升他为正团的通知和追加的转业费。那时他正负责基层整党,工作很忙,便没向任何人提及此事。不久,区委组织部长找他谈话,说区里巳接到部队关于他调为正团的命令。刘校堂说:“我也接到通知了。”部长问:“过了这么长时间,怎么没见你找我们啊?”老刘说:“找什么,这不是有工作了吗?”部长说:“不。你报到时是按副团安排的。正好你们街的老书记也要退休了。区委已经研究过了,就由你来接替书记工作。”
刘校堂对笔者说:“按说,区里就是不改也完全有道理,何况我本人又没提出过。但区里总是想得很周到。这些事,使我们觉得区委真象我们的娘家,有事愿意找他们谈。俞些时候,区里举办转业干部培训班,十几个新转业的同志凑到一起,都对区里的安排很满意,表示好好干,为青山建设献出全部力量。一九八五年转业的副团职干部陈建凡同志,老家在市里比较繁华的轿口区,他本来想到青山区来试一试,如果不顺心,就调回生活条件更优越的市内去。来了以后,组织上对他很信任、很关心,他不想走了,决心在青山干到老。”在青山区采访,我觉得时时处在一和动人的感情漩流的冲击之中。这是一种令人乐观、向上的“良性循环”:区委书记说,他们之所以乐于接收军队转业干部,说到底是因为他们干得好;而绝大多数转业干部的思想轨迹证明,他们之所以干得好;与区委和区政府的关怀、信任、支持和培养有极大的关系……这种组织与个人、上级与下级、地方政府与军转干部之间互相信赖、依靠和鼓励的循环,如同航空物理中的“上升螺旋”,它一旦建立,必将越旋越快,越转越高。随着它的扩展和上升,青山区的党政建设和各项事业势必蒸蒸日上。青山区将更加青翠可爱,更加生机勃勃,永远保持青春的活力。
“第二战场”
寻找那顆星
如果把我在武汉市青山区的所见所闻报告出去,人们是否相信?青山区的转业军人们由军事型迅速转变为经济型人才,有什么必然因素?除了区委和区政府的合理安排、培养之外,他们从军人出身中带来了什么优势?在青山区成为普遍性的现象,在全国有没有共性?
不错,在全国军转安置工作和转业军人“双先会”的典型中,有一大批纯粹由“军事型”转变为“经济型”的干部,做出了了不起的成绩。但我不知道,是他们的个人素质起了决定作用呢,还是有什么共同规律?要知道,在人口众多的国家,任何一种“典型”都能找出“一大批”。我带着重重疑虑继续寻觅。
一天,总政干部部负责军转工作的冯少武处长告诉我:云南有个叫李世俊的转业连长,写了一本书,叫《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受到国内外企业界的重视……
我眼前仿佛划过一道闪电,将重重疑云撕开裂缝……我预感到那书里将有某种必然性被揭示,我的那些问号将获得解答。我急于找到那颗星。
奇怪,在“双先会”的几十份材料里,居然没有他。我寻踪访迹到云南,向省军区的军转工作部门打听,他们说:他是云兴公司的总经理,归口昆明市。市里压根儿就没把他的材料报到省里来,据说是因为一桩未了结的经济案即便如此,我也要找到他!
一天傍晚,我在西瓜摊前偶然发现一张褪了色的云兴公司招工广告。扫兴,一张“祖传秘方,专治阳萎”的白纸覆盖了广告大部分内容,只在底边露出一行字:报名地点,穿金路粮店附近省纺织局院内……
我在穿金路打听了不下二十人,终于看到了那栋租用的陋室。
我怀疑倦是专攻“军转理论”的学者
李世俊一九六二年入伍,现年四十三岁。一九七九年从对越自卫还击战场下来时是某师通信营架线连连长。
身高一米八〇,略显削瘦。阔额长脸,棱角分明。嗓音洪亮,想必在大操场上面对几百人讲话不用麦克风。他那不紧不漫的“云南普通话”里洋溢着自信,时而仰脸大笑,感染力很强。
总经理头天下午刚从深圳飞回昆明,当晚,与一位外商有生意谈判。而今天上午,他同我一见面便说:
“我转业七年来,第一条体会就是:转业干部要充满自信。”他居然象专门研究了我和我的任务似的,一开口就切中主题。
“不少军队干部下来时都遇到一个尖锐的矛盾:进入新的领域,一切都是陌生的,别人的眼光也带有偏见,不信任,不欢迎。事实确是如此,但这只是个短暂的过程,一般只有半年左右。半年、一年以后,就会有相当一批转业干部受到重视。这时,他们的自信心开始恢复了。——这是普遍现象。
“那么军队转业干部树立自信心的条件是什么呢?最有利的条件就是管理方面。管理,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结合在一起时,为了完成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单独完成的工作所开展的活动。它存在于人类一切共同活动中,对一切行业都是通用的。不论是部队还是地方,你担任领导,你就是在搞管理。而管理的核心是管人。在这方面军队干部的素质往往更强,甚至可以说是军队干部的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