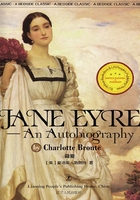五、
裴春丽将醒未醒的时候感到脖子好象落枕了,轻易动弹不得,头也疼得厉害,尤其胸部被压迫着喘不过气来。
她一夜都在做梦,梦的还是在地质队的日子,她还是那里的一个新分配去的毕业生。她梦见月经来了,梦见她到刘队长的帐篷里请假,可是刘队长偏偏派她上山,还说上山是最轻的活儿,要不也可以跟车去拉设备。她有些委屈,刚要哭,她的上一届学长小崔进来了,小崔穿着工作服准备出发的样子,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刘队长,什么也没说又走了。这好象还是在俩人没好以前,她刚分到地质队的时候。她就想,算了,谁让你干的就是这行哪。她又想,离开这里的唯一方法就是考研。她边想边跟着小崔向外走,却无论如何走不出去,帐篷的门帘紧紧地裹住了她。小崔!小崔!回来帮帮我!
突然,她感到有一只手在她的胸口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还有一只胳臂箍着她的脖子。裴春丽猛地醒过来,她立刻知道自己是跟谁在一起了——是那个叫王大力的人!
她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身上,是穿着衣服的,她松了口气;又紧张地拉开被子看王大力,他也是穿着衣服的。这时,王大力突然咧开嘴笑了,眼睛却没有睁开,他声音嘶哑地说,你是不是想偷看我的裸体?
谁偷看了?讨厌……
裴春丽试图摆脱他的胳膊和手,他死死地箍着,笑道,你还没有谢谢我……
她问,谢你什么?
谢谢我对你的爱护,让你有尊严地醒来,而不是一片狼籍,浑身青紫……
她打断他,生怕他说出什么不堪的词来。马上说,好好好,谢谢你。
怎么谢?王大力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
裴春丽一听就急了,说,我就知道你得问这句话,你说怎么谢!
亲亲我!
我就知道你得说这句话,就不!
为什么?你得说为什么不……
因为你一嘴臭气。
好,王大力一跃而起,说,好,我去刷牙!
裴春丽起身拥被而坐,努力回想昨晚的过程。一起喝酒还记得,后来怎么就到了这里,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王大力洗漱回来,身上带着薄荷的清香,凑近她,噘起嘴,说,来!
裴春丽望着眼前的这个大男孩一样的男人,互相认识以来,他一点不掩饰他的迷恋,却在她毫不省事的境况下保持了君子风度,他的确是个不错的男人。于是她轻轻地吻了他。
王大力的回吻就不是轻轻的了。他重新搂住她,把她压回被子里。他的手带着些许清凉,带着些许颤抖,试探地摸索着解开她,然后把自己火一样燃烧着的身体贴住了她。
不行!
为什么?王大力两手撑起身体,居高临下地吃惊地问她。
该上班了。
王大力一听就笑了。你呀你,欲擒故纵是不是?
什么呀,你用错词了。
那就是半推半就,欲——就故推!王大力看她还是不说话,就泄了气,翻过身与她并排躺下,问道,你怕什么?
你说呢?
我说?王大力想了想,问道,是不是真的要上班?
有点吧。
还是身体不舒服?
有点吧。
王大力心里明白她的障碍在哪里,但他就是不能说出来,不能加强她的这种心理负担。不就是一女不嫁二夫吗?问题是,你并没有嫁呀。不过,女人忠实是个好品质。男人得保护女人的一切好品质。
于是他说,那好吧,我不会强迫你。我要的是两情相悦。如果你并不喜欢我,我只能很遗憾。昨天晚上,是你让我把你带回来的,我知道你心里不快活,我想让你高高兴兴的,每天都高兴。可惜咱们同床共枕一场,却不能共享快乐……好吧,起床,我送你上班。
他一跃而起,背着身扣衣扣,穿鞋。然后他回过身,看她用被子蒙住了头,就笑了,问道,怎么了,哭了?又舍不得我了?
这时只听一声禁不住的啜泣真的传了出来。
嘿,怎么了?!王大力扑过去,掀开裴春丽的被子,只见她梨花带雨,正哭得欢。他伏在她面前,问道,嘿嘿嘿,怎么了?告诉我……
这时,裴春丽伸出手臂揽住他的脖子。王大力没防备,一头栽在她的脸旁。女人特有的体香,湿润的肌肤,他当然明白,她接受了他。
裴春丽只在一瞬间想了想小崔,就立刻被王大力带回了现实中。他在她身边,他需要她的呼应,她的目光。她不可能象与小崔时那样被动地接受,闭着眼睛掩饰自己的渴望。王大力要的是交流!要的是她的配合,还有她的热情。她被他带动着从天上到地下,从南极到北极,带着她来回穿越经纬,反复跨过赤道,两人最终停在一处火山口,险些被熔化。
象把电玩打到最后胜利,王大力大大地吐出一口气来,与裴春丽相视而笑,说,真好!你呢?
裴春丽微微一笑闭上了眼睛。
两人再度醒来已是中午。阳光照在眼睛上,一片橙红色的雾。大力的一双手温柔地滑过小裴的脸,她的眼睛、鼻子、耳朵……
小裴笑了,懒懒地说,行了,知道了,该起了。
离开的时候,王大力问,什么时候再见?
小裴说,再说吧。
大力问,什么意思?
小裴笑说,下次开会的那天吧。
大力叫道,什么?!中间还有五天哪!就不见了?!
小裴说,中间正是我“倒霉”的日子……
大力就笑了,委屈地说,“倒霉”也可以见面呀,……我又不是野驴,见了面就得干那事。可见我在你眼里是什么形象了。
小裴一边笑一边解释道,不是不是,是我的原因。你不知道,我一“倒霉”就特别惨,疼得不行,连床都下不了……单位的人都知道。
那我去看你。
不,不行。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住的是单位的集体宿舍。
集体宿舍也不是不能见面……
小裴突然大叫道,你怎么连这个也不懂?!这么不体谅人!
王大力着实吃了一惊。他呆呆地望着她,似乎仍然不明白她为什么发火。
小裴见他的样子,象被吓着了,就缓和下来,说,我知道你是自由惯了的人,可我不是。我是个单位人,时时处处都在单位同事的眼皮底下。我需要平静的生活。单位同事都知道我有男朋友,是地质队的。如果突然冒出来一个你,他们会怎么说?
王大力说,这并不是说,你就没有重新选择的权利了。
小裴叹了一口气,说,几乎没有了。
什么?!王大力绝望地叫起来。
裴春丽是家里的大女儿,她下边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是个老地质,年轻的时候在外面转战南北,年纪大了就带着一身病回了家,到一所地质中专学校教书。父亲一生的信条是,量力而行。所以裴春丽高中毕业只考地质中专,毕了业就下地质队,挣钱贴补家用。等弟弟妹妹高中毕业,她才一举考进了地质大学的研究生院。
就是在地质队的四年里,她落下了痛经的病根,每到一个月的这个时间,她就只能蜷缩在床上,强忍疼痛,浑身大汗,面色惨白。假如当时有一些老同志的家属在,她们会把红糖、生姜熬成汤给她送来;假如没有,她就只好蹲在火炉边自己熬。男友小崔就是裴春丽那时候交下的。他会在出发前给她熬好红糖水,会在下班后陪着她熬过疼痛。他比裴春丽早一年进队,却已经是队里的技术骨干。他业务精通,为人厚道,积极肯干,工作和生活中对裴春丽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有一次小崔陪着裴春丽去附近一个县医院看病拿药,妇产科的大夫毫不留情地告诉他们,裴春丽的痛经过于严重,不排除子宫内膜有器质性的问题,比如畸形,也不排除将来影响生育的可能。就是在那次以后,小崔带着裴春丽去了他的家,见了他的父母,定下了他们的关系。因此,裴春丽对小崔从一开始就怀着感激之情,报答之情,以身相许之情。
在这样的感情之中,她没有理由去想别的。虽然小崔不是你选择的,是你在当时当地的情境中不得不依赖的,而且队里只有他们两个未婚的年轻人,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选,而恰恰他又对你十分的好,但是,在野外艰苦的环境中,这就象寒冬里的炭火,你只有围着它转,你才能有温暖。
而王大力是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你的生活的。他与你毫不相干,既非你的上司,又非你的同事;既不碍于家里的面子,又不碍于群众舆论;他是他自己的主宰,你是你自己的奴隶;他看上的是你这个人,没有背景资料作参考,没有各种利益作选择,除了喜爱,其余没有干系。总之,她与王大力是一种两情相悦、简单快乐、不计得失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能够发展为爱情,是否能够长久,是否能够深刻地扎下根来,她没有把握。
想到此,裴春丽仍然认为小崔还是她的男朋友,他还是她准备与之共度一生的人。而王大力不是。王大力只是一个伙伴,朋友,没有任何誓约的、眼前的、偶然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与其他人稍微不同的是,在他和她的关系中,似乎不存在障碍,从心理到身体,没有抵制没有界限甚至没有羞耻。怎么回事?她不明白。究竟是自己的毛病?还是人世间确有这么一种东西在?
下午上班前,王大力把小裴送回了单位。依着小裴的意愿,他把车远远地停在大街边,由着小裴自己走进胡同口。他在车里望着她婷婷袅袅的背影。这个外表瘦弱、内心强硬的女人,竟然强烈地吸引了他。嘴唇上留着她嘴唇的气息,脸颊上带着她亲昵的摩擦,手掌上仍然握着她细嫩的肌肤,耳旁是她的轻言浅笑,呆坐在驾驶座上,身体仍在一次次地亲热……不不不,小裴,你正是我要的女人。我发誓,我要和你在一起,永远,今生今世。
很多摄影爱好者对于日出日落的丰富色彩和壮丽景色十分向往,他们往往辛苦等待很多天,才能凭运气抓住宝贵的几秒钟拍摄下最美丽的画面。如果他们到北极来,捕捉日出日落的美景该是多么容易。因为在这里,每个黎明或者黄昏都能持续一两个月,这么长的时间足够摄影家们细细地把握时机拍出最美好的照片来。
六、
与林光明结婚之前,于小羽还有过一次短暂婚姻。那是在她高中毕业到部队医院当了小兵以后。而那时,她的初恋男友、哥哥于大勇的同学林光明却在海南因为涉嫌汽车走私而被捕,进了监狱。据说数额巨大。彼时彼刻,一方面是,她的身边自然少不了青年军官们的狂轰滥炸,穷追猛打;另一方面,林光明那边却是音讯全无,而她又不知道他究竟还能不能出来,何时出来。少女爱情面对着一次次的婚姻憧憬,是忠于往日情侣,还是抓住身边不可多得的机会?
最终,于小羽两年后复员,嫁给了一个青年军官。她虽迷恋林光明的痴情,但她更欣赏成功的男人。
当林光明两年后从监狱出来时,于小羽已是他人之妇,结婚刚刚半年。而且她还死心塌地地在部队驻地的县政府当了总机的话务员。林光明一听到这个消息,气得连发火的劲都没有了。他去总机室找她,寻求重修旧好的可能,可是于小羽却为平息他的怒火,而给他介绍了一个原来军医院中的好友邱英英做女友。虽然小邱是个很可爱的女孩,但是林光明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她作为于小羽的替代品。
当他们两个历尽艰辛千方百计重新走到一起的时候,无论他们自己,还是他们周围的亲人,包括于小羽的新婚丈夫,包括邱英英,都已是伤痕累累。这一段曲曲折折的故事后来就被同是军中好友的一位女作家写进了小说。
惹了一大堆麻烦事后,于小羽不得不选择离开。由于走得不清不楚,离开后的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于小羽跟着林光明回到从小在此长大的城市,为了生存,她当过招待所服务员、公园售票员、美容院按摩师。他们两人在林光明母亲单位的一所筒子楼里实践着他们的爱情生活。这期间,他们生了儿子林思羽,日子过得杂乱无章。后来林光明终于东山再起,两人才彻底摆脱了那种困窘的境地。
按说这么一种曲曲折折历尽艰辛获得的婚姻应该是经得起考验的。
在王大力家闭门锁居的两天两夜,于小羽感到突然有了很多时间能够认真地想想自己的过去。告别了过去以后,将来呢?将来怎么办?
刚刚早上六点,她拿起电话。查尔斯还没起床。他接电话的声音迷茫而性感。
Hello……
这使她油然想起与他激情迸发的那一刻。他细致周到并且内行。
于小羽突然想哭。查尔斯生活在他的那个世界里,怎么可能理解一个中国女人的处境呢?可是,假如为了让他理解,让他早早地介入,也许只会把他吓跑。再说,他这个人真的就能让你托付终身吗?当初离开部队而嫁林光明,想的也是要托付终身。什么是终身?几年能算终身?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而一个中国女人四十多年的历史对于查尔斯来说是不是太长了?是不是也太复杂了?
她轻轻地放下电话。让他继续睡吧,他不一定懂。查尔斯是九十年代中期进入中国的外商。他做医疗设备,B超、CT、心肺复苏机、烧伤植皮机、甚至小型X光机等等。她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到处“找关系”。因为当时的正常渠道常常是堵塞不通的,他才知道“关系”在中国的重要。他去找了他的朋友约瑟夫的中国太太邱英英,请她给他介绍认识一些有权有势的人。
在若干家外企联合举行的一个新年聚会上,于小羽认识了查尔斯。她是应邱英英的邀请出席的。她与邱英英和邱英英的丈夫约瑟夫坐在一个桌。当舞曲响起时,邱英英先客气地让约瑟夫请于小羽跳,却被于小羽婉拒了,她以为这是礼貌,以为每个丈夫的第一支舞应该与妻子跳。所以,当第二支舞曲起来之时,邱英英的丈夫约瑟夫马上起身请走了邻桌查尔斯的中国女友,查尔斯反过来请走了邱英英,剩下于小羽独自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