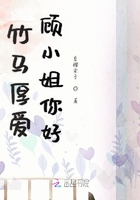丈夫也想让她来,只是不好意思说,现在她自己提出来,丈夫自然很高兴,说到工作调动问题,他大包大揽地说,工作好找得很,包在我身上。
庄玉菊走的时候,丈夫把已经到了上学年龄的女儿留了下来,庄玉菊带着小儿子踏上了归途。
庄玉菊回到山东又待了一年,她提出要调到新疆去,厂里不让走。舂天,丈夫的一个战友探家,说老吕病了,女儿也病了。她再也呆不住了,又请了假,带着儿子上了西去的列车。
这一来,她再也没有走。通过信件交涉,单位寄来了X作调动关系,可直到如今,整整十年,也没有联系上一个接收单位。
她问丈夫,你不是说工作好找得很吗?
丈夫说,谁能想到这么难,话又说回来,当初就应该想到的,你看这地方,出了门,不是山就是戈壁滩,哪有单位可找的。
她说,我二十一年的工龄就这样白白丢了。
丈夫说,丢就丢吧,又不是你一个。
丈夫说的虽然轻巧,不中听,却也是实话。丈夫把她安顿下,又上了阿里。
虽然到了丈夫身边,但他们离得还是那样远,一年多两年丈夫才下山一次,随军的十年中,庄II菊和她的丈夫相聚的日子加在一起还不到一年。
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一个瘦小的女人默默地支撑着一个简陋的家。
1995年,庄玉菊的娘家妈摔坏了腿,来了信,她悄悄压下了,没跟山上的老吕说。不久,老家来信又说老吕的父亲又病了,她想这可不能不跟丈夫说,可找不到上山的车,又不通电话,没法把信捎上去。庄玉菊正着急着,娘家又连着来:上两封电报,说母亲病危一息尚存,希望临终再见女儿一面。和丈夫联系不上,庄玉菊急得心如火焚,有人出主意,让她直接给阿里军分区司令员打电话,请司令员转告丈夫一声家里的情况。她硬着头皮给司令员打了个电话,司令员很客气,说立即转告。过了两天,丈夫通过阿里军分区后勤部的张部长传来了话,说让庄玉菊把孩子留下,托个邻居,自己回,他说他工作忙,脱不开身。丈夫的回答庄玉菊能料想得到,她又托人转话给丈夫,说她打算把大的留下,带小的走,小的托给別人不放心。就这样电话传过来传过去,过去了二十多天。
一天,她买汽车票回来,一进屋女儿就对她说俺爸下山了。”她一愣,屋子里外打量一番,对女儿说广你脑子出毛病了。”“真的。”
“人呢。”
“我听人说的。”“听准了是你爸?”
“是我爸。”
庄玉菊还是不敢相信。
天擦黑时,庄玉菊到楼下的一个瓜摊上买西瓜,远远地看见来了一个人,满脸满头满身都是土,弓着腰,往这边走。她没看出是自己的丈夫,继续挑瓜。那人走过来,在她肩上拍了一下,说:“你看谁来了?”她一看,果然是他。
他是搭便车下来的。
她问他你不是说回不来吗?”
他说广你让司令员转电话,司令员把我撵下了山,他命令我和你一起回老家。’
庄玉菊和丈夫回到山东老家时,娘家妈已经去世了。
丈夫懊悔地说我要是在山丄不耽搁就好了。”
庄玉菊说你没有错,我知道你离不开阿里。”
丈夫没有说话。
离不开阿里的丈夫最终还是离开了他朝夕相处了二十年的风雪高原。2000年1月,部队确定老吕转业,虽然这个结局早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但接到转业命令的那一天晚上,老吕还是彻夜不眠。
看着丈夫难受的样子,庄玉菊说要不跟领导说说,不走了。”丈夫说没听说4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庄玉菊说:“你立过功,授过昆仑卫士称号。”
丈夫说:“这就能不走?”
庄玉菊说:“咱不指望进步了还不成?”
丈夫说部队又不是养老院庄玉菊不说话了。
忘原边防军人的女人们大都循着这样一个人生轨迹:先舍弃了一切来和她们当军人的丈夫团聚——规范的说法叫随军;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等待她们的丈夫从山上下来,短暂的相聚是她们无尽守望中的盛筵;十年二十年过去,最后她们又随着转业的丈夫回到她们原来的地方,她们的丈夫转业大都是在营团职的位置上。而此时,她们已经不再年轻。
这些女人在选择了边防军人的同时,也选择了这种人生之路。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们的女儿高中毕业了,髙考时她报了乌鲁木齐附近的一所军医学校,不过她被录取的希望不大,庄玉菊说老吕常年在山上,她没有管好女儿的学习,她说她对不起老吕。九月初,别的考生的录取通知书都已经到了,她的女儿还在等待着。
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那等待越发显得空洞。庄玉菊催丈夫到军区的有关部门去打听打听,她对丈夫说,咱兵也当到头了,从來没求过人,你就i找人打听打听吧。丈夫说,打听什么,你该不是让我去活动吧,我哪会,连找谁都不知道。想想,丈夫说的也对,庄玉菊虽然为女儿的事着急,也不再难为他。
就在这时,老吕转业安置单位的通知却到了,说他的工作已经联系好了,在老家县城的反贪局当副局长。
庄玉菊对丈夫说:“把你用到地方了。”
冬天到来的时候,庄玉菊一家四口离开了“女人村",她的女儿没有能上军校。汽车开出院子的时候,这个倔强的女人已经泪流满面。
她的身后,是她整整生活了10年的“女人村”,是那条熟悉的路,那路通向喀喇昆仑山通向阿里高原,此时,她觉得自己对这甩的一切竟是那么依恋…
庄玉菊走了,她的那些姐妹还在“女人村”里默默地守望着喀喇昆仑山,守望着阿里高原。
张树文是个十分内向的女人,三十多岁,她的眼睛里总是含着一点淡淡的忧戚。
她的丈夫叫濁展来,1980年人伍,一当兵就在昆仑山下,后来上了蚌埠汽车管理学院,毕业后回到南疆当汽车连长,1986年上了阿里,现在是阿里军分区后勤部的副部长。
张树文和蔺展来都是秦皇岛人,张树文在秦皇岛的一所学校里当老师,她经人介绍,认识了在新疆当兵的蔺展来。第一次见面,蔺展来就用军人的直率对她说你可得想好,跟当兵的是很苫的。”
张树文点点头广我知道
“在新疆当兵更苦。”
“没啥,北京有趟火车直达乌鲁木齐。”
“到乌鲁木齐也才走了一半路。”
张树文愣怔一下,又点了一下头我不怕。”
蔺展来说你得想想你的将来“想啥?”
“结了婚,要么两地分居,让你守空房,要么你得随军到新疆,跟我一起去吃苦。你只有这两样选择。”
“我知道。”
张树文平淡地说,她的承诺语不惊人。
书信往来了三四年,却因为蔺展来工作太忙,他们的婚期一拖再拖,张树文已经拖到了二十八岁。对于一个姑娘来说,二十八岁是个敏感的年龄,于是,周围渐渐有了闲话,父亲母亲也一遍遍地催。87年夏天,她独自一人从秦皇岛来到了喀喇昆仑山下。
在叶城,蔺展来见到了她,他问她干啥来了。她说来结婚。他说怎么结什么准备也没有。她说有人就行要什么准备。
他们就在叶城结了婚。
他们的婚礼很简单,却来了许多人,昆仑山不缺乏热情。
“还走不走?”新婚之夜,客人散尽,蔺展来问她。
她摇摇头我要让你下山的时候,有个温馨的家。”
从那以后,她就没有再离开过南疆这片土地。
她像许多随军军嫂一样,失去了心爱的工作,几年之后,她才在留守处的幼儿园里当了一名幼教老师,这是在军分区菹围内,惟一能安排的工作岗位。
蜜月还没过完,丈夫就带领车队上了阿里。
在家属基地,丈夫上山是件大事,军嫂们都要提大包拿小包,把丈夫送t车,目送着车走远了,才恋恋不舍地冋到家里。之后的一两个星期里,她们魂不守舍,什么也干不下去,只有得到她们的丈夫来了报告平安的消息,那一颗悬着的心才能放下去。
张树文的丈夫t山那天,她为他做了精心的准备,煮了茶鸡蛋,买了咸鸭蛋,包好了洗得于下净净的衣服。她送他走出屋门之后,她对他说:
“你走吧,我不送你上车了。
丈夫笑着问为啥?”
她说我怕……”
“怕什么?”
“……不知道。”
“你放心,什么事也没有:
“我知道。”
丈夫出门后,她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了下来。她一连哭了儿天。她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勇气去把丈夫送到车上,再目送着他走远,是怕丈大看到自己的眼泪吗?是怕别人看到自己难割难舍的新婚别离吗?还是……她不知道,她说不清楚。她说丈夫一出门,她的眼前就闪动着那条飘在云中的风雪之路,她说那路把她的心带走了。她听过关于那条路上的太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