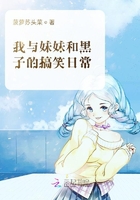月玲对着镜子照了照,觉得起床时穿的这身蓝色衣服不够好,不冷,就又从高低柜中翻出了一套红色西服来,这身衣服穿到身上,无疑显得热烈一点。应该……月玲想,应该改变那种冷酷氛围啊!
离九点钟还有半个小时,月玲又想了一件事情:她这么慌慌张张不说明她自作多情吗?有这种必要吧吗?已经是分道场镳的人了,还来这一套干什么?再说,乙坤心中还有她吗?人家是快要做爸爸的人了!
八点半,乙坤却踏进了月玲的家门。
月玲的娘,昨晚上神庙替人伐神,直到现在还没回来;月玲的爹,一个早就去替邻家人帮忙盖房子。屋子里就剩下月玲一个人。
他们本来可以坐下来谈几句话,月玲昨晚睡在床上编织了许多话,她完全可以趁这个大好时机给乙坤谈一谈。可不知为什么,见到乙坤后嘴里没辞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月玲就锁了前门,帮乙坤提了一个小包,两人默默地走出巷口,踏上村边的石子大路。
清河镇今日逢集,他俩很快地汇入在赶集的人流中。
清河镇是玉山县数一数二的大镇,“三、六、九”逢集,每月九会,天阴下雨,雷打不动。适逢春天农闲季节,庄稼活儿安排得窝窝逸逸,人们没事干,只好逛会了。四周八向的人流都沿着各自的大路小路朝清河镇涌来。任家村是清河东岸大小十几个村庄和山民们赶集的必经之路,这条大路上的行人更多。拉车的,挑担的,蹬着自行车的,乘着“蹦蹦”车的,徒手的,负荷的,把个大路上塞得满满荡荡。当然,这其中不泛有许多熟人,包括老二认识的,月玲认识的。他们和熟人频频打着招呼。
月玲不怕众人瞅她,她需要的就是众人的眼光。
知道他俩离婚的人,见他们又走在一起,就投来怪异的一瞥。有些人甚至在走过他俩之后,还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好,月玲就希望得到这种效果!
过了小溪,乙坤迈开了大步,想尽快赶到镇上,立即坐上去县城的班车。月玲却从后边拉了一下他的衣服后摆,说:“走那么快干啥?”
“我,我想赶快回到牛肉店,”乙坤瞅着月玲的面庞说,“离开牛肉店已经五六天了李娜一个人在那里经营,我实在不放心……”
月玲向前赶了两步,靠近乙坤的身边,说:“老二,我……我想给你说个话。昨天晚上,我一夜没合眼,想了许多事情……”
乙坤瞅着月玲眼中那种希冀的光芒,心中不觉惶恐起来。他真害怕月玲说出让他难堪的话来。他记昨,月玲和他一块上高中那阵,两人在一个礼拜天归校的路上,月玲的眼中就曾经流露出这种光芒。后来,她果然向他求婚……如今,这种光芒又出现了,他真害怕她再一次重复那个古老的话题。
他有意和她拉开一段距离。
她有意靠近她。
忽然,潘满年老汉埋着头急匆匆地从镇子上走过来,他们打了个对面。
乙坤不觉脸一红,忙问:“姨夫,赶集的人正朝镇子上走动,你怎么从镇子上返回来?”
听见有人问话,满年抬起头来,用袖子擦着额头上沁出来的汗珠,说:“我刚到集上,却听人说你们家跟西京家打了架,还听人说你哥被人家打……打伤了……我一时心慌,就想过来看看。”
“姨夫,你甭熬煎!”乙坤站住了,说,“我哥头上缝了两针,又打了几天消炎针,已经不当紧了。”
“不会……不会发生危险吧?”老大甲坤的岳父潘满年,最怕的是女婿有个三长两短,“我光害怕他得了破伤风……”
“药还没断。吃的,注射的都有。不会发生问题,你老人有就放心吧。”乙坤说。
潘满年老汉无限失落似地顿着脚,囔囔地说:“咳,我简直跟个死人一样,整天钻在家里,四门不出,却怎么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乙坤说:“姨夫,你老人家要是不放心,就去看看吧。”
“咳,我说乙坤啊……”潘满年老汉不无报怨地指责:“你们这一帮青年人啊,太张狂了!太没情况了!你……你以为你们弟兄三个精壮壮小伙子,劳力美,吃不了亏,就在村子是村子跟人打架,是不是?你跟老三灵性,有心计,腿底下灵活,你们两个都没吃亏……咳,就是甲坤太笨,太蠢,吃亏的也是他……再说,他还有三头奶牛哩,他受了伤,这奶牛……谁来经管……”
几句唠叨话,说得乙坤心里冷冰冰的,愣在大路上,月玲见他们两人说话,就向前走了几步,站在路边等着他们。这会儿,见乙坤不再说话,就喊乙坤赶快离开。
乙坤正要转身走去,潘满年老汉又拉住了他。说:“哎,哎,乙坤,听姨夫给你说……早晨派出所把我叫去了,那个当官的说,县上来了电话,在山东省什么地方……我也记不下名字,反下,在那么把幺女找到了,让咱们赶快领人哩……”
乙坤心里一惊,就朝月玲喊:“快来,月玲,这儿有个事……”
月玲又折回身,向乙坤他们身边走来。
潘满年老汉神秘地拉着他俩朝一条小路上走来,一直走到一棵绽开了鹅黄色绿芽的柿子树底下,这儿有几块并排儿放着的大石头,他们就分别坐下来。老汉瞅了瞅周围没人,就压低声音说:“那个当官的给我说,咱娃……是被一个贩卖丝光袜子的女人……骗走的……”
老汉由于心情太激动,结结巴巴地总是说不清楚。经过了一顿饭的时辰,总算说完了。乙坤和月玲也算听出了个眉目。原来,同时被骗的还有陕北一个女子。那女骗子骗她们说,去河南贩一次袜子只需三天功夫,就能赚回二百多元。两个正在食堂打工的女子就向老板请了假,说是她们回家看看,跟着人家去了。从西安一上火车,身后边就多了一个彪形大汉,满脸楂楂胡子,黑封着脸,整天不说话,只是守在他们身边。从那彪形大汉与贩袜子女人说话的举动来看,两个女子知道,他们是熟人。于是,心中就产生了疑团,她俩问那女人:“这男的是……”那贩袜子女人很干脆地说:“保镖!去河南贩袜子,身上要带上万元,不跟个保镖哪能行?三个女人敢出外做生意?而且还有两个年轻女子,没有个人保护咋行?”
……原说在郑州下车,可是,火车已把河南走完了,他们还没有下车。两个女子更加怀疑了,就要求下车。贩袜子女人说,再有两站就到了。两站后,果然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小站下了火车。贩袜子女人把他们领出车站,来到一条小巷,钻进一家低矮的石棉瓦房内,让那彪形大汉和陕北女子坐在那里等着她们,那女子又领着幺女向车站以北的一个小村子走来。幺女疑惑地问:“不是要到织袜厂购袜子吗,怎么向小村子里走?”那女人说:“这里都是一家一户的小作坊,家家都有织袜子的机器……”
……进了村,拐过两个小巷,贩袜子女人领着幺女走进了一家人的门楼,一位老太太和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小伙子迎了出来,像熟人一样,招呼她们进屋子坐下,并递上了茶水。然后,那贩袜子女人向那小伙子说:“你领我去车间看看货吧!”说完,就随着那小伙子一道出去了。
那女人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幺女就被留在这个家了,过了一个多小时,那小伙子回来告诉幺女,说:“……她不会回来了。我给她出了五千元人民币,把你买下了,买下你给我做媳妇……”
就这样,幺女被贩袜子的女人骗到了山东,一去就是一年多!
潘满年擦着眼泪说:“……听说,幺女肚子都大了,有啥了(怀孕),咳……公安局让咱去一个人,他们陪着咱一块儿到山东领人……”
乙坤和月玲都愣住了,两人互相看看,都没了话说。
老汉又结结巴巴地说:“我上了年纪,又是个睁眼瞎子,大字不识一个……这出远门的事……咳,咳!你哥……这下被人打伤了……谁去接呢?他……”
乙坤确实为难了。
“我看,”潘满年老汉又擦了把眼泪,望着乙坤说:“我看还是你去一趟吧!呃?”
这阵儿,乙坤根本就没有听见潘满年老汉的话,他脑子里想的是另一个被人从新疆骗到陕西来的苦命女子……他眼里同样溢出了泪花!
月玲很同情幺女的不幸遭遇,她以为幺女的出走,与她有关,是她逼出来的。老三丙坤那阵儿想把幺女也叫到牛肉店,一块儿干活,她依家庭主宰的身分拒绝了……为了两个钱,她不得不去西安替人打工,西安是个大地方,幺女这个清河川的老实姑娘没有见过大世面,经不住金钱的诱惑,焉能不被人骗走?咳!当初都是她错了!
月玲瞅了瞅乙坤,就把胸膛一拍,一本正经地说:“乙坤,姨夫人老了,也确实不能出远门。你如果太忙,牛肉店脱不开身,山东领人的事就让我去吧。反正,我在家里又没事儿,走了就走了,谁也管不上我。”
“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能出远门?”乙坤摇摇头。
“怕啥?公安局的人跟在后边,还怕谁抢去不成?”月玲把一只花手帕递到乙坤手里,要他擦擦眼泪。端详了他一会儿,又调笑似地道:“……你如今是有了媳妇的人,还能操心我的安危吗?”
潘满年望着月玲那坚定的面容,十分感激。但他也觉得让一个年轻女子走出东,太不放心,于是,也摇了摇头。
乙坤擦完眼泪,望了月玲一眼,把花手帕装进自己的裤兜里,没有还给月玲。他转过头来,向正在垂头丧气的满年老头说:“姨夫,你先到我家去吧,和我大哥坐一下,把幺女的消息向他和我大嫂子说一声,让他们也放下心来。他们都操心了一年多,心里够难受的。这儿,我和月玲再到清河镇派出所去一趟,把实际情况详细地了解一下,然后与县公安局联系联系,看看究竟怎样去山东。”
潘满年老汉“咳嘘”了一声,就抓着膝盖站起来,向大路上走去。
乙坤和月玲没有动,仍然坐在那里。
看着潘满年老汉的影子走上大路,消失在赶集的人流中,月玲“忽”地一下扑进乙坤的怀里,嘤嘤地哭了。
乙坤很害怕。他没有丝毫的精神准备,被月玲的突然行动一下弄懵了,就一边推开她,一边惊愕地说:“你……你怎么……”
月玲紧紧地搂着他,并把头塞进乙坤的怀里,不愿取出来。
她没有话说,她一句话也说不出,就是这样嘤嘤地哭着,好像要把一年多来的苦愁在这一瞬间哭完,哭个痛快!
乙坤扳起月玲的脸来,见她那搽了胭脂的脸上流出了一道一道的泪痕,心一下子软了。于是,就俯下身在她的脸上,嘴上,轻轻地吻了两口……
月玲满足地合上了眼睛。
大路上又走来了一对年轻男女,乙坤松开了月玲,并提醒她说:“那边来人了……咱俩还是到派出所去一趟吧!”
月玲从乙坤怀里抽出了头颅,直了身子,拢了拢蓬乱的头发,拉着乙坤的手说:“走吧……”
两人刚刚踏上大路,却见荷塘村的吴媒人,从清河河堤的大路上过来了。他背抄着手,身子一左一右轻轻地摇晃着,一副十分悠闲的样子。手中攥一条龙须草绳,草绳的头儿长长地拖在地上。眼睛眯着,只留小小一条缝儿瞅着路径……
乙坤用胳膊肘扛了一下月玲,下巴颏朝吴媒人一指,两人都感到好奇,就站住了。
等吴媒人悠悠地走上清河大桥的时候,乙坤喊住了他:“哎,白话步!你赶集去呀?”
吴媒人蓦地睁大了眼睛,见是槐树庄老二和他已经离了婚的媳妇月玲,就精神振作起来,说:“噢,是呀,是呀,我赶集去。我想……我想把这头克朗猪卖了,这驴日的不好好吃……”
月玲好生奇怪,他说去卖猪,怎么只拉了一条草绳?于是,就笑着问:“白话步,猪呢?”
吴白话把草绳交到左手里,腾出一只右手,朝身后指指,就又闭上眼睛。看来,他昨天晚上给谁家姑娘说媒,又熬了一个透透夜。
月玲笑着说:“白话叔,你扭回头看看,哪儿有克朗猪的影子?是一条空草绳!”
吴白话立即从迷迷瞪瞪中醒过来,抻了抻绳子,见果然拉着一根空草绳,就惊愕地喊:“咦,我的猪呢?咦,我的猪呢?我****妈……”
乙坤和月玲一块走过去,拉起草绳的另一头一看,见是谁用刀子割断或用剪刀剪断的茬口,就嘲讽地说了一句粗话:“叔,谁把你的活路做了!”
吴媒人哭丧着脸说:“我****妈,保不住是我迷迷瞪瞪地在前边走,谁****地从后边给我把绳子绞断了。妈的,这头猪至少卖一百多块钱哩,谁做这亏心事?”
“还不快去找?”乙坤怂恿着说。
“要找的,要找的!”
吴媒人扭回头朝原路走去。刚走了两步,又停住了,朝着乙坤喊:“哎,老二,你跟玲玲娃过来,步给你说个话……”
月玲和乙坤相视一笑,朝着吴媒人走了过去。
吴媒人诡谲地夹夹眼睛,问:“咦,你们两个是不是复婚了?”
月玲脸面一红,没有说什么。乙坤却把脸面一黄,说:“没有啊!”
吴媒人望着他俩,没有笑,也没有恼,却郑重其事地说:“要是还没有复婚,叔给你两个中撮合撮合……本来就是好好的一对儿,你看……”
“嘁!嘁!”月玲不悄地训了一句吴白话,扭头就朝大桥上走去,并嘟嘟囔囔地说:“谁要你吴白话多嘴!”
乙坤见月玲对吴媒人轻蔑的那种姿态,就小声地安慰他说:“白话叔,甭在心里去,她就是那种脾气……再说,我已经结婚了,媳妇马上就要生娃了……”
“噢,是这样!”吴媒人失落地说:“叔不知道喀!”
“乙坤,过来!”月玲在大桥上喊:“跟他有啥话说?不嫌乏味?”
吴媒人听到了,朝月玲扔过一句:“你贼女子嚣张个啥?连你妈也是我说的媒!”
“快走快走,到派出所里还有正事哩,跟那号货有啥说的!”月玲又催促乙坤。
乙坤只好向吴媒人苦涩地一笑,说:“叔,把猪要好好寻哩,养一头克朗猪不容易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