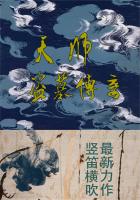“可是这一次错误我是终生都不会原谅自己的,真正的罪人是我,我既害了柳毅,又害了她的妻子和女儿。”
我问她:“柳倩是怎样把命丢在了路上,你又是怎么坚持到了拉萨?”
“柳倩是在藏北的两道河得病的。她先是拉肚子,接着发高烧,不吃不喝,昏昏迷迷。我叫她的名字她不答应也不睁眼,我害怕极了,便背着她走回头路,想返回五道梁。没想走到唐古拉山下,她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病倒在地。多亏了一位牧民阿妈,她掩埋了柳倩,又把病得奄奄息的我背到她的帐篷里,请来藏医给我治病。一个月后,我的身体恢复了健康,上路继续朝圣。到拉萨已经是半年以后的事了。”
德吉梅朵的睫毛上挂着泪珠。为了转移话题,我又给她提了个问题: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仍然很想知道你写那张大字报的动因和一些细节。”
德青梅朵显然不大愿意提起往事,她尽量用简练的语言,浓缩了当时的情景:“那些天,我从站内站外人们的议论中,第一次知道了彭德怀这个名字,也第一次知道了柳毅曾经犯下了佛祖也不会饶恕的罪。这时,我突然想到了他对我唱语录歌那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于是你就写了那张大字报?”
“不,是有人启发了我……”她不往下讲了,稍停,又说,“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决定柳毅去道班后我才写的大字报。”
我仍然觉得有话要问。
“那一年你多大啦?”
“14岁。”
“柳倩呢?”
“跟我同岁。”
“应该说你们都是懂事的年龄了,但是毕竟很单纯。”
“单纯就是善良吗?”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德吉梅朵似乎不大同意我的话,她说:
“正是单纯,别人给你涂上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
“如果说我开始懂事的话,从此我懂得了一个单纯的人是多么危险!”
我们都不说话。我知道,我的心、她的心都在剧烈地跳荡。
孩子的单纯是一种罪过吗?德吉梅朵错了吗?生活中真的不该有单纯吗?我不知道。
我对她说:“德吉梅朵,抬起头来,丢弃已经无用的那些格言,去创造我们心目中真正的太阳。世界上绝对不会有不落的太阳,但是每天迎接一个新太阳这是我们应该享受的一种权利。”
德吉梅朵听了我的话,擦干眼泪,旋即,泪水又涌满了眼眶……
当德吉梅朵把那本识字课本埋在柳毅和他妻子的坟前时,我才发现这儿是一片墓堆。
这是我和德吉梅朵来到五道梁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天刚蒙蒙亮,我俩就来到柳毅夫妻的墓地,与这对亡人告别。同来的还有五道梁道班的青年养路工索朗央金。
选在这个时候来祭灵,完全是索朗央金的主意。她告诉我们,每天太阳出来之前,她总能听到从坟地里传来一阵一阵的脚步声,开始她并没在意。无论是什么人的脚步声都似乎与她无关。这件事引起她特别的关注,是一天清晨,她上班时无意间闯进墓地以后,明明空无一人,可是脚步声却依然清晰、洪亮。她原地站着,看了又看,分明没有一个人,可是脚步声一直没有间断。她回到道班后把这件怪事给大家一讲,同志们都说那是柳毅和妻子起得早,用脚步呼唤太阳出山呢!从此,就有了这样一个传说:柳毅夫妻每天起在太阳之前,沉睡的青藏高原是他们唤醒的。
这毕竟是个传说。我们三人到墓地的这天,就没有听见任何脚步声响,因为风特大,所有的声响都被风卷走了。
德吉梅朵跪倒在墓前,三叩首。我和索朗央金默默地跟着她依次动作。
来时她带了一把铁锹,这时在距离坟前一尺处挖了一个坑。我俩帮她干活,很快一个像脸盆样的坑就出现于眼前的地上。
德吉梅朵把一个用红布包着的长方形的东西放进坑里,埋上土。
合葬墓前突起了一个小土堆。
“埋的是一本书吗?”我这样猜想,问道。
她并不回答我的话,只是说:
“那年,柳站长和李琴阿姨费了好大劲才弄到这本书,他们对我抱着多大的希望啊!我也坚信自己有了文化后一定会吸取丰富的营养,做一个真正的人。没有想到我学了一点文化,倒变成了一个傻子。”
我明白了,她埋葬的是那本《农民识字课本》。
她又给小土堆添了一锹土,说:“我不配拥有它。让它物归原主吧!”
之后,她又跪在坟前,痛哭起来。
太阳还没出来。
我们三人在墓地久久地徘徊着。因为越来越靠近日出,大地那弯弯曲曲的轮廓线渐渐地明晰起来。当我们走到一个山坡前时,索朗央金突然提了个建议:咱们就在这里看日出吧,你们会看到一幅非常壮丽的日出景色。
于是我们坐在了山坡上。
随着曙光的降临,五道梁那一片房舍越来越清楚地跳人我的眼帘。当然,我首先看到的还是那座合葬墓。随之,我又看到在合葬墓的后面及左右两边,都有一个一个的土堆。我马上想到了那很可能也是坟包。一问索朗央金,果然是。
我又问:“这里埋的都是些什么人?”
索朗央金答:“死在死期之前的人。”
“什么意思?”
“柳毅和他妻子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时都三十多岁,柳倩难道不也是这样的人吗?一个14岁的姑娘!”
“柳倩?她不是死在去拉萨朝圣的路上,埋在唐古拉山了呀!”
“后来有一个人把她搬迁到这里来了。”
“谁?”
“就是在兵站和柳毅搭班子,后来在《解放军报》那篇文章旁边批下一句话的那个人。”
“他的良心发现了?”德吉梅朵似乎不大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我们都沉思着。
我继续和索朗央金对话:“你说得很对,确实他们都是死在死期之前的人。还有些什么人?”
索朗央金一一数说着:“有一个步行准备穿越西藏的独行者,走到这里患上高山肺水肿,永远倒下去了;还有一个从珠江边来的孤儿,到西藏去寻父。他说他父亲是50年代进藏的老西藏,可是他找遍了西藏也没有找到。在返回老家的路上,他在五道梁咽下,最后一口气;另外,有个来自北京的支援西藏建设的大学生,不幸遭遇车祸,命丧黄泉……”
索朗央金把这些死者的身份、死因说得这么清楚,使我十分惊讶,当然更多的是钦佩。在这个“生命禁区”,死人的事太常见了,有多少人默默无闻地隐姓埋名地长眠在这里。没有亲人在身边,一个土坑,几锹黄土,就是他们永久的归宿地。他们都是父母的骨肉,他们都曾经有过温暖的家,甚至是一家之主,他们在明亮的教室里听过老师讲课,有的还是从中国名牌大学走出来的……他们完全可以在明媚的阳光下选择自己的未来;但是,他们肩负着使命来到了西藏,离世时年轻得已来不及完成使命了。也许他们在离开家乡、学校、单位的那一刻,想到过会有苦难和不幸来找自己,但是当厄运真的降临时,他们肯定感到突然甚至有过怨恨。是的,他们也是支撑共和国的一部分基石,包括埋葬在这里的那些冤魂……
索朗央金突然大喊一声:看,太阳出来了!
她的喊声还没落地,一轮喷薄而潇洒的红日跃上山脊,积雪的山巅立时像喷上了一层艳丽的红粉,十分诱人。几乎只是一眨眼工夫,阳光便呈扇形扩散开来,洒满了眼前的坟。最先接受这阳光的自然是那座合葬墓了,它变得金红闪亮。接着,它周围的坟堆全都披上了艳红的彩衣。
这时候,我最直接最动情的感觉是,这片被人遗弃了的墓孕育了在中国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日出风景。
我觉得那本刚埋进坟地的书翻动起了书页,记载着五道梁瘫痪在永冻层的历史从此被翻过去了。这里的亡灵在瞬间都变成了一粒粒发绿的种子。我触摸到了可可西里草原萌动起来的生命的血脉。
我的心头涌上一股难以遏制的情感:这片也许不能算古老但却充满未知的坟地,一下子变得生气勃勃了。我和我的同事们多少年来担惊受怕的那个世界,在这个美丽的清晨,随着这徐徐上升的火球消失了!
就在我们返回兵站的路上,听到可可西里草原深处传来几声分不清是藏羚羊还是野驴倒地的扯肝裂肺的惨叫!
我无法不为一只野生动物的命运悲哀,但是我更多的还是关注人的生存。在这日照很短,终年冰雪不化的五道梁,我毕竟有了一次令我永生难忘的看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