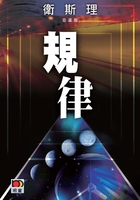天青拄着拐杖,站在河边一棵枯槁柳树下,静静望着河面。
当着樱草和竹青的面,他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不想让他们担心。但是到了深夜,他们都不在了,黑暗的屋子里,绝望和痛苦就像两只巨大的怪兽向他袭来,凶狠地噬咬着他,让他整个身体支离破碎,就像那条腿一样,永远都拼不起来。这天晚上,他咬紧牙关,硬撑着拄起双拐,推开屋门,走进静寂的院子。这院子曾经洒下他多少汗水,留下他多少足迹,纵是在受伤后,他还曾多么热切地在这里练他的腿,不怕辛苦,不怕劳累,不怕那些钻心的剧痛,信心满满地期待能奔走如飞的一天……
但是,原来,它们是早就已经死透了的,任他怎么坚持,也不会再有一丝生机。
前门车站的大钟,悠远地打了三响。天青悄悄开了街门,穿过寂静无人的大街,走向广盛楼。刘师傅不在,院门虚掩着,他一步步挪向戏楼后面,想去久违了的后台看看,但是那短短几个台阶的小楼梯,如今已成天堑,身边没人搀扶,他根本上不了楼。站在楼下,仰望着那曾经无比熟悉的门口,头顶白惨惨的月色,黑黝黝的天,冷漠地向他昭示着未来的下半生。
如果从此跛了,他还能做什么?一个堂堂七尺男儿,就这样残疾着度过余生吗?永远告别他的戏台,告别他的西皮二黄、胡琴锣鼓,告别他的盔头他的靠,他的银枪他的刀……就算他能放下他的戏,能头也不回地转身,又将如何面对茫茫前路?腿跛成这样,连窝脖儿打鼓儿都做不了,他难道要靠樱草养家吗?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废在家里,看着樱草一个人辛苦劳作,做戏衣做盔头,娇嫩的小手磨出厚厚硬茧,为着一家人的温饱?
仿佛上天觉得他的痛苦还不够彻骨,悲怆还未到极致,突然又让他撞见一个林郁苍,将他狠狠地打入尘埃,沉沦在绝望的黑沼之底。他终于意识到,可怕的还不在于他将没有办法谋生,而是在于,他根本失去了最基本的保护自己的能力,更不用说保护樱草。他再也不可能从拐子手里,从焦德利手里,从林郁苍手里,从任何人手里救下她,在如此危机四伏的乱世,他没有办法再保护自己心爱的人,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孤独地对抗这一切了,他是一个彻底的废人、累赘,连林郁苍都能尽情将他折辱,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踩成脚底下的泥。
晨光中,他跌跌撞撞,拼命地走向西河沿。右腿还是那样疼痛难忍。但是他也不想再顾念着它了,毫不犹豫地一步步踩下去,任那锥心刺骨的疼痛,一阵阵穿透他的全身。到了那棵柳树下,腿已经完全不听使唤,血顺着裤脚向下流。就让它这样痛着,心中的抑郁,似乎反倒减轻了些,原来一个人在极度心恸的时候,肉体上的痛苦根本不算什么,让人甘愿用它将精神上的痛苦分担。
眼前就有一个冰洞,离他不远,冰缝犬牙交错,露出里面一泓黑漆漆的河水,静静地,发散着彻骨冰寒。这黑洞仿佛有着奇异的吸引力,在吸着他过去,走过去,投身向它,那里面的寒冷,一定能冻结他的所有苦痛,肉体上的,精神上的,全都被它融化,吸走,他再也不用为这条断腿挣扎,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他操劳,这生命静悄悄地来,也静悄悄地去,就像他从高台上摔下来时一样,转瞬之间,一切化为乌有……
他迷迷茫茫地望着那个黑洞,迷迷茫茫地抬腿,却不料这腿已经一步都挪动不了,只有身体向前一倾,摔倒在冰面上。他的脸贴着寒冰,唇边都是灰土,感觉得到脸颊有擦伤,热辣辣的,似乎流了血。但是他不想理会。他闭紧了眼睛,似乎就飘浮在一个虚无的世界里,触手冰凉,身体内却是一片火热,凶猛地燃烧着,将他烧得晕眩,不想再去思考任何凡尘琐事。
如果这就是人生的尽头,该有多好!他希望自己就这样长眠下去,永远不要再起来,当他的腿已经没有办法支撑身体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再起来。眼前如一出大戏即将终场,锣鼓声骤,各色人物纷纷登台,唱出自己的最后一曲,他已经没有力气为他们喝彩了,只能这样无声地告别:三叔,三婶,竹青,师父,樱草……那张小桃子脸,就在今晚临睡前,还伏在他身边,温暖地亲吻着他,语声至今回响在他的耳畔:
“用了这么多年才终于和你在一起,这世上我什么都不再企求了,只求你在……”
天青又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碎得一块块、一片片,散落尘埃,无法收拾。是,他以前听到过,他曾经有过这种被利刃插进胸口,把心割裂成一片一片的感觉,那是在他十一岁,在白家小院,眼看着哭得双眼红肿的樱草被塞进车子,驶出胡同的时候;是在他十九岁,在林家大宅,樱草惨白着脸将那小铜牌牌还给他,要他忘了她的时候;啊还有,在六国饭店的楼下,他抱起樱草,看见她嘴角带血、面无人色的时候……
他原来已经有这么多次以为会永远失去她了吗?他原来已经心碎过这么多次,死过这么多次吗?他和她历经了多少劫难才守在彼此身边,他难道要自己操起这把利刃,去割裂自己的心也割裂她的心吗?
他没有法子再躺下去,再怎么意冷、心灰,都做不到。他渴望着重新站起来,走回去,和她在一起,紧紧握住她温暖的小手……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不是生计,不是荣辱,就是这双充满爱惜与信任的手。为了这双手,值得丢下一切的浮华,一切的旁骛,一切的内外交困、纷扰嘈杂。能不能高贵地活着,有什么重要?真正的爱与珍惜,是能为了她,宁愿残缺而卑贱地活下去。不是吗?肯为她的开心而开心,为她的伤怀而伤怀,肯为她付出勇气、关爱、血汗、生命,就应当肯为她承受伤痛,承受折辱,承受世间一切苦难与挣扎。
他猛地睁开眼睛,望了望四周,一时间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如同再次从高空跌落一般的冲击,让额头都冒了一层虚汗。他咬紧牙关,艰难地撑起身子,重新爬回柳树下,抓住拐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天已经完全亮了,他得回去,她一准在找他,大家准定都在找他,那么多爱他的人,他不应当让他们担忧……
“天青哥!”
一个熟悉的身影,沿着河边飞跑而来,老远地冲他挥着手,一口气奔到他面前。她的辫子跑散了,一头长发披在脑后,鬓边几缕发丝,挂满汗水。她惊恐地上下打量他:
“一早上就不见了你,怎么回事?乌老三说,我哥……打了你?啊!你这满腿的血,他打的?”
天青没有回答,一把拉过她的手,颤抖着,紧紧握住。他珍惜地感受到她肌肤的温热。那是只有两个人好好地活着,真切地相守,才能触摸到的温热。
“我没事。我们回去吧,以后我……再不会这样。”
樱草还是站在原地,不太置信地凝视着他:“真的吗,你自己跑到这河边来干什么?天青哥,我知道你性情刚硬,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天青眼中酸痛,轻轻拥住她,将脸埋在她的头发里:
“我来想一些事情。现在已经想明白了。”
“什么事情?你告诉我!”
天青静了一会儿。
“我得好好活下去。只有活着,才能……爱你。”
他握紧她的手,拉到自己胸前,按在心口。隔着衣衫,隔着肌肤,两人的手掌都能感受到那强健的心跳。
“只要我这里还在跳,就算我的腿没了,手也没了,鼻子眼睛耳朵,全都没了,我也会好好地留下来,陪着你。”
樱草的泪花飞转,但是她的眼睛在微笑。她伏在他胸前,轻轻按住他的心口,手心的温暖,一直传递到他心底最深处。
“只要你这里还在跳,我也会好好地留下来,陪着你!”
人,到底是为了什么活着?樱草以前,还真没有仔细想过。对她来说,活着就是活着,是世间最美好的事,天底下有太多事物值得开心地活着:灿烂的阳光,凉爽的风,丁香花的香气,老槐树的浓荫,故宫的红墙绿瓦,北海的碧湖白塔,广盛楼的丝竹锣鼓,九道湾的青砖小路……尤其还有那些温暖的手,亲爱的笑容:爹爹的笑容,天青哥的笑容……
但是,生命短暂,万物无常,一个人的一生,浮沉辗转,原是由不得自身。总有些人,有些时候,无法看到那些美好的光芒。当你懂得了失去的滋味,尝到了绝望的痛苦,永恒地陷身在黑暗里的时候,还要为了什么活下去?樱草和天青,曾经也不知道,现在他们知道了:人活着,是因为人间有爱。只有活着,艰难地走下去,挨下去,才有可能迎来那些风,那些阳光,那些丝竹锣鼓,那些温暖的笑容……当活着成为一种勇气,爱也就有更大的力量,让你在漫长的黑暗里,始终守着一线不灭的光。
春风起了,裹着细细的沙尘,吹得人满头满脸。阳光倒还和暖,洒落在孕育着新一年生机的枝头。天青坐在樱草房里,帮她给盔头簇纸活儿,他的手劲儿,着实厉害,那厚厚的纸袼褙,一刀下去连簇八层,图案纹丝不乱。
“说真的,天青哥,你做什么活儿都是把好手。”樱草的眼中,还是充满少年时候的倾慕。
天青笑了,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多谢林师傅夸奖……我是想好了,就算彻底瘫在炕上,我也能养活你。七行七科,我能做的活计多着呢,衣箱盔箱梳头桌,都说肯收我做徒弟。戏呢,我也不放下,还能帮着师父教导师弟们。差只差在,跛了脚,终是不能再上台了。”
“跛不跛脚,你都是一等一的好男儿,没谁能及得上你。”
“你再夸下去,我要把手也戳坏啦。”
樱草噗嗤一笑:“你跟竹青哥没学着好去!……”
“樱草,有朋友来看你。”三婶在院子里喊道。
樱草放下手中活计,赶出屋子一看,不由得惊喜地呆在当地:
“少湖!天哪,可太久没见着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