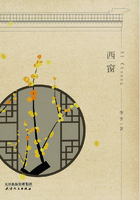夏日,清晨,九道湾白家小院,樱草倚坐在檐廊栏杆上,静静看着天青练功。
这座栏杆,本是她小时候坐惯的地方。每每拿着一块槽子糕,或是一把海棠果,坐在这里悠搭着两条小腿,看三个师哥在院子里练功……“当时只道是寻常”,生活中那么多平凡琐碎的小事,谁珍视,谁记得?都要在岁月更迭、风霜历练之后,才知晓它的宝贵。童年时司空见惯的情形,在如今的樱草看来,都是最幸福最安宁,最值得留恋的好时光。
学期已经结束了,虽然在复习备考的紧要关头被关了黑屋,但是樱草的大考成绩,还是名列前茅,这令她很开心。林家没人关心她的学习成绩,对林墨斋来说,或许樱草整日关在家里针黹刺绣更合心意,但是当年在白家生活时,白喜祥时常对她和三个徒弟谆谆告诫:功是为自己练的,书是为自己读的,人生在世,太多事情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有学问、功夫,修到了都是自己的。这些话儿,至今还牢牢记在樱草心里头。
天青也还是像小时候一样,那样聚精会神地练着,都没有察觉樱草的到来。今天天气燥热,艳阳毒辣,他只穿了条扎起裤脚的练功裤,赤着上身,却蹬着一双厚重的厚底靴。左手扣了一对银枪,右手扳起右腿,做一个“朝天蹬”,脚尖直抵头顶,然后又将腿扳向面前,仅凭左腿之力,慢慢曲膝下蹲。蹲到几乎贴地之后,循着原路,慢慢起身,将右脚扳回“朝天蹬”,接着又蹲下去,又站起来……
樱草坐在他背后,一直望着他如此循环反复,把这套身段做了有十来遍。完成之后,换另一条腿,又做了十来遍。烈日照耀下,汗水顺着他的脊背滚滚奔流,似一道道银蛇,迤逦闪亮,在脚下方砖上,滴成小小的一汪。那条始终金鸡独立的腿就像是和这块方砖铸到一起似的,牢牢地,稳稳地,钉在地上。
樱草斟了一碗茶,在天青终于收式停下来时,跑上去递给他。天青接过来,兜碗底倒进嘴里,对樱草一笑,一口雪白牙齿在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醒目异常:
“放暑假了,怎么不待在家里,还能出来?”
樱草做个鬼脸:“整天待在家里头,还不闷死了我?我禀明爹爹说是学校组织活动,嘻嘻……天青哥,刚才练的是什么?小时候可没见过。”
“三起三落。”
“三起三落?我看不止呀。”
“噢,这活儿看的是个‘稳’字,特别吃功夫。师父说了:台下起码得练成十起十落,台上才能稳稳当当地三起三落。等会儿他出来查验,若是做得不够稳,还不知要再来几起几落呢。”
“这大暑天的,真辛苦。”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嘛,要的就是这个劲儿。”
樱草递上绞好的面巾:“什么时候有空,也给自己放个假呗,出门逛逛什么的。成年到头就是练功唱戏,一点儿都不见你们休息。”
天青接过面巾,擦着脸上的汗:“习惯了。”
“出去逛逛嘛。生活不光有戏,世上也不光有一座广盛楼。”樱草歪过头,“我陪你一起逛,好不好?”
天青手里的面巾,停在脸上,只剩一双睁得大大的眼睛,亮晶晶的,在面巾上头望着樱草。十八岁了,他始终还带着点儿少年人的稚气神情,眼神清澈澄明,透着满腔的认真、诚朴,仿佛未经尘世沾染一般的纯良。樱草见惯了自己兄长的惫懒模样,对天青哥这份清气,尤其地感动起来:同样都是十八岁,相差怎么这么大呢!忽然她想起来:
“对了,天青哥,过两天是我们诗社聚会,在颐和园,我和你一起去,好不?有十几个人,中学生、大学生,年纪都和咱们差不多,大家一起谈诗论诗,顶有意思的。”
天青为难了:“诗啊,我不懂呢。”
“我们也不是很懂啊,就是同龄人在一起交流交流,学习、生活、国家、社会,各种的感想。年轻人嘛,要有思想的碰撞,才能产生青春的火花!”樱草很为自己的主意兴奋,两只脚一踮一踮,笑眯眯地仰望着天青,“一起去吧,我做你的介绍人!没准你一去就喜欢上了,以后总想参加呢!”
天青无奈地摇了摇头。他可不觉得自己会喜欢上诗,但是这小师妹要他做的事,他什么时候拒绝过呢。
在天青小时候,颐和园还是传说中慈禧老佛爷的离宫,皇朝虽已不再,重门依旧深锁。五年前,这座皇家园林辟成了对外开放的公园,当时全北京老百姓蜂拥而去,争相瞻仰盛名久播的佛香阁、仁寿殿、玉澜堂……但天青的生活,整日围着广盛楼打转,还真是从未优哉游哉地逛过公园。如今,在一个无戏的下午,破天荒进了这座宏大园林,满眼花香鸟语,草长莺飞,楼阁成群的万寿山,碧波荡漾的昆明湖……于天青而言,全是闻所未闻的胜景。
快乐地呼吸着山林间芳草的清香,他对身边的樱草频频点头:
“你说得对,世界这么大,这么美,真应该出来逛逛,一畅胸怀!”
尤其,还是和樱草在一起。她正开心地笑着,脸颊上绽着小小梨涡,像小时候那样,一边走一边情不自禁地蹦蹦跳跳。平日里只穿女学生制服的樱草,放假之后,换上了旗袍和绣鞋,虽然总是颜色素淡,花式简单,但是看在天青眼里,都比戏台上天女还要更美十分。今天她穿一件淡青旗袍,窄窄滚了一道同色丝边,衣角绣着小小的嫩黄中带点儿浅绿的花朵。袍身并不像时下流行那样紧紧箍在身上,而是十分宽松,反而显得整个人更加纤细窈窕。
“好看吗?”樱草拎着衣襟给天青看,“我自己做的,花样都是自己画的哪。”
“真好看,好俊的手艺。”天青认真地俯下身子看了看,“绣的什么,海棠花?”
“樱草花呀!我的名字。”樱草得意地笑,“樱草色的樱草花!”
天青不禁又仔细看了一遍:“真漂亮!颜色也雅致。”
“能用到行头里不?我家裁缝金爷,祖上在前清宫里做行头的,家传绝艺,等我好好跟他学学,给你做一件樱草色的行头。”
天青笑出声来:“我心领了!不过,武生行头可不能是樱草色的。”
“怎么不能呢?”
“行头都有固定形制,颜色花样,各有讲究。颜色只用十种,‘上五色’红黄绿白黑,‘下五色’蓝粉紫香月,像我唱的戏,通常只穿‘上五色’的行头。”
樱草扁扁嘴:“好多的规矩呀。颜色只要漂亮就用呗。”
“那哪成,你想,赵云穿一件樱草色的靠,像你这样,嫩生生的,哪还有白马银枪赵子龙的气概?他在所有戏里都只穿白色,这都在讲儿的。”
说话间,他们已经走在湖畔长廊,曲径通幽,玲珑剔透,层层叠叠的坊梁上全是彩画。樱草仰头望着,喃喃道:“我记得……”突然疾走几步,指着梁间一幅画:“看,这是赵云吧?”
天青赶上去,凝目一望,那画上是一员白袍将军,持枪挎剑,牵一匹白马,面前一位抱着婴儿的妇人坐在井边。天青又惊又喜:
“正是赵云,这是《长坂坡》啊,我会唱这出戏。呀,这长廊上画的都是‘戏出’呢,你看,《卧龙吊孝》《武松打虎》《四进士》《八大锤》……”
要依着天青所好,莫不如就在这长廊游玩整个下午,方是赏心乐事,但樱草还是拉着他一直赶去长廊尽头,到清晏舫那儿参加诗会。这是一座十余丈长的巨型石舫,壮观的两层船楼,花砖铺地,彩色玻璃镶窗,湖光山色之间,宛若一座宏大而精美的雕塑。船楼上已经聚集了一群年轻男女,远远见到樱草过来,叽叽喳喳地招着手。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探身到船栏外,笑着喊道:“最后一个啦,还不快点儿!”
“你们好早!我也没迟到呀!”樱草大声应着,拉着天青,加快脚步走上船楼:
“天青哥,这是陈少湖,我们诗社的社长!”
“这位就是樱草介绍的靳先生吧?欢迎新成员!”
陈少湖穿一件雪白的翻领衬衫,潇洒地卷着袖口,腿上西裤笔挺,皮鞋锃亮,和穿着长衫布鞋的天青,恍若身处不同朝代。他迎候在船楼栏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天青,老远便伸出右手,见天青已经拱手作揖,也仍然执拗地伸着。天青微微一笑,放下手来与他相握。陈少湖神情略为和缓,转身拍了拍掌,对船楼上一众诗友介绍道:
“今天我们诗社有幸迎来新成员,靳天青先生!著名武生,见过报的。”待大伙儿鼓了阵子掌,天青作了个四方揖,陈少湖笑着转向他:“靳老板,戏里上山入伙要有投名状,我们的新成员也得有啊。这样吧,您先分享一首您喜欢的诗吧!”又是一阵热烈掌声,倚在四周栏杆上的男男女女,都好奇地望着天青。
天青没料到还有这一出,怔了怔,笑道:“我只是来长见识的,自个儿却不懂诗。”
陈少湖目光闪亮:“过谦了靳老板,来参加诗会,怎会不懂诗?选一首让我们见识见识才是吧。大家说好不好?”
掌声再起,陈少湖鼓得比所有人都响亮。
天青微一思忖,大方颔首:
“我是唱戏的,没读过你们说的诗,不过很多戏的戏文,也都是上好的诗句。我奉送诸位一段《铁笼山》里的《八声甘州歌》。”
他微微错开脚步,站个子午相,朗声吟道:
扬威奋勇,看愁云惨惨,杀气蒙蒙。
鞭梢指处,神鬼尽觉惊恐。
三关怒冲千里振,八寨雄兵已成空。
旌旗摇,剑戟丛,将军八面展威风。
人似虎,马如龙,伫看一战便成功!
势若渊渟岳峙,音如虎啸龙吟,众人都看得呆了。一直以异样眼神打量天青的陈少湖,也不由得在声歇的裉节儿上,低喝了一声:“好!”满场“哗”的一声,都跟着猛烈鼓掌。这声好儿,叫得在行,叫得地道,天青不由得注意地望了他一眼,两人目光相接,交换了一个微笑。
诗会正式开始了。男生女生一个接一个地,或慷慨激昂,或宛转哀怨,声情并茂地朗诵一首首诗歌,每首都是天青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认真而困惑地听着:
……您的爱给了我才有生的喜悦;
可爱的姑娘,请与我怜悯,
莫要把人命看同鹅绒轻!
您的爱不给我便是死的了结。
这是陈少湖选来分享的诗,他蹬在船边石级上,伸开双臂,仿佛在戏台上一样动情地朗诵着:
……假使您心冷如铁地将我拒绝;
可爱的姑娘,这您太无情,
但也算替我决定了命运!
假使您忍心见我命运的昏黑……
朗诵结束了,陈少湖脸上浮现笑容,向大伙儿施了一个西式鞠躬礼,赢得一阵热烈掌声。天青坐在角落里,茫然跟着鼓掌,悄声问樱草:
“他念的是什么?”
“刘梦苇先生的诗《最后的坚决》。喜欢吗?”
天青实话实说:“嗓子很好,音正,气足。不过诗里讲的,我不大喜欢。什么‘不给我便是死’啊的。”
樱草笑了:“我也不喜欢。黑暗,忧郁,太悲苦。我觉得爱情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天青脸上一热。他从未这样直通通地面对“爱情”这个字眼,但在这样的气氛下,似乎确是可以,应该,很自然地拿出来讨论。他怔了一瞬,望着船楼外的湖水,轻声道:“那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
“爱情应该是热烈的、温暖的,带给彼此最完满的幸福与快乐。以死相挟有什么意义呢,爱一个人,难道不应该以对方的幸福为前提吗?得不到的爱就应该放手,不能以爱为名,而行伤害之实。”
樱草的小脸,还是那样青葱、稚嫩,眼神还是那样纯真、热烈,但是,天青头一回觉得,她跟以前,不一样了。她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身到心地长大了,不再是以前那个整天跟在师哥后面跑的小丫头子,她现在是个十五岁的大姑娘,文质彬彬的洋学生,身上似乎散发着逼人光芒,平日里聊天并不觉得,但是谈起诗来,这样明朗大方,侃侃而谈,那口吻那用词,于天青而言,陌生得几乎听不懂。他很努力地思考着,半天没有出声,樱草歪起头,笑着问他:
“你说呢,天青哥?”
天青把目光从湖水转回到樱草脸上来,认真回答:“我不知道。我没想过这些。我学的都是忠孝节烈、仁义礼智信,‘为国家,秉忠心,食君禄,报王恩’……”
樱草笑着摇摇头:“那都是旧时代的事了。天青哥,你别老是扎在戏里,真应该走出来,多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都是新时代的新青年,青春、爱情、自己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都要多做思考。戏呢,毕竟是上百年的古董了,它只在廊画里,在戏台上。”
天青蹙了蹙眉:“你不要这样说戏。”
“我尊重戏,它很美,很多学问,但是它弘扬的东西,肯定是腐朽的、过时的啊。”
天青的脸色沉下来,几乎要与舫上石砖一般冷硬。戏于他,是神圣的信仰,他不喜欢旁人随意亵渎,就算是樱草。尤其是樱草。一腔闷气,不愿意对这位小师妹发作,停了半天,方说:
“你还没看过戏呢。”
“倒是没进过戏园子,不过,从小就听你们说啊,看你们练啊。”
“你没好好看过,就不懂。戏里的好,不会过时。我就是喜欢忠孝节烈、仁义礼智信,这才是老祖宗千百年来留给我们的真正的做人道理。”
樱草仍然笑嘻嘻:“天青哥,你真犟。我不跟你争。你多来我们诗社就好了,听听咱们的同龄人是怎么看世界的。”
天青倔强地昂起头:“你多来看看戏就好了!看看真正的中国人是怎么看世界的!”
樱草伸伸舌头,做个鬼脸:“生我气了,天青哥?你可从没对我这么凶过。”
天青低下头,不做声。
又是一阵掌声,轮到樱草的诗歌了。她跳起来,笑嘻嘻站到船头上,两手在心口交捧着,曼声吟诵道: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惊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