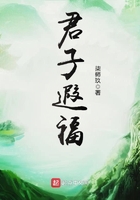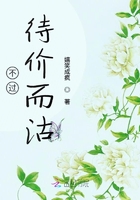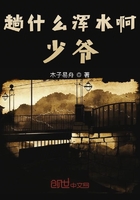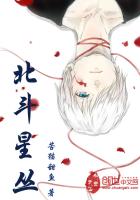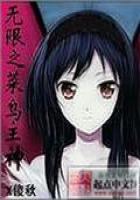“啊……”赵传书伸了一个懒腰从卧室里走了出来,经仪门(军官卧室的主门)走出卷楼(主桅下面的主楼)来到了甲板上。
但是与往常不同的是,舒服的海风并没有拂面而来。他甚至感觉不到任何的风。
赵传书一个激灵,睡意马上消失了大半。他抬头一看,只见前后两帆已落下,只留主帆依然安静的挂在主桅之上。
他左右看了看,只见离他最近的熟人就是姜三。于是他马上走了过去。
姜三此时正在将用完的绳子捆好。看到赵传书来笑了笑。
“三,怎么没风了。”
“早就没风了。”
“早就没风了?”赵传书吃惊的喃喃着:“多久了。”
“有两个时辰吧。”
“两个时辰!”赵传书几呼要跳起来了:“为何不叫醒我?”
“高掌柜说海上无风不过常事。无需担心。”姜三也知道高杰说的没错。所以不以为然的说道。
赵传书一听顿时便气急攻心,便想骂人。但是想一想自己制定了规具不能骂人于是便又忍了下来,道:“曹六睡了。”
“嗯。”
“去,把他叫睡到将针房找我。”
“好来。”姜三一听便起身去找曹六了。而赵传书则是急急忙忙的来到了舵楼内的针房。
明代针房乃是全船最重要的地方。什么是针房。针房就是放航海罗盘的房间,称为针房。明代海船一般都将针房设地舵楼之内。而舵楼故名思意就是操舵的地方。一般大船还在这里设军官的盥洗卫生之设备。而在舵楼的上面便是望亭。两者之间只有格栅阻格。方便捕盗随时了解方位指挥战船前进。
航海罗盘是我国发明的。我国发明指南针后,很快使用到航海上。北宋时的指南浮针,也就是后来的水罗盘。宋代朱或叙述宋哲宗元符二年到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099年到1102年)间的海船上已经使用指南针。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徐兢到朝鲜去回国后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描写这次航海过程说:晚上在海洋中不可停留,注意看星斗而前进,如果天黑可用指南浮针,来决定南北方向。这是目前世界上用指南针航海的两条最早记录,比公元1180年英国的奈开姆记载要早七八十年。
至明代中国航海业发挥到了巅峰。其中对罗盘的认识也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许多留传到后世的针经就是最好的证明。所谓针经就是以文字的型式将航行过程当中的罗盘针的指向,还有路程、参照物等记录下来的地图。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地图方式。
所以在明代航海只需要知道航向,然后通过计算速度得到路程便可以确实自己的大致位置。这也算是一种惯性导航吧。如果再加上一些参照物,如小岛、礁石一类的东西,便可以精确的知道自己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针房是整个船上最重要的位置的原因。
明代《西洋番国志》中说:要选取驾驶人员中有下海经验的人做火长,用作船师,方可把针经图式叫他掌握管理。“事大责重,岂容怠忽。”可见航海罗盘是海船上的一个重要设备。而堂管罗盘的人被称为火长。
顺风号的火长叫薛沛。乃是韩千户从定海卫请来的一个福建的老火长。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他原本已经不出海了。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经济不太好,居然被韩千户请来了。
不过虽然知道他是一个老把式。但是赵传书也觉得此人很怪。平日里都不喜欢与人交谈,就呆他的针房里整天研究他的针路(即航道,因为记录时用罗盘针方向记录,所以称针路)。一本针经象是宝贝一样的护在身上,除去他外谁都不能看。
赵传书刚一走进针房就见到了房间的中间放着一张四脚桌。在桌子的上面放着一个瓷碗。赵传书认得这就是明代的水罗盘——针碗。只见磁碗的外面用沙子固定,使得它不会因为船的摇晃而落到地上,或是移位。碗內底一般釉绘了一個类似“王”字的图案,有些碗外底还釉书一“針”字。而那个“王”字实则意指浮於水面的指南針,“王”字中一竖表示磁針,三横表示磁针穿过的灯芯草。灯芯草比重极轻,可以作为水浮磁針的载体。碗外底的“針”字表明這种瓷碗是专用於放置指南針的。
除去字以外,碗内还定二十四向,同样用釉绘上去二十四向,这点在我国汉代早有记载。北宋沈括的地理图上也用到这二十四向。把罗盘三百六十度分做二十四等分,相隔十五度为一向,也叫正针。但在使用时还有缝针,缝针是两正针夹缝间的一向,因此航海罗盘就有四十八向。大约南宋时已有这四十八向的发明了。四十八向每向间隔是七度三十分,这要比西方的三十二向罗盘在定向时精确得多。所以三十二向的罗盘知识在明末虽从西方传进来,但是我国航海家一直用我国固有的航海罗盘。
碗里一般都装有半碗水。无论船只如何的摇晃其水面都处于相对的平面,以最简单的方法实现了陀螺罗盘的功能。碗里的磁针就可以发挥作用。针碗的里边有一个穿着磁针的木鱼。鱼浮水上,鱼嘴与鱼头分别指南北。
薜沛此时正与他的一个本家的小孩一起正在桌子的另一面,居然都拿着一张纸在写写算算的。看见了赵传书来居然半点表示都没有。赵传书只知道那小孩子叫薜二,也不知道与薜沛是什么关系。但是这些不是他操心的事。
“赵捕盗进来做甚?”薜沛虽然没有象平日里赶其他人一样赶他出去,但是也没有表示支持。赵传书好在今天心里有事,心里不快一听薜沛的话不由得怒从心中来。
“都什么时候了,还搞你这小团体主义。”赵传书怒气冲冲的便将后世的东西随口而出。
中华语言就是这么奇怪,虽然什么小团体,什么主义的这个老头听不明白。但是他居然好象读懂了赵传书的意思一般。楞了一楞便叹了口气走到了赵传书的身边。
“赵大人可是为了无风而来。”
“当然,不为此事为了何事。这海上的事,事无大小具是大事。每一件都不能疏忽。二班的那些船工们现在已经精疲力尽,其他两班还在休息。现在船上都没几个能干活之人。只是这海上的危险说来就来犯不得一点疏漏。故而我只想知道这无风是也不是危险。”
“唉。”这老头叹了口气:“原本小老儿也欲告知赵总旗。只是事情尚不清楚故而未说。”
“什么事。”
“怕是暴风要来了。”
“暴风!”赵传书惊得一下子就要跳起来。在海上最可怕的不是什么海盗一类的。而是恶劣的天气,碰上海盗一类运气好的还能逃走。碰上不好的天气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正是,赵总旗请过来一看。”在薜沛的示意之下赵传书与他走到了船边。然后薜沛指着下面的海水说道:“赵总旗请看。今日的波浪松软无力,一点也不象平常那般平滑。今天空气燥势不安,带有异味。鸡鹅笼(船艉突出之悬舱,内饲禽类)里的禽类也都燥动不安。便是在此都能听到其叫声。可见危险不远。”
“……”
听到此赵传书呆了。开玩笑,自己第一次出航就就中了奖。前一世怎么不见运气这么好地的时候。
“什么暴风!”呼然一个声音从后面响起,赵传书回头一看,原来是曹六与高杰走了进来。
“曹甲长,高总管。”看到两人进来薜沛才拱了拱手。
“是暴风要来了?”高杰的脸色不太好。有些惊慌的问道。
“未能确定。”
“薜火长是老船把式了。你说地便是事实。现在还是当如何应对。”赵传书看到两人来了心理也安定了一点,主动走到他们的面前说道。
曹六与高杰看了看赵传书都没有说话。他们现在心情也很不好。都没想到原本想搏个出身。居然现在随时可能见了海龙王。
赵传书在发了几秒种了呆之后居然缓过来了。他走到薜沛的面前说道:“薜火长,现在船到哪里了。”
“之前几日顺风号较快,测速之时大都不上更。若是以赵总族的香烧之法,则测得为四节左右。晚上要慢上一些。总算下来共走了十二更多一些。”
赵传书知道明代计程的时候用的是“更”做为单位。一更相当于现代的三十公里。一般用小木片扔水里,然后用人走的方法来测速。如果人比木片更早到达船尾,则叫不上更,反之为过更。一般船速快于2.2节的时候往往为不上更。反之过更就是船速低于2.2节。
所以理论上薜沛的计算都是没错地。这个时代不可能有精确的里程计算,便只能大该的得出一个数字。而十二更就是说明船走了三百六十多公里的路程,大约是整个航程的一半还多一点。
“那我们周边可有海岛可以避风的?”赵传书马上便问道。
“难,此地乃是海之中。周边最近的岛也有二三百里之远。绝无可能找到可以避风之岛。”
“不至于吧。”赵传书一听呆了。这敢情好,怕什么来什么。他想了想又问:“那风从哪里来,我等有无可能避开。”
“从这海水来看,风当是从南,或是西南北上。我等若是要避开只能向北,希望他们会转向东面,不然……”
薜沛没有说不然会怎么样。但是赵传书不用说都知道不然会怎么样。这是什么年代,通讯技术不发达的年代。死了都没人知道。更别谈救助了。一但出了危险除了自救没有可能有人来救助自己。所以船一但出事,那全都完了。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高杰仿佛还觉得不够乱地,居然就坐在凳子上自己一个人胡说了起来。而曹六此时则是脸色铁青,一脸的灰败,呆呆的看着窗外默然不语。
“嚎嚎嚎。嚎什么嚎。嚎了便可以脱险吗?”赵传书看着高杰与曹六两人便来气。虽然自己也害怕到极点。但是至少还在想办法。这两哥们直接便在这里等死。
“你们两个若是要等死便一边去,若是还想活下去就听老子的话。”赵传书怒气冲冲的大声喝道。
还别说,这个时候他一喝高杰马上便停了下来。一脸惊诧的看着他。而一边的曹六也惊讶的看着赵传书。
“看什么看,现在就给我出去,把所有还在睡觉的死猪给的叫起来到甲板集合。凡是不起来地都给我扔到海里去。快去。”赵传书一喝两人居然都乖乖的出去了。
“我们尚有多少时间。”赵传书转过身来看向薜沛。哪里知道他居然也楞了一下。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哦,至多不过十个,八个时辰。”
“是吗。看来连老天都想跟我赌命哪。”赵伟书冷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