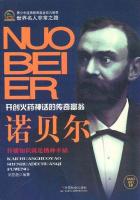“嗯,是吗?那他们干什么呢?”“到刚才为止都围坐在一起,喝着酒等着,但觉得可能不会来偷袭了,就各自睡了。让我一个人在这么冷的夜里站岗。”“这么说,是吩咐你站岗,你才站在外面了?”日吉点头时,天藏飞身而至,用大手捂住他的嘴说,“你要是叫,就没命了!”
日吉挣扎着:“大叔,大叔,跟我们说好的不一样啊!我不会叫嚷的,你放手啊!”他一边在天藏的掌中叫着,一边用手扒着天藏的手。
天藏摇头:“不行,我是御厨的渡边天藏。虽然听了你的话,知道这家已有所准备,但就是这样我也不能空手回去,那样就没脸见我的手下了。”
“所以……所以呀!”“你想怎么办?”“我会把大叔想要的东西拿给你的。”“你拿给我?”
“是呀,那样就行了吧?不用砍来砍去的,就解决了。”“你确定吗?”天藏收紧了日吉脖子上的手,逼迫他道。因为门迟迟不开,门外天藏的手下起了疑心,又惶恐又怀疑地频频叫着:“头……头儿!”
“出什么事了?”“这门怎么了?”他们开始摇晃大门。天藏拨开一半门闩,从开了的缝隙对外边说:
“情况有些不对,都安静点儿。还有,你们也不用围在这儿,藏到那边阴影里比较好。”于是手下们带着怀疑和惧意散开了,在草丛呀,树影呀各自藏了起来。日吉为了拿出渡边天藏让他拿的物品,从仆人的房间悄悄地向主屋走去,到了一看,半夜主人的房间应熄灭的灯火却亮着。
“老爷!”日吉在走廊恭敬地叫了一声。虽然没有回答,但却感觉主人拾次郎和夫人都没坐在那儿。
“夫人!”他又叫了一声。“……谁?”是夫人的声音,明显地因恐惧而颤抖着。刚才那些细微的声响和人声已经惊醒了主人和他的妻女。他们慌忙起身,察觉到有土匪来袭,正不知所措。日吉拉开门走了进去,主人拾次郎和夫人都盯着他看,带着无法抑制的恐惧不安的表情,无言地睁大眼看着他。
“野武士来了,有很多人。”日吉禀告。主人夫妇无声地咽着唾沫,紧咬着牙根无法言语。“要是让他们踏进来就大事不好了。老爷和夫人都会被绑,出五六个死伤的人也是肯定的。所以,我设计让野武士的头目在外边等着。”日吉把对渡边天藏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对主人夫妇说了一遍。
“所以,老爷,把野武士头目想要的东西拿出来给他吧。我给他拿去,给他了,他也就会走了。”
过了一会儿,“日吉,野武士的头目,到底要什么呢?”拾次郎开口了。
日吉立刻答道:“是,那盗贼渡边天藏看上的是当家珍藏的红瓷水瓶。”
“啊?要红瓷水瓶?”
“说是给他那个的话就走,没有这么便宜的事了,给他比较好。还有,这是我的计策,所以就做出让我偷偷拿出去给他的样子吧。”日吉有些得意地向主人夫妇建议,但拾次郎原本就比夫人阴郁惊恐的眉目间都有些发黑了。
“红瓷水瓶不是为了今天宴席,从库中取出,在茶会上用的那个瓷器吗?野武士的头目也真是个愚蠢的家伙,还以为他想要什么呢,跟我说要那个东西。”日吉有些窃笑的样子这么说着,可夫人呆住了,更加无语,拾次郎长叹一声,说道:“真为难啊!”
“老爷,您为什么考虑那么久?舍了一件瓷器就可以不见血光地渡过难关啊。”
“那可跟我卖的那些瓷器不一样啊。那是即使在明国也不多的珍品,是我费尽心思从明国带来的,而且还是已故的祥瑞大人的遗物啊。”
拾次郎一开始说,夫人也一起说道:“那是在堺的茶道用具店里,千金难求的呀,你……”虽然忍不住恨意说了,可是还是惧怕野武士。现下的世间,在各国都有很多因为反抗而被杀、家宅被烧的例子。这种时候,男人还是果断些好,很快拾次郎将难以割舍的留恋忍痛割断,说着“避免不了啊”,同时也多少恢复些倨傲的神态,从涂饰精美的柜子的小抽屉里拿出钥匙,扔在了日吉面前说道:“拿去吧。”虽然心里觉得日吉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才智,设了很高明的计策,但对这么轻易失去的红瓷水瓶的执念让他悔恨至极,没有夸奖日吉。日吉一个人去了仓库,抱了一个盒子回来了,把钥匙还给了主人。
“熄了灯,静静地休息比较好,不用担心。”提醒完了,日吉又再次走出门去。
“怎么样?”半信半疑等着的渡边天藏从日吉手上接过盒子,查看着里面的物品。“嗯,就是这个。”他脸上的表情放松了下来。“那大叔们还是早些回去比较好。刚才我在库房找东西的时候,点了蜡烛,所以加藤大人和其他的武士们醒了,说是要在宅里巡视一圈呢。”日吉一催,天藏立刻慌忙往门外奔,“小子,欢迎随时来御厨,让你做我的手下。”说完,身影消失在黑暗之中。
猫饭
天亮了,惊恐的一夜终于过去了。第二天白天,因为还是新年期间,来庆贺新年的客人一直络绎不绝。但瓷器店里有一种微妙的消沉气息在空气中飘浮着。主人拾次郎表情失落,一直都很活跃的夫人也不见踪影。在她的房间里,儿子於福正安静地坐着。她好像还没有从昨夜的恐惧中清醒过来,脸色苍白,像病人似的躺着。
“母亲,刚才,我已经跟父亲聊过了,现在,您就放心吧。”“是吗?怎么说的?”“开始时,父亲对我说的话半信半疑。我有跟他说了日吉平日的态度举止,还有我记不清什么时候他抓着我威胁说要把御厨的野武士叫来的事,父亲才得知,吓了一跳的样子。”
“说了要立刻解雇他吗?”
“那倒没有说,父亲还在考虑,可能觉得日吉是个有可取之处的小猴子。但我也说了,不能在家中养贼的喽啰。”
“最重要的是,我一开始就不喜欢日吉的眼神。”
“那个我也说了,说完后,父亲觉得他要是跟大家都那么难以相处的话,就只有解雇他了。但是,因为还有薮山加藤大人的面子,他自己不太好说,让我们去谈,还嘱咐不要冒犯到他们。留下这话,父亲就出门去了。”
“那太好了。那种像猴妖似的孩子,连半天我也不想用了,实在是受不了了。现在,日吉干什么呢?”
“在库房帮着打包呢,要不我立刻把他叫来,现在就告诉他?”
“算了吧,我不想看到他的脸。既然你父亲已经说了。你就今天把他送走,不就行了吗?”
“是。”於福心里是有一些胆怯的。“我明白了,报酬怎么办呢?”
“本来就没说给薪水什么的。他也没干多少活儿。我们供他吃,供他穿,这就已经多过他做的了。这么办吧,他现在穿的衣服就给他吧,再给他两升盐。”
於福觉得自己一个人去跟日吉说的话,总有些不对劲儿。所以他带着别的雇工一起往外边的瓷器库房走去。他到库房后看着里边叫道:“猴子,在这儿吗?”
头上顶着些秸秆干活儿的日吉说:“在,什么事?”他比平时都有干劲儿地回答着,跳了出来。
日吉觉得昨晚的事跟别人说不太好,所以谁也没有告诉。但他自己心里很得意,觉得主人今天一定会再次夸奖他,一天都暗自等待着。於福的旁边站着雇工中最强壮、日吉平时最怕的伙计。
“猴子。”
“啊?”“你,今天开始就回去吧。”於福说道。
“去哪儿?”日吉惊异地看着他说。
“哪儿?你自己的家呗。你现在还有家吧。”“家有是有……”没等日吉问出为什么,於福抢先说道:
“到今天为止,你被解雇了。现在穿着的衣物就给你了,马上走吧。”身旁的伙计拿着日吉的衣物包袱和两升盐道:
“这是夫人的心意,赏给你的东西。不用道谢了,马上从这儿出去吧。”
“……?”日吉有些茫然。然后,血一下子涌上了脸,眼神像是要向於福扑过来般的愤怒。“……明白了吗?”於福向后退着,从伙计手里取了睡衣包和盐袋放在地上,慌忙走了。日吉对着那身影,又是那个像是要扑上去的眼神,可是,眼中慢慢充盈了满满的泪水,什么都看不见了。他像野火一样的愤怒想要肆虐发作的同时,母亲悲哀的面容也出现在他的脑海。来这里做工前,母亲含着眼泪说道:
“这次要是再被赶出来,不仅失了薮山加藤大人的面子,母亲我也会觉得羞耻,没脸见人。”每次生了孩子后,都愈加憔悴的母亲,让他含着泪,抽着鼻子,像是不知该怎么做似的,呆站在那儿。
“猴子!”“你想怎么办?”
“怎么又弄砸了,不是说了解雇吗?”“已经十六岁了,到哪儿都能吃口饭,你是个男人,别哭,别哭。”其他的雇工和在场的人笑着,大家在他周围来来往往地干着活儿说道。
在日吉的耳里,只是觉得大家在嘲讽他。可他也没有让任何人看到他的哭脸,反而回头露齿笑道:
“谁哭了?我已经在这瓷器店待腻了。下次要去武士家,我要去侍奉武士。”日吉背起睡衣包,用地上的一根细竹棍插着盐袋挑在了肩上。
“要去侍奉武士哦。”“哈哈哈哈哈,”他说着那种话逞强。
虽然不讨厌他,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同情地目送日吉远去的身影。日吉踏出土墙后,立即就被蔚蓝的天空吸引了,只感觉到没有束缚,自由了。
去年八月,在与今川家的小豆坂战役中,为了立功,深入敌军阵营的弹正身负重伤,终于回家来了。弹正自回来后就一直卧床养伤,让妻子伊都看护。经过了寒冷的岁末,到了正月,腹部的枪伤每日疼痛,痛苦的呻吟声不断传出。伊都正在宅院中的溪流边给丈夫洗沾满脓血的汗衫时,突然听到了一阵歌声。
“是谁呀?……这么悠闲……”伊都有些火大地站起身,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因为房子在光明寺山的半山腰,把头伸到土墙外就能看到山下的路和中村的耕地,也能眺望到广阔的庄内川和尾张平原。萧索的冬日残阳,渐隐于田野尽头,今天也已是日暮时分了。
“晚上要纺线,天黑就到了晚上,赶着滴溜溜地纺线啊,时日却比纺线更难熬,呀哟,更难熬!”歌声很大,是不知当下社会的险恶和疾苦之人的声音,唱的是室町末期人们唱腻的纺线歌谣。传到尾张一带后,农家姑娘经常带着乡音传唱。
“哎呀,那不是日吉吗?”伊都远远看着从山脚边唱着歌边走上来的人,吓了一跳。来者正是前年拜托弹正介绍到瓷器店去做工的日吉。他背上背着一个不知装了什么的脏兮兮的包袱,肩上扛着一根不知挑着什么的竹棒,悠闲地走来。
“哎呀,一转眼长这么大了……”打量了一番后,她对日吉虽然长了个子但却依旧不知愁滋味的样子有些吃惊。
“——纵然辛苦,却怎么也得不到回报呀,唉!”“啊,姨母,你怎么站在那儿?今天……”日吉到了跟前,对着伊都点了一下头。边唱边走的他,轻松地问候了伊都。但是,年轻的姨母好像忘了该怎么笑似的,脸上还是一片阴沉。
“真是少见,是让你到上面的光明寺办事吗?”“不是。”日吉挠挠头,有些为难地说,“我被瓷器店解雇了,想着不跟姨父说一声不太好,就过来了。”“啊?怎么又……?”伊都皱起了眉。“你,怎么又被赶出来了?”
“那是……”日吉想解释一下,可不知为什么又开始觉得麻烦,就作罢了。
“姨母,姨父在吗?在的话,让我见一见行吗?我有事拜托。”日吉央求道。
“真是不像话,我丈夫在小豆坂战役中身受重伤,有今天不知有没有明天的状况,怎么可能让你见!”年轻的姨母毫不客气地说,“真是的,有你这样吃不得辛苦的孩子,中村的姐姐也真是可怜哪!”
日吉听了后轻声地问:“那,我有事想拜托姨父,不行是吧?”“什么事?”“姨父是武士,下次我想找个武士家做事,想让姨父介绍。”“你今年到底几岁啊?”
“十六岁。”
“已经十六岁了,你也多少懂些事理吧。”“所以啊,我才不想去那些寻常的地方做工了。姨母,没有什么可以介绍的地方吗?”“你也给我看看情况。”伊都没有一丝玩笑意味地告诫道。她瞪着日吉说:“武士家不会使用与他们家风不符的人,像你这种乡下长大的散漫小子,哪里会要你!”
婢女赶来报告:“夫人,您快点儿来吧,老爷好像很痛苦的样子。”伊都听后,什么也没说立刻就进去了,仿佛日吉根本不存在似的。被留在那儿的日吉,发呆了一会儿,看了看黄昏时尾张平原的流云,不久后他还是从土墙口走了进去,站在加藤家厨房的外边。虽然想马上就回中村的家,想见母亲,可是一想到继父筑阿弥,他就觉得回家的路满是荆棘。“还是先找到下一个做工的地方吧。”正是考虑到这个,所以日吉才先到薮山加藤家来说说,想先到这儿来看看。可是,弹正受了重伤。
“怎么办呢?”饿着肚子,日吉一边想着,一边漠然地想着今夜的住处。突然觉得冰冷的脚上,有什么柔软的东西贴了上来。低头一看是一只可爱的小猫。日吉抱起它,坐在厨房的边儿上。
“你也肚子饿了吗?”日暮时分的残阳,映照着他和小猫四周的寒意。小猫在日吉怀里瑟瑟发抖,暖和一点儿后就“吧嗒、吧嗒“地舔日吉的脸。“不要,不要舔。”日吉躲避着对小猫说。他并不喜欢猫,可是现在除了这只小猫以外没有人亲近他。突然传来了女人的惊叫声,日吉支起耳朵,小猫也惊得瞪圆了眼睛。对面廊下的房间里,突然传来了病人特有的暴躁怒斥声。不久,伊都就哭肿了眼睛退回厨房来了,可能不知为什么,她让弹正生气了,她用袖口擦着眼泪,把煎药的陶罐放在了炉上。
“姨母……”日吉小心翼翼地叫道,他一边摸着小猫的背,一边说,“这只猫,肚子饿了,一直在发抖。不喂它的话,就要死了……”
其实他也是在说自己也还饿着。可是,对伊都来说,这却不是管猫吃没吃饭的时候。
“你还在这儿啊?即使天黑了,也不会让你在这儿留宿的。”说着,她又开始擦眼泪。她煎着药,一个人抱着肩沉思,年轻的姨母身上已经不见了两三年前的幸福模样和初为人妇的美丽容颜,已经像被雨水打过的花一样凋零了。日吉抱着猫,和小猫一起忍着饥饿走向睡铺。
“姨母哭了,也许是有担心的事吧?”日吉设身处地地想着。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伊都,突然,他觉得年轻的姨母的身形有些奇怪,脱口问道:“姨母,姨母的肚子大了,是怀孕了吧。”
哭泣的伊都,正在最难过的时候,突然被问了这样的问题,好像被打了脸一样,猛地抬起头。
“你一个男孩子,这种话可不是你说的!下作的孩子!”伊都更加难过,生气地说,“快点儿,趁天还没黑,中村也好,什么地方都好,你快走吧。我现在没精力招待你。”说完就哽咽着躲到屋内去了。
“……回去吧。”日吉自言自语,正要站起来,小猫却不肯离开他温暖的怀抱。这时婢女因为日吉刚才的话,用小碗盛了些凉饭,浇了些汤,一边给小猫看着,一边叫着小猫。看见了饭,小猫抛开了日吉的怀抱,朝着饭奔去。日吉一边咽着口水,一边出神地看着猫食和小猫。
“……”没有人给日吉晚饭。日吉决定回中村的家去。他饿着肚子起身,走在院子里时,脚步声引来了从一个紧闭着窗户的房间里传来的盘问声。“谁呀?”
日吉吓了一跳,但立刻听出是弹正的声音。他答道:“是日吉。”他想着正好趁这个机会告诉弹正他被瓷器店解雇回来了的事。
“伊都,把那个打开。”弹正的声音在屋内响起。但是,他的妻子一直在劝说,傍晚的风冷,凉着了,伤口又会疼了,并没有打开拉门。
“蠢货,多活个十天二十天又能怎么样?打开!”弹正又怒道。伊都哭哭啼啼地拉开了门。
“日吉,会影响他养病的,问候完就赶快回去吧。”“是。”
日吉就站在那儿朝病室行了礼。加藤弹正把病重的身体靠在被褥上。“被瓷器店解雇了?”
“是的。”“嗯,也好。”“……”
“被解雇也不必觉得有什么羞耻的,只要不做不忠不义之事就好。”“嗯。”
“你的父亲,以前也是武士,武士啊,日吉!”“是。”
“只是为了吃饭,是为了口腹之欲而碌碌无为的武士,要为了尽天职,为了尽自己的本分而度过你的一生。食物只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是人天生命里注定的。所以,你一定不要成为一生都为混饭而碌碌无为的人。”
盐
已经快半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