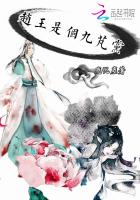他们关着房门争吵,声音越来越大。致善惴惴不安地坐在外面。门开了,他的母亲披散着头发,眼睛红肿。她尖声嘶咧,对抗着致善的父亲如同古钟鸣击般的声音。他看到他们两个人面目狰狞,粗野地扭打在一起。致善的父亲将她的手腕一把拧住,一手揪住她的衣领。
他非常惶恐,觉得他的父亲一定是想杀了他的母亲。他本能地冲过去保护,使劲推开他的父亲。他们估计不到年幼的致善会有这样的反应,一时间愣住了。他的父亲颓丧地松开手,魁梧的身躯如同泄了气的充气公仔,忽然之间松了下来。
他退后几步,沙哑着嗓子对致善吼道:“她都已经不要你了,你还在帮她?跟你妈一样不知好歹!”
声音像是从几十米处的井底沿着长满青苔的石壁传来,挟裹着巨大的冲击力,致善懵住了。然后是一片死寂。三个人在一番狂风骤雨之后各自默默消化着情绪。她朝致善看了一眼,欲言又止的样子,终于什么都没有说,拿起手提包跑出了家门。
在以后十几年的人生里,致善总是试图去回忆这个眼神和整个场景。那是他最后一次见他母亲的场景。如果他知道自那以后她与他就变成形同陌路,见一面要隔十年的陌生人的话,他一定会努力把所有细节记住。她穿的衣服,裙子的颜色,凉鞋的款式,有没有戴首饰。但是他什么都不记得,只有那个眼神。好像这个眼神是孤立的存在,不依附于任何人。
从哭得红肿的眼睛里投射出来的视线,蕴含着一个六岁的小孩无法理解的深刻意味,但是他读懂了,那是一种将要放弃的眼神,带着愧疚和无法挽回的决绝。他也没有跑过去拽住他的母亲,做出哭喊的样子,只是怔怔地站在那里。于是他记住的,只有那个最后离开时的眼神。
好像是在一夜之间,他母亲的东西从这个家里彻底消失了,似乎从未存在过一样。衣柜里塞得满满的衣服,各式各样的凉鞋,高跟皮鞋,洗手间里的沐浴用品,化妆品,香水,五颜六色的药片,长柄梳子,书架上的书,电影杂志,甚至包括清晨送牛奶的联系单上的名字。失去了这些东西的房子,好像是一具被挖去血肉只剩下骨架的躯壳,沉闷空洞。
他也再没有见到过赵叔叔。有的时候,连这两个人是否真实存在过他都开始怀疑。他翻出相册,一页一页地找,一丝痕迹都没有。都是他自己小时候神情漠然的照片。偶尔看到一张成年男人的相片,是父亲更年轻时拍的,站在某个风景区的入口处,双手叉腰,手臂上挂着西装外套,踌躇满志的年轻人的脸。
玻璃罐里的石头还在,他拿起一颗椭圆形小石头,周围有一圈圈红色条纹,条纹的形状像是高速运行的飞行器在空气中产生的轨迹,他举起石头,像是看到了遥远星空里的某个星球。他想,如果是赵叔叔,会看到什么。
他的父亲依然很少在家,他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致善,让致善称呼她作钱阿姨。钱阿姨的老家在安徽农村,身材粗壮,声音洪亮,讲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她的几个孙子也已经成年,用她的话说,她带过的小孩,自己的,加上雇主家的,少说也有几百个了。
她以风卷残云般的态势将这个房子重新清理了一遍,残存的骨架被填上了不一样的血肉,是粗糙的极度实用主义的血肉。门口的装饰柜被当作了鞋架。洗手间里摆上了各式清洁剂。书架被擦拭得干干净净,象征性地摆放着一些致善父亲早年的书,《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市场经济的要素》,等等。
钱阿姨负责接送致善上学放学。基本上,不上学的时间,致善只能和钱阿姨在一起。她是勤俭自持的人,哪怕没有大人在监督她,也总是恪尽职守,一刻不停地工作。致善不能明白她究竟在忙些什么,为何总要这般风风火火、十万火急的样子。
她去接致善,总是一手拖着他疾行。他以前常常会被路边的事物吸引,人行道一边的花园里种的花,遇到的野猫,都可以让他驻足观望很久。他的母亲便会停下来,耐心等待他完成他的探索。有一次,他看到草地里有一张糖纸,印有加菲猫的图案,他试图过去捡,结果被钱阿姨制止了,“哎哟,这种垃圾去捡它干吗?脏死了。”她不由分说就继续拖着致善往前走。
钱阿姨的厨艺很平庸,缺乏想象力。或者更准确地说,她完全不愿意将心思花在研究做菜的式样上面。吃饭的功能性被无限放大了。致善的父亲回家的时候,她会勉强多做几个菜以示隆重,但平时,她就反反复复地做同样几道菜,有的时候,是连着几餐吃同样的东西。
致善唯有以不吃来抗议。钱阿姨摇头叹息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当年有一碗粥喝就很幸福了。你去问问你爸爸,他小的时候有啥吃的,还不是有啥吃啥,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于是他只能反复咀嚼着这难以下咽的食物,然后强行把食物吞咽下去。
钱阿姨热衷于看电视,只要停下来,她就守在一个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前。这是她对于致善家最为满意的条件。她每每看得极为投入,将自己代入角色中,有时跟着抹眼泪,有时咬牙切齿地痛骂坏人。在这个时候,她会忘了致善只是一个小孩,又像是自言自语般,分析剧情给他听。
有一次,电视里播放着走投无路的女主角准备跳崖自尽。钱阿姨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坐立不安。
“她要做什么?”致善问她。
“她想不开,要寻死。”钱阿姨回答他。
“然后呢?寻死之后会怎样?”
“寻死以后就没有然后了。人死了,就什么都结束了。只能等着投胎下辈子了。”电视里的女主角被救了回来,钱阿姨松了一口气,总算得以分神回答致善的问题。
下辈子,致善想象着,是不是和做梦醒来一样,只是开始第二天的生活。
“下辈子啊,可能做只狗,可能做只猫,也可能投胎继续做人。”钱阿姨试图解释这个概念,却发现她所知道的,也只是一种随机分配般的角色扮演,与她想要表达的那种深层的宿命的东西相去甚远。她对自己的表达有些失望,但想着致善只是一个小孩子,也未必理解,于是又释然了,转而继续将注意力放在电视剧上面。
大部分时间,他就一个人独自待着,看书,玩拼图,打发漫长的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间。愈发的沉默,有时只是发呆,大脑处于一种茫然一片的停滞状态,仿佛灵魂从身体抽离,俯视这个属于自己的肉身和周遭的生活。猛然回过神来的瞬间,竟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
少年的时光像是被显微镜放大过,泛滥成灾。他盼着时间快点过去,可又不确定期盼着怎样的一个明天。他尚未厘清时间的概念,只是觉得似乎等不到未来。
十岁那年,他父亲带回来一个女人。
她第一次出现,穿着尖细的高跟鞋,走起路来发出急促的噔噔声。她俯下身来摸致善的脸,亲热地称呼他,致善。
他看到一张妆容极浓的脸,扑着厚厚一层粉,脖子以上的颜色和身体的颜色是脱节的。眉毛很细,似乎是剃掉了原来的眉毛后画上去的,如果用橡皮擦一下,可能会把眉毛擦掉。鲜红的口红,凑近了闻,有浓郁桂花的气味。不是秋天街头桂花树盛开时的味道,而是初冬落在泥土里的花瓣,失去了生命力,腐败的躯体带着的尚未完全逝去的味道,混杂在寒冷空气里,莽莽撞撞冲入人的鼻翼。
头发是精心烫过的,染成时髦的深棕色,喷了厚厚一层定型的发胶,像是带上了一个巨大的刷碗用的钢丝球。
看不清楚这张脸谱一样的脸,如若拭去妆容回到原初,究竟是什么模样。但是这张脸让他莫名的紧张,有一种剑拔弩张咄咄逼人的气势在里边。
她笑起来极其夸张,鲜红的嘴巴可以一直咧到耳根,细长的眉毛上扬。她似乎很能干的样子,矮小的身子踩着高跟鞋走来走去,就像女主人一样。
有时她大声呼喝钱阿姨,用命令下人的口气,让她出去买菜,洗衣服。这个房子里原有的一种平衡被打破了。
她给他买新衣服,以她自己的审美趣味,硬邦邦的小西装,繁复的夹克衫,时髦的牛仔裤和皮鞋。她不由分说让他穿上,一手搂住他对着镜子说,好看多了。
他父亲带上他们俩出去吃饭。致善穿着崭新的衣服,硬得像木头做的衣服,糨糊一样裹在身上。新鞋子硌得脚趾生疼,每走一步都好像是被车碾过一次。他父亲和那个女人在餐桌上热烈地交谈,生意上的事情,一些他没听说过的人和听不懂的事。致善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也没有办法放松,他感觉自己像是被绑架在这个餐凳上的摆设。
她夹菜给致善,也是让人毫无招架之力的殷勤气势,芹菜,狮子头,虾仁炒蛋,百叶结,杂七杂八堆了满满一碗。他本来也没有胃口,这堆得山一样高的食物让他压力极大,甚至有些作呕。他拿起筷子拨弄食物,完全没有要吃的意味。他父亲忽然发怒了,命令他把碗里的食物全部吃完。致善被迫以极缓慢的速度将食物送入口中,努力想要忘记自己正在咀嚼的食物,只是机械地完成吞咽的动作。但是吃到芹菜的时候,他的意识没有办法麻痹下去了,这是他最讨厌的食物,每一个气味都在提醒他,口腔里的芹菜通过味觉嗅觉占领他的大脑,他试图要强行咽下去,喉咙却接受了本能的指令,拒绝吞咽。他终于把咀嚼过的芹菜吐在了碗里,随即迎来他父亲的一巴掌。
他的脸瞬间火辣辣的,脑子里嗡嗡作响,十几秒后才是痛的感觉,但是努力忍住不要让眼泪流下来。他不想在陌生人面前哭。
“没家教!”他父亲骂他。
“也不怪他,一个安徽乡下来的阿姨,怎么教得好小孩?”女人算是在安抚。他轻轻抬头,正好看到一双筷子将一块红烧肉送进一张鲜红的嘴巴里,酱油汁沿着嘴角渗出,油汪汪地覆盖在口红上。
他继续无言地坐在餐桌前,穿着簇新的衣服。他听不到他们的对话,只感觉到脸颊上刺剌剌的痛和残留在嘴里的芹菜的气味。
他开始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越来越少出门。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慢吞吞从房间无声地走出来,坐在餐桌前,也不挑剔食物,只吃离自己最近的菜。
女人对钱阿姨颇多微词,嫌她做的菜粗糙,洗衣服不分颜色布料。钱阿姨开始时尽量隐忍着,终于发展至水火不容的地步。女人扬起眉毛,拔高了声调数落钱阿姨,指责她缺乏常识,将一件昂贵的羊毛衫烫坏。钱阿姨在那个当下,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之前积累的种种怨气一概而出,当即发狠说不做了。
致善躺在房间里发呆,听到外面的声响,他神经绷得紧紧的,每次有人提高音量他的心就跟着提一次。可是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他似乎已经开始习惯接受事情往最坏的方向发展。这段时间以来,他已经感觉到那种紧张的气氛,终于发展至鱼死网破的地步,好像反而令人松了一口气。如同预见到一个垂危的病人即将死去,却不知道究竟可以捱到什么时候,每一天在惴惴不安的绝望中度过,终于到垂死那一刻,暗地里有长吁一口气的感觉。
可是,有的时候事情并非到了最坏的地步,只是最坏的开始。钱阿姨离开了,他又回到了没有任何依靠的状态。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如此需要依赖某一个人,或者某种恒定的状态。钱阿姨的简单粗糙里有种让人放心的宽厚,她走后,这个房子里连唯一令人安心的东西也失去了。
他开始失眠。无论怎样,大脑总是处于一种极度清醒的状态,而且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越亢奋。脑子里闪出无数的画面,或者不受控制地运算数学题。大脑后侧仿佛有人紧紧拉住了一根神经,刺激着思维的运作。可是一旦坐起身,头脑就昏昏沉沉像打翻了糨糊一般。
白天上学的时候,他坐在教室里,精神不受控制地涣散。声波的传播速度变得很慢,周围的声音到达他的耳膜,继而传送到大脑给出反应,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是有时又突然无比焦虑,似乎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稳妥的欢愉里,除了他,看不到未来的任何可能性。
他也害怕看到那张鲜红的嘴或是听到高跟鞋急促的声音。于是总是紧闭着房门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下辈子,他想,如若可以做只猫,也不错。正在想着,他的父亲粗暴地敲门,他心惊肉跳地起身开门。一群人涌了进来,是请来的装修公司的设计师和工人。他们站在致善的房间里大声讨论着如何改造房子,摆设家具。他只听到轰隆隆机器轰鸣般的吵闹声在房间里回响,震得头脑发胀。两个穿灰色衣服的男人走近了书柜,开始搬动书柜,他茫然地站在那里看着进行中的一切。声音好像是变成了无比喧闹的背景,与那些走来走去指手画脚的人似乎没有关系,那些互相交谈着,搬动家具的人,只是在喧闹的背景下演出一场哑剧。
然后,他听到一个清脆的砰的声音。世界忽然安静下来。他看到地上是打碎了的玻璃罐,玻璃弹珠像蔓延的洪水般朝四面八方滚出去。有一些像跳跃的浪花在地上弹动,有一些在原地迅速打转。光从窗口斜射进来,照在满地的玻璃弹珠上,反射出各种耀目的色彩。那是他曾经举起弹珠对着太阳时看到的光。他听到后脑勺有一个橡皮筋绷断一样清脆的声音,如同收到洪水泄闸的讯号,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叫。
他被带到医院,坐在充斥着消毒药水味道的过道里等待。一个穿白大褂,戴着厚眼镜的中年男人用粗厚的手指抬起他的眼睑,转动他的头。检查完毕,他在诊断书上面用钢笔沙沙地写下几个潦草的大字,他依稀可以辨认到四个字,神经衰弱。
他不需要去学校了。每天吃很多白色的药片,味道极苦难以吞咽。就着水仰头吞下药片,苦涩的味道却还停留在喉咙处,无论喝多少水都无法冲散或稀释的苦味。胃口因此变得很差,所有的食物吃起来都带有药物的味道。
药物的作用下,焦虑的情绪似乎没有那么明显了,换来的是对什么都无法提起劲的一种懒散淡漠。认字,看图反应极慢,如同老式电脑不够容量处理信息,以致滞后许久。头脑总是处于一种晕眩的状态,周围的事物好像永远在一种失衡的旋转晃动之中。
半夜醒来,药效过了。一下子回复清醒,是站在萧瑟秋夜里,寒风吹过头脑带来的那种彻底的清醒。他起身站在镜子前,看到一个瘦弱的身躯,乱蓬蓬的头发,面颊瘦得凹陷下去,眼睛周围发青的一圈,鬼魅一般。他忽然感到非常困惑,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在这样的一个躯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