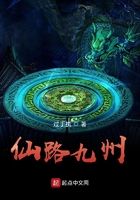计程车里播放着电台节目,是异常喧闹无厘头的callin节目,除了主持人放肆的笑声之外,完全听不清楚究竟在讲些什么。打电话进来的听众絮絮叨叨地讲着自己的感情故事,被几个主持人七嘴八舌的讨论完全覆盖掉,甚至不能理顺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苏锦深再一次看了看表,已经七点十分了,约了七点在中环,如今还一动不动地堵在隧道里。主持人的嘈杂声终于停止,开始在间歇播放流行歌曲。司机气定神闲地跟着节拍,用手指在方向盘上敲打。苏锦深探头向前方看了看,一辆接一辆的车像巨大的蜈蚣一样,延伸到看不见的尽头。这样一个周五的晚上,车里坐着的,多半是赶着下班回家吃晚饭,或者约了朋友出去的人。
“这个钟数是这样的啦。”司机一边安慰,一边开始换台。计程车司机是典型的中年男人,从计程车后座只能看到他头发稀疏的后脑。车前窗有司机的证件照,是看过后转身即忘的普通南方男人的脸。方向盘上面摆了一排的手提电话,从坐上计程车开始的半个小时内,司机已经忙碌地接了几个电话,全是繁忙的电召生意。堵在隧道里的这段时间,司机有条不紊地安排了接下来的几场生意,周末是计程车司机的黄金时间。滞留的这十几分钟,丝毫没有影响司机准备迎接繁忙生意的好心情。
主持人高频率的声音再次出现,充满了这个小小的车厢。急促的语速与锦深的焦虑交织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像一根越拉越满的弦。突然之间,锦深感觉释然了。当知道无能为力的时候,不如干脆随遇而安,这是锦深一贯的态度。只是迟到,还是让锦深有点不舒服,对于一个极度讲究准时和效率的人而言,无论何种原因的迟到都是不可谅解的。锦深决定给陈致善发一条消息,告诉他自己将迟到十分钟。
“你好,我是苏锦深。不好意思,迟到十分钟,还在路上。”
一分钟后,收到回复。“Take your time.”这种简单的回复让锦深感觉放松了一点。
十分钟后,巨大的蜈蚣终于开始蠕动,慢慢加速。伴着电台嘈杂的声音,速度也渐渐令人亢奋起来。七点多,这个城市还笼罩在晚霞的余晖中。爬出隧道,马路两旁的高楼闪烁着微弱的灯光,远不及玻璃幕墙反射的夕阳来得耀眼。从的士窗口望出去,只能看到远处一栋又一栋的高楼,天空从密集的大楼的缝隙里露出来,被划成零零碎碎的一小片。远处码头起重机在繁忙地工作,巨大的工地上堆满了各种建筑材料。从车里望过去,像是这美丽的海湾背脊上一个巨大的疤。车子一路开进狭窄的街道,每一个红绿灯的两边都站满了人,如同随时会出闸的洪水。
这个城市似乎永远在繁忙的川流不息中。走在马路上的人,如果步伐稍微慢一点,就会被后面汹涌而来的人潮吞没。连红绿灯的提示音,都是急促的,逼着你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扶手电梯的速度是快的,便利店售货员的结账速度是快的,更不要说午餐时间的快餐店。锦深来到这个城市已经快十年了,也已经习惯这个节奏。每一次去机场,坐在机场巴士上看两边连绵起伏的青峰和远处耸立的高楼。或是在机场快线上,透过斑驳的电线看到对面海天一色、干净纯粹的白和蓝。在这个时候,她竟会莫名地对这个城市生出些眷恋。她已不记得当年为什么会被选中来参加这个交换生计划。只是从此,她的人生轨迹,从上海这个城市交错到了香港。一切好像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对锦深而言,甚至有点暗暗的释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再没有过去,没有纠缠不清的人际网络,一个人飘零在异地,落得个清静自在也好。一旦决定,所有的困难就如记事本上罗列的计划,只需完成,微不足道。从初来时提着一个行李箱迷失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到现如今如一个熟稔不过的街坊一样下楼吃早餐买报纸,其间的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种种可料想之困难,似乎只是随空气蒸发之露水,淡然了无痕迹。
出租车停在餐厅楼下,七点三十五分。
电梯里照例塞满了人。都是附近工作的上班族,黑压压的一片,全是深色西装。穿过人群的缝隙,锦深在电梯的镜子里看到了淹没在这一片黑色中的自己。深灰色的boss西装,黝黑的皮肤,刚刚及肩的短发。因为下午去见一个重要客户,搽了一点点深蓝色的眼影。电梯门开了,黑色的潮水突然间涌了出去,四楼是一家很受欢迎的日本餐厅。电梯继续向上,锦深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电梯里,面对对面镜中的自己,像是被一个陌生人直直盯着一样。刚刚下班,深灰色的西装上面还是一副要去和人商业谈判的神情。锦深脱掉了西装外套,里边穿的是粉色衬衫,看上去不那么严肃,又理了理头发。六楼到了,是一家著名的广东菜馆,今年被评为米其林三星。
餐厅是陈致善挑的。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相亲安排中,苏锦深完全处于被动。这几年,锦深偶尔也会去参加一些相亲活动。恋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可是结婚,却如同升学就业考专业试一样,是必须完成的一个任务。如果哪天醒来,发现自己已经结完婚,床边躺着一个面容端正的男子,该有多好!这样一来,生活似乎只要按部就班地继续就可以了。
也曾遇到过各方面都不错的男人,在这个时候,锦深也会安排时间,如同计划一项工作任务,比如吃饭,看电影,所有的步骤都按情侣发展的模式逐步推进。但是在某一个节点,对方像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只是这项任务中被计划的一部分,带着点不甘心慢慢退出苏锦深的世界。
二十八岁的苏锦深最近开始认真地考虑结婚的事情。财经杂志介绍的那些光鲜亮丽的成功人士,无论男女,似乎在事业成功的同时,亦都经营着一个模范幸福的家庭。锦深接受这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并且按着这种理所当然的逻辑生活。
久未联络的大学师姐突然打来电话的时候,锦深正坐在会议室里对着一堆资料和Excel表格埋头工作。晚上十一点,中环的街道人迹寥寥,办公楼却还是灯火通明。对于这样一个深夜莫名来电,锦深有点意外。
“锦深,还在工作啊?”
“是啊,最近有点忙。”
“这么晚还在加班。像你现在的工作状态,应该还没有男朋友吧?”
“噢。倒是还没有。”锦深迟疑了一下,如实回答。面对突如其来被质问个人问题,锦深有一点无所适从。
“我老公的朋友的同事,加拿大读书回来的,跟你一样年纪,已经是董事了。他们是家族企业,在上海、香港都有业务,虽然不是什么城中富豪,但是条件也算够好了。要不然安排见面吃个饭吧?”
哦,是这样啊。锦深听上去似乎有些无动于衷。头脑里一个计算回报率的Excel公式顽强地霸占着她的思维,令她无法对其他事情作出适当的反应。
她好像是怕锦深会拒绝,又开始描述起她所知的这个相亲对象的优点,包括家世背景、学历,种种硬件条件。
“那麻烦你和他确认一下见面时间吧。”如果锦深不应承这个安排,这个单方面的对话估计会持续下去。
“那我去安排,”师姐语气中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末了还叮嘱一句,“总之,遇到这样的黄金单身汉你可要把握机会噢。对了,他叫陈致善。”
对于安排相亲活动,锦深倒也没有特别抗拒。当然师姐在电话中对于陈致善的种种溢美之辞,锦深也没有太过在意。虽然结婚是锦深近来想要完成的事情之一,对于结婚的对象,却从来没有过一个具体的要求或标准。多少女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幻想着将来穿上婚纱嫁为人妇的那一刻,或是列数出种种心目中完美配偶的条件。可是对于锦深而言,结婚的对象似乎只是一个面容模糊的存在。更何况,锦深虽然接受主流的社会价值观,认同金钱地位所划分出的等级,却始终还是一个自持的人。
锦深记得,这位热情的师姐,在读硕士期间没好好上过一门课,却常常跑去旁听MBA的课程,一年后终于在人家课堂里找到了合适的男友。锦深常常会在她焦头烂额之际帮她准备些助教讲义、论文资料,本是权且当作自己学习之用,反而意外地结下了这份交情。
挂了电话,想到这位师姐,锦深觉得自己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似乎真的有点太漫不经心了。抬起头,会议室里的同事们,面如死灰地对着电脑屏幕快速敲打着,似乎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不会有任何反应。而她刚才的电话和思虑就好像只是不小心跑到错误的分叉路上而已。
周一的时候,收到陈致善的消息,询问周五晚上是否有空一起吃饭。他的语言平实简单,却莫名地给人自然亲近的好感,像是一个久未谋面的朋友发出的邀请。在工作日,因为工作强度和时间的不确定性,除了工作应酬,锦深很少约朋友。对于陈致善周五的邀约,锦深有点迟疑。若是改期,难免让人觉得自己可能在摆架子。锦深想了想周五的工作安排,倒也不是没有可能,不知怎地就横生出一股杀出一条血路也要出席的决心来。
锦深走出电梯进入餐厅。周五的晚上,餐厅异常喧闹,座无虚席。锦深跟着带位的服务生穿过餐厅来到尽头的包厢,门推开了,一个斯文的男人坐在里边。
“你好,我是苏锦深。抱歉迟到了。”
男人放下手中的菜单站起身,露出略带羞涩的笑容:“你好,我是陈致善。”
有那么一刹那,锦深在这羞涩的笑容和开场白面前竟不知如何应对。双方站在餐桌两端,定格了几秒钟之后,陈致善回过神来,道:“请坐。菜我已经点了,如果有什么不喜欢的食物,请不要介意,我让厨房换。”
“没关系,我对食物不挑剔。”这是实话。锦深对于食物,没有强烈的喜恶。但凡经过适当烹煮的正常食材,对于锦深来说都是不错的果腹之物。锦深总是怀疑,那些愿意跋山涉水去找寻,或者排几个小时的队去等候的美食,真的能给味蕾带来如此大的愉悦感吗,还是只是一种心理暗示?而对于那些号称自己对什么过敏,又或从不碰什么食物的人,总觉得那是一种矫情。
“刚刚下班吗?”
“是的,路上有些堵。”
陈致善的面容在餐厅灯光下显得有些苍白,衬上蓝白条纹的衬衫,给人一种柔弱的感觉。虽然高大,身形确是单薄的那种。干净的短发,不知道是不是灯光的缘故,是浅浅的亚麻色。手臂到手背,清晰可见隆起的青筋。加上皮肤白,更加显得触目惊心。
包厢的气氛有点冷,双方都不是那种热络的人,可以一见如故地攀谈,可是也不觉尴尬。在这间歇的静默之中,像是有种默契存在。
陈致善拿起餐桌上的白色茶壶,帮锦深添茶。锦深低头,看到陈至善白皙修长的手指,手指的关节却大得出奇,像是另外安装在手上以连接那几节不成比例的手指。茶还是烫的,陈年普洱的香气慢慢弥漫开来。
菜很快上来了。热气腾腾的菜肴令气氛也开始轻松起来。服务生忙碌地穿梭其间,添茶盛汤,竟令这小小的包厢有种热闹的假象。
“一定要试一下脆皮烧肉,是这家店的招牌菜。”
“好的,谢谢。”锦深继续低头喝汤。
“这里的脆皮烧肉,需要选用肥瘦均匀的五花肉,先过水,腌渍,晾晒两个小时,再在两百多度的烤箱烤三道才出炉,所以肉皮特别松脆。”陈致善像一个美食节目的主持人。
“嗯。”锦深想象着整个制作工艺,如同记录一个复杂的化学实验,必须记住每一个试剂的分量,以及反应的时间。
“你不喜欢吗?”
“什么?”锦深有点不太明白这对话的逻辑。
陈致善笑了笑。锦深发现他笑起来有种童叟无欺的真心实意,或许是因为笑起来眉角铺开的鱼尾纹的关系。“通常别人听到后,都会直接去夹起来吃。你的回答,像是应承一件布置下来的任务。”
这么尖锐的话,配上他宽厚无比的微笑,让锦深有点摸不透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是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吗?锦深生活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各自隔着铜墙铁壁,对话是迂回和退避三舍的,尤其是工作以外,没有人会去深究你的潜台词,有时是不在乎,有时是故意视而不见。每个人都忙着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暇顾及,亦不想冒险侵入别人的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