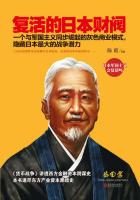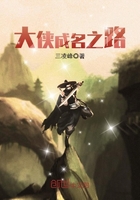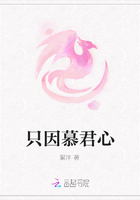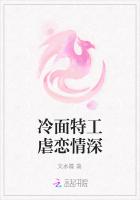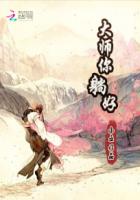莫怪河豚价不廉,
桥南酬过五千钱。
谁知太宰归田日,
只与屠沽意气鲜。
徐明珠是一个十分精明老道的商人,他在做买卖的过程中,在各地安插有“耳目”,相当于今天的经济情报人或市场信息调研员,根据当地情况不定期地向他报告市场行情、商品价格等。他在这些情报的基础上再加以综合预测,然后才决定经营行为和经营项目。
这天,他正在账房与掌柜李安议事,这时他安插在常熟县的耳目郑金龙风尘仆仆地回来了。此人比较精明,办事能力也较强,重要信息都能够及时捎给徐明珠,徐明珠对他比较满意。
徐明珠一见是郑金龙亲自跑回来,就知道一定是带回来了什么重要信息,一问才知道是棉花价格暴涨的情况。这正是徐明珠目前最关心的问题,刚才他与掌柜李安谈论的也是这事。看来郑金龙也比较清楚主人的商业行为和内心活动,故而亲自把这个重要信息带了回来。徐明珠赶忙询问棉花价格。郑金龙环顾一下四周,见这里只有主人和掌柜,于是伸出右手比了一下。“哦?暴涨到这个数了?”徐明珠不禁暗暗吃惊。他不大放心地又追问道:“价格是否确切?”郑金龙向他保证到,这是他亲自去市场问了好几个棉商得来的一手情报,绝对可靠。徐明珠觉得不妥,于是又问起了棉花价格暴涨的原因,但是郑金龙说由于他急着赶回来,以免延误商机,就没有多查,所以不太清楚。郑金龙说得很在理,商场竞争激烈,一条有价值的信息往往比什么都珍贵,最需保密和及时,倘若信息泄露被其他商家截获,让别人捷足先登,那就悔恨莫及了。这都是徐明珠曾向他交代过的要诀。问过情况后,徐明珠让郑金龙到后堂歇息去了。
待郑金龙走后,徐明珠转身问掌柜李安是否知道本地棉商谁有囤积?李安对此了如指掌,他知道唯有杨氏一家还囤积了不少,主要原因是当时与杨氏做生意的那个蒙古商人杀价太低,杨氏觉得亏本太多,因而没有成交。
徐明珠知道后,沉吟道:“蒙商大量收购棉花,其中定有原因。不知其他蒙商和东北人是否已经到了常熟一带,我想应当有这个可能!”掌柜李安当然明白徐明珠的意图,现在既然常熟棉花行情暴涨,或许那个蒙商还会返回来购买杨氏囤积的那批货。另外,如若杨氏知常熟的棉花行情,那么它也会随行就市抬高价格的。老板是想抓住时机,把杨氏的积货全部买下。但是这样做风险太大!弄得不好,倾家荡产。但若过分犹豫,已到手的厚利就会白白跑掉。此时到了关键时刻,徐明珠的思绪像波涛般汹涌翻腾,眉头皱得很紧。买,还是不买,就看他一句话了。突然,徐明珠说:“走,我们一起出去到杨仁贵那儿走走!”
棉商杨仁贵与徐明珠在生意上打了多年交道,但一般都由手下的掌柜具体接洽,两人倒很难碰面。因此,当徐明珠亲自登门到杨家时,杨仁贵自然是摆上酒宴,盛情款待。
两个商人寒暄客套过后,就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主要是些生意上的事。李安见主人只字不提棉花的事,自己当然也不便提及此事,就全当没有这回事,只顾吃酒聊天。酒过三巡,徐明珠这才开口:“杨兄,你真是老于世故啊,直到现在还不问我徐某今日来贵府所为何事。”杨仁贵笑道:“非也,非也。不瞒徐公说,我确实正想此事。但我又想,我如若向你问及,那我设宴款待徐公不就显得有些虚情假意了吗?徐公与我杨某难得相见,今日坐在一起喝喝酒,叙叙旧情,也是稀罕可贵之事,不一定非得马上谈买卖。不过现在徐公既然开口了,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还望徐公不吝赐教。”
徐明珠摆手笑道:“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今日是路经贵府,想顺便来问问你囤积的那批棉花。听说曾有个蒙古商人来看过,但后来交易未成。”
徐明珠故意首先提到杨氏上次交易失败,先将对方置于一种被动位置,这样,买方在无形之间就先胜了一筹。没想到,杨仁贵听了很是漫不经心地问他的掌柜道是否有过此事。他的掌柜答道的确曾有个蒙古商人来过,但那天他也不在,后来听二掌柜提过。杨仁贵巧妙地一问三不知,什么情况也没透露给对手。他反问说:“徐公想买这批货么?”于是徐公直言不讳地肯定了他的提问。杨仁贵笑道:“据我所知,徐公是个作风稳健之人,一向不会轻易投入资本。怎么,你要将这批货销往何地?怕早已有了买主了吧?”徐明珠玩笑道:“恕我无可奉告。”杨仁贵一愣,也哈哈笑道:“呵,对、对、对,来来,请吃菜”。停顿片刻,又说:“既是这样,那我杨某也愿助你一臂之力!”席间,徐明珠假装问掌柜李安道:“上次蒙商来此地收购棉花,那些棉商卖的是什么价?”李安用手势比出一个价。桌上的人均迅速地朝李安的指头一瞥,然后很快把眼睛移开,就像没看见似的。杨氏望着桌上的盘子说:“徐公与我不是外人,价格的问题嘛,好说,好说。”一连说了很多“好说”,可就是不把价格说出来,只是当着众人的面对他的掌柜轻轻耳语了一番。他的掌柜会意,于是用手指比划了一个价,道:“既是老交情了,就这个价吧。”
这个价比上次蒙古商人出的价要高,但比起目前常熟地区暴涨的价格来又要低很多。徐明珠念头转得飞快,一下便计算出这批货的差价和总利润,不由暗暗欣喜。但他不动声色,作出为难的样子说:“这……这个……”杨仁贵并不松价。过了很久,徐明珠见杨氏像是铁了心一般,于是站起身来叩手道:“好吧,待我先回去考虑一下,两天之内再回话,告辞。”于是徐明珠和掌柜李安离开了杨氏的家。
一走出杨府,徐明珠便摇头道:“我现在愈来愈觉得这其中有问题!”
这让李安不由吃了一惊。徐明珠给他分析自己看到的几个疑点:首先,常熟的棉花为何暴涨得不可理解。据他多年的经验和目前对棉花市场的分析与判断,棉花价是不可能上涨的,即使有特殊原因上涨也不可能是那种价。其次,在与杨某的交谈中,杨氏绝口不提常熟的棉花行情,可能他早就知道郑金龙常驻常熟,但他却只字不提郑金龙,好像在回避,只问是否已有买主。再次,按照常理,杨氏是应该急于将货脱手的,他却反而故作镇定,好像尽量在掩盖什么。听了老板的分析,李突然明白了,可能这次是郑金龙与杨仁贵合谋设了个局。徐明珠想了想,便对李安耳语一阵,李安笑了,点头称是。
到了晚上,徐明珠让李安去把郑金龙叫到厅堂,对他说了决定去杨仁贵那里买货的情况。郑金龙听后赶紧催促,劝主人买下这批货,还说定可获厚利。但是徐明珠又说为了慎重起见,要李掌柜明日与郑金龙一道再去一趟常熟,等重新核准棉价后再作决断。哪知郑金龙一听,忙说这样一去一回,那批货被别的商家买走,还是别去的好。但是徐明珠表明常熟是一定要去的。即使货被别人买走,只当没有这生意,也不可冒险行事。“但是,如若不做,实在可惜啊!”郑金龙急切地说。徐明珠说:“事情是这样的。昨晚我做了一梦,梦见我的一名伙计已被别人买通,串通起来想骗我。这虽然只是个梦,但我这人做事历来小心慎重,故而多此一举。谁叫这件事如此巧合呢?”
郑金龙听后,似乎有点心虚,瞥了徐明珠和李安一眼,见他们正在盯他,于是连忙将眼睛躲闪开。厅堂内沉默地使人窒息。突然,徐明珠用一种怪怪的声调问郑金龙来他这里做事有多久,以及是否亏待过他等等。问得郑金龙支支吾吾,连连摆手。事后,郑金龙愈想愈觉得不对,于是坐卧不安,在房里来回踱着。第二日一早,人们发现郑金龙早已逃走了。
真是中了那句俗话:姜还是老的辣。徐明珠的走街估测、多方打探最终使得郑金龙的阴谋败露。在商情瞬息万变的商海中,单凭经验是不行的,必须扎实地吃透市场行情,并捕捉每一个与之有关的信息,进行细致的分析,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后往往得出的结论才最接近现实。只有充分了解了商情,并充分吃透商情,才能对市场行情作出准确地估测。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商海中,谋得一席之地。